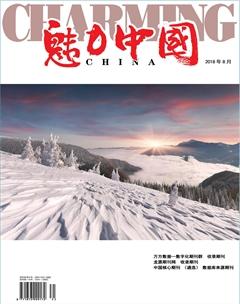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日本文學研究
李文竹
摘要: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的祭日,然而對于這一歷史問題日本依然堅持否認和掩蓋史實,因此有必要對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日本文學進行梳理和研究。本文選取了兩部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日本文學,進行正反兩方面的對比研究。一部為堀田善衛的《時間》,另一部為同是戰后派作家的三島由紀夫的《牡丹》。相較于堀田善衛對于戰爭的人道主義反思,《牡丹》有著強烈否認歷史的傾向。本文從形象學的角度研究《時間》與《牡丹》中的人物形象,并通過文本分析探尋兩位作家對戰爭與歷史態度的不同,以此對人性進行探求,對歷史進行思考,并進一步揭示日本殖民侵略的野心及企圖抹殺掩蓋歷史的丑態。
關鍵詞:堀田善衛;《時間》;三島由紀夫;《牡丹》;南京大屠殺
2017年2月24日,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新作《刺殺騎士團長》在日發行,由于書內提及了南京大屠殺真實的屠殺數據,而遭到了日本右翼團體的“圍剿”。然而據日本銷售調查公司“ORICON”公布的數據顯示,這本書上市前3天就賣了47.8萬冊,位列綜合銷售排行榜第一。此書雖廣受中國讀者的高度贊揚,亦引起一小部分日本讀者的不滿。戰后日本,特別是其右翼分子既沒有放棄他們的侵略史觀,也沒有深刻反省戰爭罪行。因此研究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日本文學與史料,了解日本左、右翼和中間派的各種觀點,對雙方爭議較大的問題展開討論,可以更好的去審視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問題。
一、堀田善衛《時間》對中國人形象的塑造
1945年3月,為了躲避國內的戰事,堀田善衛乘飛機來到上海。在上海,他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暴行,切身感受到了被占領國的人民的悲慘與恐懼,由此激發了他對戰爭的沉痛思考。而關于《時間》的創作動機,應該緣于他的一次南京之行。那次他同友人一同登上了因戰事而傷痕累累的南京城墻,悲慘的戰爭場景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回國后,他在中國的所見,所感,所思交織在一起,醞釀了他蓬勃的文學創作能量。
堀田善衛于1954年底創作完成了《時間》,這部作品是日本作家撰寫發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從日軍占領前的人心惶惶到日本占領后人們的恐慌與戰栗,從日軍種種令人發指的惡行到百姓流離失所,全文充滿了主人公大量的內心獨白與對戰爭、人性的沉痛思考。作者也在文中塑造了很多中國人形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特定時期特定的心理,都是時代背景下社會的縮影,反映了社會現實。因此十分有必要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進行分析與解讀。
其中,很具有戲劇性的一個代表人物是主人公的表妹楊小姐。在蘇州局勢十分混亂之際,她及時審時度勢,逃回了南京,并在危難之時組織難民,組織同敵人接洽班與扶老協幼班,以防止無謂的犧牲,盡可能地掌控自己的命運。從此可以看出楊小姐對生的渴望,對生命的珍視,對時局的智慧把握。但是經歷了南京大屠殺,經歷了顛沛流離與生離死別的她又是怎樣的呢?“楊面對大尉,臉上沒有任何反應。她一言不發,隨意瞥了他一眼,大步地從他面前走過…[1]”此時的楊小姐是麻木的,當她看到了帶給她諸多苦難的日本人,也沒有表現出任何憤怒。她經歷了諸多苦難,在遭受日軍輪奸后自殺未遂,身患性病并服用大量鴉片,此時她身上已遍體鱗傷。但是她并沒有表現出絲毫痛苦的模樣,沒有表情,沒有喜怒哀樂,儼然已變成一具行尸走肉。這與小說開頭所描寫的楊小姐的形象大相徑庭,而這一切一切的悲劇都源于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作者作為一個日本人,卻真實而又詳盡地還原了南京大屠殺的全貌,堅定地守護真實的歷史,其遠見與勇氣令人可敬可嘆。
二、三島由紀夫《牡丹》對日本人形象的塑造
作為戰后派作家,三島親眼目睹了日本戰敗的全過程,他向往中的文化也在他的生活中一去不復返。軍國主義雖然戰敗投降,但它的幽靈似乎還在繼續游蕩,三島在后期民族主義愈加偏頗和極端,以至于最后剖腹自殺。日本剖腹自殺的武士道精神在戰時是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工具,這無疑對三島的審美情感與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三島為了表現自己渴望的美,即使拋棄一切倫理道德亦在所不惜,從收錄了《牡丹》一文的《憂國》開始,他開始走向了下坡路,將美與惡視為等同,其反人道主義和否認歷史的傾向開始暴露無疑。
《牡丹》于1955年面世,是由三島由紀夫撰寫的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小說,這篇文章描述的是一位名叫川又的老人,曾是南京虐殺的戰犯。在逃避了戰時審判之后,買下了一座牡丹莊園,親手栽種牡丹,并將牡丹數量嚴格控制為五百八十株。“嚴格地說,上校作為一種娛樂,親手實際殺戮的是五百八十人……這個家伙是在利用一種詭秘的方法,紀念自己的罪惡。[2]”三島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將其稱之為“罪惡”,實際上這樣一個“殺人魔”,在三島筆下卻成為安享審美愉悅的藝術大師。川又當年在南京犯下了種種惡行,但是他卻沒有絲毫的懺悔與反思。他親手栽種的一株株牡丹實則為屠殺人數的轉換,他曾屠殺的人數只有五百八十人,并且僅是作為一種娛樂。而據資料記載,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約有超過26萬名非戰斗人員死于日軍手中,還有專家認為這一數字超過35萬。[3]而文中的川又由于這“僅有”的“娛樂”竟要遭受審判,他自身甚至感到了一股委屈與無奈。這些都表明了作者對于歷史真相的掩蓋、曲解與辯護,具有強烈的反人道意味。而在作者飄忽的敘述中,川又對南京大屠殺應負的責任就這樣被飄然吹散。
三、結論
與日本爆炸原子彈和歐洲猶太人遭到屠殺不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恐怖很少為亞洲以外的人們所了解。更有甚者,頑固的日本人拒絕承認自己的過去,并篡改教科書試圖掩蓋這一事實,給這段歷史及中日關系蒙上了一層塵埃。但是仍然有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作家,真實地書寫了這一歷史,也有一部分日本作家,試圖用作品扭曲這段歷史。因此,研究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日本文學作品,對于我們更好地審視這段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堀田善衛.堀田善衛全集[M].筑摩書房,1958.81-163.
[2]陳德文.鮮花盛開的森林·憂國[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10.
[3]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M].東方出版社,1998.14.
[4]秦剛.用“鼎的話語”刻寫復生與救贖[J].文藝報,2017.12.
[5]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23.
[6]胡春毅;惡之花.三島由紀夫《牡丹》的大屠殺敘事[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5.6.8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