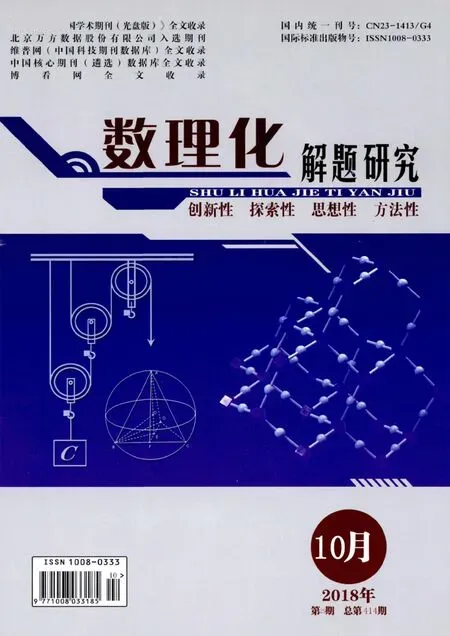從理論走向實踐 淺析以學為中心的數學課堂
王露錦
(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攝山星城小學 210000)
一、從虛擬走向真實——基于學生真實的起點
教師在上一節課之前,特別是公開課,往往會精心備課,絞盡腦汁進行精彩導入.而有些課我們是不需要特別導入的.比如《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計算》,我們要不要導入?我看不必.有的老師會提前給學生做預習單,學生對要學習的主要內容已一清二楚;有的老師不提供預習單,但今天要學的課題也會在課件上不經意間“暴露”出來;即便是不做預習單,課件上課題也隱藏起來,聰明的孩子也會根據課本教學內容安排,老師的只言片語“提示”想到今天要學什么內容.所以,就學習內容而言,孩子不是一張白紙.
當然,正視學生真實的起點是很難的,因為他有無窮的可能性.老師教學生有三種,一種是教完全不會的學生,第二種教有點會的學生,第三種是完全會了的學生的,你最怕教哪一種?有人說完全會了的學生,還有人說半會不會,反正最喜歡教完全不懂的學生,因為有極強的可塑性——想怎么教就怎么教.但是,我們面對的孩子,大多數是懵懵懂懂,有點感覺,似懂非懂的,你讓他把具體的情況解釋清楚,他也說不出來,只懂了些皮毛而已.因此我們要本著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去設計教學.所以,學生進入課堂時,不是對新授“一無所知”,而我們的教材在內容安排時往往把孩子當作對知識的“0起點”來安排內容,這就要求教師要根據學情(實際教學對象的情況)設計教學.
二、從隱形走向顯形——暴露學生的思維過程
優秀的數學老師最擅長對癥下藥;“費力不討好”的老師問題出在——隔靴搔癢.沒有哪個老師是不敬業的——學生作業出了問題,老師很生氣:“我都講到這份上了你怎么還不懂?今天這個作業你訂正了n遍了怎么還不會!”因為他不懂的地方老師根本就沒講明白.給學生補差,不是哪里差補哪里,而是要往后退,退到他懂的地方,才能往前教.一個好老師能夠讓學生在課堂上非常坦然地說出“我不懂”,才能充分暴露出他思維的過程.
如學習《因數和倍數》一節,學生初次接觸關于數的性質,枯燥又抽象,“找出100以內的質數”是教學的重難點,但學生“屢教不會”.很多教師為此發愁.此時,我們可以采用《第56號教室的奇跡》里的Buzz小游戲,改善大量練習造成的負面效應.
我們經常會聽到一些老師這樣說(尤其是上公開課時):“今天課堂上學生配合得很好.”從這樣的話語中,我們看到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從屬”的地位;當課堂成為了教師表演的舞臺時,學生又怎么能在一種自由、安全的環境中學習呢?學生說什么,成了學生猜測老師想讓我說什么,想想這樣的課堂,學習又能真正發現多少呢?
再看《認識負數》中,把12張數字卡片貼在黑板上請學生來排序,排序的過程就是暴露學生思維的過程,孩子能把他對負數真實的感覺“貼”在黑板上,并且借助這12張數字卡片,聚焦大家討論的焦點,讓學生展開討論,所以說,呈現結論,不要過早.暴露學生的思維過程,對癥下藥更重要!
三、從舉一反三到舉三反一——凸顯概念的本質
概念是什么,概念是“捅破一層窗戶紙”,就是孩子他心里有,但說不出來.作為老師,總想快點捅破這層窗戶紙,可是概念是不能簡單地、快速地、剛有點感覺就灌給孩子的.
四年級上冊《可能性》,補充習題有道題:一個口袋里裝有20個同樣大小的紅球,10個同樣大小的綠球,小明每次任意摸1個球(摸后放回袋中),摸30次,把他摸到每種球的次數畫成的條形統計圖(每格表示1次).因為我沒有提前讓他準備20個紅球,10個綠球,所以布置這個作業的時候,我的心里預設學生做題不順利.第二天早上作業我沒急著收,我統計學生作業完成的情況:“有多少同學完成了?”一大半的學生都舉手表示完成,還有幾個沒做,他們表示:“我們家里沒有那么多的綠球和紅球”.這是第一種層次的學生,理由也說得通.對于完成作業的學生,我問:“能說說你是怎么做的嗎?”馬上就有人說:“沒有球沒關系,可以自己用紙一團,一摸,不就行了嗎?”你看,第二種層次的學生他已經曉得自己去做了.第三種層次的學生就更厲害了.他說:“老師,我拿撲克牌代替球,20張紅桃,10張黑桃,就代表這些球了,一摸,就出結果了.”我們發現,這三類層次的學生對“統計概率”這個概念本質的理解也是有三個層次的:第一層次的學生以為球就是球,所以沒有球作業就沒法完成.第二層次的學生認為球是可以用東西替代的,比如那個用紙擲團的孩子,假如認定紙團大一些的就是綠的,我偏偏摸到一個大的,你摸得不就不準了嗎?只有用撲克牌的孩子,他認為球的替代是需要特定的條件的,是不是特別厲害?他既用東西替代了球,又體現了“概率”的本質.所以有時候,一些簡單的素材就能夠凸顯概念的本質,發現不一樣的數學內涵.
此外,如何進一步凸顯概念的本質,板書的留痕也很重要.《認識負數》這個概念的幾個要點:“比0小,有無數個,帶有符號的數,意義相反的數,基于標準的數”,都會留白在黑板上,供學生回顧反思.因為PPT是說沒就沒了,只有板書是能留著的.所以心中有教案,腦中有板書.概念的形成,從舉一反三到舉三反一.
四、從客體到主體——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
老師們每天上課之前都會想著:“同學們,今天我要讓你們成為學習的主人”.可是課上了一小會就覺得孩子們怎么講不好的呢?我自己來說吧,于是一說就說到下課.尤其是公開課,老師緊張,學生也緊張,有的孩子人一多就不開口說話,這個時候有的老師他就會繞過去,他寬慰彼此:“你坐下來再想想.”如果你一上課就這么說,十有八九注定了你這節課就要自己說到底.學生都很聰明,他們都知道:“只要我不說,老師就得說”.著名特級教師華應龍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故事:華老師有一次外出上課,學生都不說話,華老師拿著話筒對著他,他也不說話,華老師說:“沒關系,我愿意等.”那個學生嚇了一大跳,不得了,下面坐幾百人,我上了這么多年學,沒遇到這種老師,他竟然就在這兒等.學生等一分鐘就覺得很長了.因此,當第一個學生被老師撬動了以后,后面的學生都知道,這回來的這個老師來者不善——他愿意等,所以多多少少要說一點.只要學生肯說,教學就發生了——孩子說的對,老師就提煉精華;孩子說的不對,教師就查漏補缺.怎么讓學生成為主人,老師一定要往后退.
不少人觀察到小學數學課堂中,低年級和高年級學生舉手的情況截然不同.所以,不禁有人感嘆,一個問題拋出后,低年級的課堂中總是“小手如林”、“爭先恐后”,但高年級的課堂卻是“寥寥無幾”、 “鴉雀無聲”,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難道僅與學生的心理變化有關嗎?我們教師在調動孩子積極舉手發言方面,又能做些什么呢?從一些專家的建議和一些老師的實踐中,我們似乎能找到一些規律.比如,將舉手賦予了新的意義,“舉手”代表著你思考過了,你想過這個問題了,就可以舉手;當然,這樣就會很好地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并使他們樂于去交流、去分享;那么如何讓這些積極的同學帶動組員,共同進步呢?我們可以告訴學生,一個人的力量可能太單薄,若有一組人同時來預約,那么準備最充分的組,推薦題目最好的組則更有力量.
要是老師把學生都“教”會了,那這時候的老師必然要做主人,因為你最會,學生都不會.基本的教法是什么,把大概的基本原理教給孩子們就可以了.他有很多不會的時候,你就教給他去用,他用的過程里面會遇到很多困難,這時候,真正的探究就產生了?同學之間是不是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這時候討論就產生了.當你在學生不太會的時候就愿意讓他去用,他一定有可能成為主人.
基于學情,立足學生,建立以學為中心的課堂,就是要充分暴露學生的思維過程.作為老師,不要怕他們“不行”,就是因為他們的“不行”,他們才有可能有思維的碰撞,才會讓孩子們有機會成為學習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