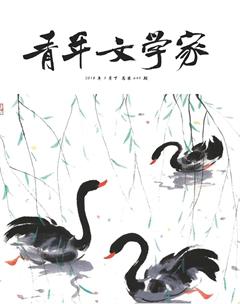審美的“鬼宴”
姚玉林 魏巍
基金項目:本文為上海杉達學院2017年度科研基金項目“席勒美育研究在中國:2007-2017”(項目編號 2017zz12)的階段性成果。
摘 要:《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是日本科幻作家夢枕貘(原名米山峰夫)耗費十七年心血和兩千六百頁稿紙完成的一部四卷本的歷史傳奇小說。小說以日本文化史上的傳奇,“弘法大師”,空海和尚為主人公;描述其于中唐德宗治世,隨遣唐使入大唐留學,其間經歷一系列詭異事件,并通過發現楊貴妃的死因而破解所有秘密拯救大唐的傳奇故事。小說于不久之前被著名導演陳凱歌改編成電影《妖貓傳》。本文認為,《鬼宴》一書存在著三場宴,一是沉香亭眾人皆歡的游戲的極樂之宴;一是馬嵬驛眾人不得不做出的理性的犧牲之宴;一是小說最后的高潮,幻象與現實交融宣泄的鬼宴。基于席勒的美學思想,本文指出,最后的鬼宴其實是游戲沖動的重現,將極樂之宴的審美幻象與馬嵬驛的現實交織在一起,調和了二者之間的沖突,將二者有機統一,顯示出和諧與規則,讓三場宴的參與者彼此的愛恨情仇得到宣泄。
關鍵詞:幻象;席勒;游戲;審美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9--02
夢枕貘耗費了十七年心血寫就《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以下簡稱《鬼宴》)。故事以日本文化史上的傳奇人物,留學大唐求密宗佛法的高僧空海為主角,并輔以一系列中唐傳奇人物,如橘逸事,白居易,柳宗元,韓愈等,以《長恨歌》為線索,通過對馬嵬驛楊貴妃死亡真相的探尋,打造了一場宏大的歷史幻象的極樂盛宴。陳凱歌初次讀完小說后,即有拍成電影的打算。在歷時五年耗費數億之后,其精心打造的改編電影《妖貓傳》于17年底在國內上映。在“咒語的游戲——《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中的席勒美學探析之一”一文中,筆者認為,通過主人公空海親歷的種種咒語,夢枕貘指出語言就是世界,通過咒語控制語言進而就能控制世界。語言的背后則是人心,而世間的本質就是大日如來(佛教中的普遍真理)。空海所求,即是讓自己成為音符,將無形的大日如來轉譯成語言,教化人心。這與德國美學家席勒的“審美教育”的思想有共通之處。而在本文,筆者進一步解讀文本,圍繞書名中的“鬼宴”二字進行探究。認為,《鬼宴》一書存在著三場宴,一是沉香亭眾人皆歡的游戲的極樂之宴;一是馬嵬驛眾人不得不做出的理性的犧牲之宴;一是小說最后的高潮,幻象與現實交融宣泄的鬼宴。基于席勒的美學思想,本文指出,最后的鬼宴其實是游戲沖動的重現,將極樂之宴的審美幻象與馬嵬驛的現實交織在一起,調和了二者之間的沖突,將二者有機統一,顯示出和諧與規則,讓三場宴的參與者彼此的愛恨情仇得到宣泄。
夢枕貘曾說:“如果有一個可以讓時間倒轉的機器,可以讓人在他最向往的地方停留一小時,那我選擇去大唐時代的長安參加一個特殊的宴會,里面有玄宗皇帝、楊貴妃、李白、杜甫。看楊貴妃起舞,聽李龜年伴奏,飲酒作詩。”這場盛宴隨后在陳凱歌的《妖貓傳》里得到逼真的展現,如夢如幻,如癡如醉。這場盛宴的主角,毫無疑問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而相傳在此宴會上李白所作的“應酬詩”,《清平調詞》則是對極樂之宴的最好的文字表達:“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這詞也是整本小說的引子,而另一首白居易的《長恨歌》則是小說的主線。小說中的幾位重要人物,也不時地在文中回味那場盛宴。如高力士信中所寫:“在明艷動人的貴妃身邊,享受宮廷無盡的榮華富貴,眺望大唐國所有的一切,那是一種無上的喜悅。如果可以再度回味那目的盛宴:李白作詩、李龜年吟唱、貴妃起舞……我愿意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樣的錯誤。……因為我確實目睹到了,即使普通人脫胎換骨一百次,也無法目睹到的光景啊。“又如不空大師所說:“那場宴會(卻)恍如一場美夢。那樣極盡人世奢華之美的世界,原本與我這樣的人相距遙遠。不過至今我還記得,當時我仍情不自禁心馳神蕩。若將那場宴會視為人間心力的流露,則可說跟密教并非絕對無緣了。”[1]席勒認為游戲是人的標志。他說:“表明野人進入人性的那個現象是什么現象呢?不管我們對歷史的探究深入到什么地步,這個現象在所有擺脫了動物狀態的奴役生活的民族都是一樣的;對假象的喜愛,對裝飾與游戲的愛好。”[2]席勒所說的假象,就是審美狀態下的觀賞對象。審美活動是游戲沖動的表現形式,人類通過審美才能是自身的感性與理性得到和諧統一,實現個體的自由。王國維認為席勒的審美游戲實際上是讓人完全擺脫了功利的目的的束縛,因此才獲得自由。他說:
希爾列爾(席勒)所著《人類美的教育之書牘集》(著于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審美教育書簡》,襲汗德(康德)之先例,而以游戲之動向,為美之所由產出者。其第十五篇有曰:“人惟以美為游戲者也。何則?以某義言,人類即-游戲,真面目之人類,惟能于游戲中見之耳。希氏之言如此。故其所謂”游戲“者,陳義至高,括意至宏。……“游戲”者何?謂現存生物,以某種狀態,而發表其不可抑遇之動向之一切活動也。又謂活動之專向于快樂之方面者也。[3]
在這場宴會中,參與的賓客皆無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抱著游戲的目的審美—美酒,美景與美人,感到了“無上的喜悅”和“心馳神蕩的美夢”,體會到了席勒認為審美游戲能達到的和諧。
全書所有的懸疑都是圍繞著馬嵬驛楊貴妃之死所展開。在夢枕貘的筆下,馬嵬驛不再只是歷史中的兵變之事,而是多方勢力角力的犧牲之宴。為了各自的目的,楊貴妃惟有一死才可以讓眾人的危機化解。楊貴妃,這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審美客體在被拋棄之后,留給眾人的只有形式上的沖動。席勒曾說:“分析功能占了上風,必定會奪走幻象的力與火,對象的范圍變得狹窄,必定會減少幻象的豐富性…務實的人常常有一顆狹隘的心,因為他們的想象力被關閉在他職業的單調的圈子里而不可能擴展到別人的意象方式之中。”[4]這一點在高力士的信中得到了體現:
若干年后,從墳中挖出貴妃時,假使貴妃一如往昔那般平安無事,皇上一定又會改變主意。他會說不愿意讓貴妃遠渡倭國。這么一來陳玄禮就會被捕,且慘遭斬首示眾吧。而陳玄禮也可能泄漏他和我之間的事。那么,我明知陳玄禮將在馬嵬驛兵變,卻沒稟告皇上,這秘密也將敗露出來。……對我而言,為了自保,讓貴妃就此身亡,那才是最好的。[5]
然而過分的理性沖動并沒有完全壓制感性,感性與理性的沖突變得不可調和。于是在馬嵬驛各自的形式沖動之后,也就引發了整本書的各種咒術災難。所有的恩怨在最后需要得到一個化解,夢枕貘就讓空海組織了最后一場盛宴—鬼宴。其中的“鬼”字其實是時間性的,意味著從前的一種復歸。只有游戲沖動才能調和感性和理性之間的沖突。于是空海就讓曾經的審美游戲—極樂之宴重新上演,試圖讓眾人通過往昔的審美幻象來宣泄消解彼此的恩怨。如何消解?通過共情,即感受對方的感受,理解彼此,認識到了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撫平感性和理性上的沖突,恢復和諧。正如高力士在信中所說:“人,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憐的生物啊。悲哀這東西,竟一視同仁地同時侵襲著黃鶴和我。再也不能說,誰對或誰錯了。任何人都錯,任何人也都對。所謂人,就是這么回事吧。”黃鶴與高力士分別時,流著淚說得“真是高興”與鬼宴終了的眾人慟哭,構成了悲劇的命運的合頌,而在這樣的合頌中,彼此也得到了宣泄與調和。不空的“因果之說”是最貼切的總結:“不論哪種法術,都不是超出天地法理之外的東西。……任何法術都必須依循因果法則。……先有了某事—某一行為,才會生出某一結果。這世間所發生的事,都是基于某處的‘因而滋生出來的。”[6]
參考文獻:
[1][5][6]夢枕貘,《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 林皎碧譯, 北京: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
[2][4]席勒, 《審美教育書簡》, 馮至、范大燦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王國維,《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