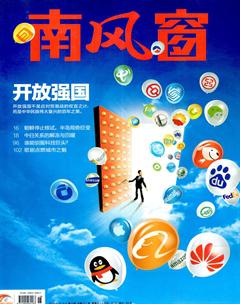“網絡”里的普米古寨
孫信茹 王東林

云南麗江古城西部的石鼓鎮,有漢、納西、普米等8個民族居民居住。
64歲的楊慧華與27歲的兒子和文會在村里開了一個小賣部。
說是小賣部,其實并沒有專門的店面和貨架擺放商品,只是在自家屋子的一角辟出一個小房間放了一些不多的商品。光顧小賣部的人可不是太多。
楊慧華的丈夫因病去世后,在外打過一陣短工的小兒子和文會回到了家里。家里還有一個女兒嫁到外地,另一個兒子在縣城工作。文會至今連女朋友也沒有,母親很擔心兒子的婚事:“大兒子和女兒都成家了,就只有我這個最疼的小兒子還沒結婚啊。”
文會卻沒有母親那么多的擔憂。一天的農活干下來,人已經疲憊不堪。他去年到香格里拉打過半年的工,可這經歷對他好像并沒有特別的吸引力。“現在手機、電視里什么都有,沒有必要再外出了。”
家里的WI-FI是去年花了440元開通的,就這樣,文會“沉浸”在自己的網絡世界里。
家里養了不少羊,“如果網絡的費用沒有了拉下兩頭羊去賣了,就又有錢去交網費了。”文會大笑著告訴我。因為養羊,他甚至做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未來,如果羊養到100多頭時,我就在羊的身上裝一個GPS定位。這樣羊去哪里就知道了。現在科技這么發達,人一個見不著一個,可以微信聊天。再想一想,為什么放羊不可以定位呢?”
文會是我重返大羊村之后認識的新朋友。因為研究需要,寒假,我帶著兩個博士生回到了闊別八年的調查點,一個地處云南滇西北的普米族鄉村。進村前,我設想過這個村落的種種變化。
記得八年前,住村半個月,一次澡也沒洗過。電視臺的朋友跟我說,根據他下鄉的經驗,村里一定今非昔比了,家家戶戶都會安裝太陽能的,你壓根不用擔心。讓我沒想到的是,走進大羊村地界的第一步,看到的第一眼,我恍惚覺得八年的時間都停滯了。一樣的村口大樹,一樣的村里小路,一樣的木楞房,還有一樣的房東大媽,唯一變化的就是大媽老了一些。
之后縣里駐村扶貧的干部曾問我,你覺得這些年大羊村有變化嗎?我想了很久,似乎無法圓滿地回答他。八年的時間,對于很多地方,尤其是處于高速巨變的城市而言,應該會有極大的變化,而大羊,仿佛被時間遺忘了。
安頓好住處,我開始走訪當年的老朋友,更急迫地想見到另一群特別的朋友。大約從兩年多前,我和村里的朋友們有了另一種交往的方式:微信。里面,有我的很多村民網友。
樹芬的期待
在大羊,我喜歡和那些年輕姑娘攀談。
樹芬就是這樣一個年輕女子。剛見到她時,她和幾個女人正在院子里聊天。我們湊過去,她主動和我們打招呼,邀請我們坐一坐。院子里,幾個孩子在追逐打鬧。她說,那個6、7歲樣子的小女孩是自己的孩子。
樹芬問我從哪里來,她說,當年也有一個云南大學的老師曾經到過這里做調查,那老師留著齊劉海的頭發。讓我沒想到的是。這些小細節讓我們的記憶彼此“喚醒”。樹芬竟然是當年我第一次到大羊的“舊識”。
那年,她是村里文藝隊成員,我們一起到鄉里參加過表演。這個發現,讓我們兩人都有些吃驚,不過,更多的是驚喜。“老師,你老了點啊。”我說是的啊,老了很多。其實,樹芬也老了不少,我壓根就沒有認出她。她告訴我,她還保留著當年文藝隊演出時我們的合影,并說等下回去就找找當年的照片。
樹芬33歲了,她和村里很多年輕姑娘有些不一樣,她從未到外面打過工,所以她并不是很愿意聽打工的朋友們說起外面的世界。“我聽了也去不了啊,就是白聽啊。”過了一會兒,樹芬又說:“其實自己內心很想聽的,但是知道聽了也沒有辦法出去。”說這話的時候,樹芬更多的是無奈。
樹芬的丈夫在鄉里當交警,家中照顧老人孩子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一個人操持。或許是無法出去的原因,樹芬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想象。“城里多好啊,和朋友唱歌、吃燒烤。最重要是沒有老人來管你。在農村就不可能了,總有人管。只要有錢,應該哪里都可以去了吧。”樹芬后來告訴我,她很渴望出去打打工,但她也反復強調,這樣的機會是不會輪到自己頭上的。
晚上,樹芬在自己的朋友圈發了一條微信:“七年不見的美女,今天見到我都差點認不出來了,我倆都老了。”配的照片正是我轉發給她的我們幾個人在草垛前的合影。她也真的找到了當年我們的合影,用微信發給了我。
成了微信好友后,我忍不住細細翻看樹芬的朋友圈。她是多愛發朋友圈的一個人啊:山野里、天地邊、火塘旁;洗頭、做飯、生病;村里姑娘的、自拍的……和那個“真實”生活的樹芬如此不一樣,卻又是如此真實、生動的樹芬。
我想起認識的另一個剛從昆明打工回來的女孩慶芳,初遇她時,她穿著粗陋的棉睡衣和我們聊天。翻到她QQ空間里的照片時,旅游時身著白色長裙的寫真照、穿著筆挺的工作制服的她,讓我一時無法把眼前這個姑娘和那些照片聯系起來。而她告訴我,后面也不打算出去打工了。我不知道,她的渴求,她對自我的期許又是些什么呢?
和樹芬的相遇,充滿了驚喜。而這些普米鄉村里的女性,她們的生活,早已離不開網絡了。
勇軍的“網絡空間”
最近村里有戶人家要結婚,勇軍在忙著挨家挨戶送請柬。勇軍和辦事人家并不是親戚,不過,自從兩年前初中畢業回到村里后,時常幫襯著村里完成大小公共事務。結婚送請柬、喪事上搭把手張羅、參加村里的大小培訓等等,勇軍很快成了村里的“熱門人物”。
其實,和我在村里第一次見面的勇軍,早已經是我在微信里結識兩年的朋友了。只是,他的微信名字總是不停地更換,害得我常常找不到他,譬如他最新的微信名字叫“喂!你別亂跑撞到我心上了”。
1993年出生的他,在微信上和在現實中有著極大的反差。如果光看他的微信,我會誤以為這是一個“無所事事”的鄉村“小混混”(不知道未來勇軍看到我這個表述時,他大概會大聲抗議吧?),還夾雜著一絲的“無病呻吟”。可是,當我結識了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勇軍,他黝黑、隨時洋溢的明朗的笑臉,熱情而又富有同情心,有些驕傲又謙和的做派,極好的人緣和交往能力,讓我無法不喜歡他。
勇軍加了不少信息平臺的微信好友。我很好奇,他為什么會對這些內容感興趣。勇軍告訴我,微信群里面有一些是因為自己做了村里的工程,認識的同事。他尤其喜歡關注信息平臺,譬如自己需要找工作或是交易物品時,就會通過“蘭坪微管家”和對方取得聯系。勇軍說,自己現在的車子,就是通過這個平臺找到的。
說起當時買車的情形,他說賣車的人是另一個鄉認識的一個叔叔,自己得知信息后,就花了1萬元多買了這輛已經用了4年多的二手車。他告訴我:“我還關注了一個保山的微平臺,有一次我做工程,沒想到出故障了,我就在這個平臺上找到了運輸車。”
勇軍喜歡玩全民K歌,歌喉也不錯,至今已經在里面發布了73首單曲。他應該最喜歡那首《美麗的普米姑娘吧》,當我們聚在火塘邊喝酒聊天時,他不止一次為我們播放并現場演唱過這首歌。
微信,在這里,提供給了人們另一種交往的“場景”和“空間”。
悄然“入場”的媒介
在大羊生活的日子里,我們遭遇了一場葬禮。于我而言,這場葬禮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對于即將要舉行葬禮的家人來說,這是無比悲傷的時刻,對于我們來說,卻意味著無比珍貴的觀察機遇。到大羊幾次,我從未看過給羊子(普米族葬禮中的傳統儀式,要殺羊祭祀),我知道給羊子在普米族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普米族葬禮中的給羊子和念誦的指路經,因其對民族歷史和祖先記憶的追溯,更有著深長的意蘊。
在整個葬禮儀式中,“媒介”悄然入場。
在葬禮的一些重要環節中,不少人用手機拍攝記錄全過程。出殯時,4、5個年輕人相伴我左右,跟我一同加入手機拍攝的隊伍。而在葬禮最后的祭三腳(普米族一種傳統儀式)中,一個大約50多歲的中年男人一直在用手機拍攝主持儀式的祭司,盡心盡力。原來,他很想學習這個過程。
葬禮中,主持儀式的祭司在上山出殯時發了兩條微信朋友圈;幾位為葬禮吹奏嗩吶的吹師也出現在了村民的朋友圈里;抬棺材的小伙子發的信息是“愿死者安息”。一個參加葬禮的大媽告訴我們,她不是這個村的,但是通過微信朋友圈知道了。他們,用自己的社交媒體,構筑起了傳統習俗和禮儀的另一個“文化空間”。
喜事也少不了網絡的介入。
我想起勇軍送請柬時,最后來不及送完,也用微信發給村民請柬。事實上,網絡已經進入到了這個傳統的鄉村生活中,甚至在改變著儀式的細節。
趙大林是村委會副主任,和村長、主任一樣,他在微信群里事兒不少。因為工作的關系,他們都加了不少群:村務通知群、扶貧攻堅群、村民小組群、普法工作群、河西(鄉)電子商務群、村干部群、提升城鄉人居環境群、政務、黨務工作群。不僅有工作群,而且還有自己的同學群、家人群。作為村里的政治精英,這樣的“入群”與信息聯絡。新媒體的確為他們提供了不少工作上的便利。在和趙大林聊天時,他的手機里響起的此起彼伏的各種提示音。讓我意識到,網絡已然進入鄉村政治生活中。
這個村莊,和我八年前來,沒有什么變化。但其實,它和八年前,截然不同。村民們在網絡里的“旅行”和自我展示.早已使得這個村莊不再是當年那個村莊了。網絡,給村民們提供了另一種體驗與想象的可能。或許,如有的學者所說,媒介和網絡的使用,不再是城鄉的差別,而是代際的差別。
村民們生活在網絡里,每個人的故事瑣碎,波瀾不驚,卻牽動我的心。
文會內心或許仍舊對外面的世界有不甘,最終還是只能選擇回家務農。不過,他在媒介中找到了另一個世界,在網絡里完成他“另一種生活空間”的想象和實踐。母子二人,終日艱辛勞作,卻能安然自得。
樹芬,讓我想起很多個自己在鄉村做研究時遇到的那些年輕女性,她用自己細膩和敏感的內心體驗去理解她心目中這個已然不再封閉的山村生活: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放下長發的自拍照;發布和我相遇的合影;三八節和村里姐妹們的聚會……社交媒體仿佛給了她另一種“書寫”自己的可能。
然而,真實的現實卻是:外面的世界跟自己沒有太多關系,無法出去,很多機會是輪不到自己頭上等等。她些許的失落和無奈在我們的交談中隨時都流溢而出。
當然,不能說,互聯網究竟給這個村莊帶來什么本質的變化。就像那個在村委會掛起的電商牌子,事實上要真正投入去使用,何其艱難,互聯網的影響也非一朝一夕就能看到的。然而。對于今天這個普米鄉村來說,網絡已經成了村民們的生活方式。就像老人們都會說起的那個“段子”,一個村里年輕女孩玩手機的故事:這個年輕人邊做飯邊玩手機,最后,因為手機玩得太入迷,結果飯都燒糊了。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