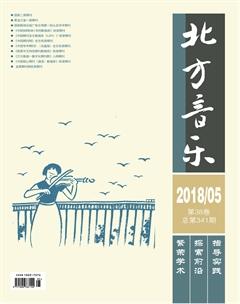古樂器“筑”研究綜述
徐文鳴
【摘要】“筑”是一件在戰國至漢代時期十分流行的樂器。從《戰國策·齊策》“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可見其在戰國時期已得到了普及;《漢書·高祖本紀》“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中也可見統治階級對其的喜愛。但漢代以后,史書中關于筑的記載大大減少,這件紅極一時的樂器自此銷聲匿跡。本文從“筑”的形制、演奏方式上對目前筑的研究做一個綜述。
【關鍵詞】古樂器;“筑”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提到樂器“筑”,很多人都一臉茫然,筆者也不曾例外。在未接觸到漢代音樂尤其是漢代樂器的研究時,筆者對于“筑”這個字的理解僅僅停留在 “建筑、修造”的意思上。一次偶然的機會,筆者了解到漢高祖劉邦的故里——江蘇省徐州市沛縣,一位老人復原出了這件已經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樂器。當看到復原“筑”的實物時,覺得其像縮小版的箏。筆者自幼習箏,因此對“筑”這件樂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此開始了對這件古樂器的研究。
縱觀古籍中對“筑”的記載和今人的研究,對“筑”的主要關注點表現在幾個方面:1.形制;2.演奏方式; 3.弦數;4.音樂表現力。
一、有關筑的形制的綜述
漢代,古文獻中關于“筑”的描述多了起來,在《史記·荊軻傳》《漢書》《后漢書》《釋名》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形制上,劉熙在《釋名·釋樂器》中認為筑似箏;《漢書·高帝紀注》中說筑似瑟;《史記·刺客列傳》中確認為筑似琴。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筑的文獻驟然減少,這一時期并未找到對筑的形制的描述。至于隋唐,對筑的形制的描寫有所增加。《隋書·音樂志》認為筑有十二弦;《舊唐書·音樂志》中說筑如箏。到了宋代,相關文獻就更加稀少,只在《宋史·音樂志》和陳旸《樂書》中出現過。陳旸《樂書》中寫筑似箏,細頸。
今人對筑的形制也爭執不休。寫筑的形制的文獻有:岳巖的《瑟筑》;柳羽的《考筑》;項陽的《筑及相關樂器辨析 》《從筑到箏》《五弦筑研究—西漢長沙王后墓出土樂器研究之一》《五弦筑的碼子,弓子及其他相關問題》;黃翔鵬的《秦漢相和樂器“筑”的首次發現及其意義》; 楊和平的《古樂器筑研究綜述》;馮潔軒的《中國最早的拉弦樂器“筑”考》;徐忠奎的《古代樂器筑的形制研究綜述》。這幾篇文章都結合了出土文物和古籍,把各種形制不同的筑做了分類。學者項陽首先提出筑在形制上分為楚筑、越筑、北方筑之說。楚筑以馬王堆漢墓中的墓畫《怪神擊筑圖》為代表,其有五弦,呈四梭長棒狀,大頭細頸,像現在鄉村中所常用的搗衣棒,共鳴箱較小;越筑以紹興306號墓中的筑的明器為代表,其形制似箏,共鳴腔體較大;北方筑以南陽為代表,這種筑似琴,一頭較細,另一頭粗圓些,較長大,因此,共鳴腔也較大。
二、有關筑的演奏方式的綜述
漢人在筑的演奏方式上,劉熙的《釋名·釋樂器》和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都有提及,所持觀點都是筑是擊弦演奏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筑的文獻雖少,齊高帝《塞客吟》、徐陵《漢高帝廟詩》、陶潛《詠荊軻》《劉子·辯樂篇》中也都提及筑是擊弦樂器。隋唐時期,《隋書·音樂志》《舊唐書·音樂志》也都認為筑“以竹鼓之”。至于宋代,《宋史·音樂志》和陳旸《樂書》中也都認為筑是用竹棍擊弦演奏的。古人對于筑的演奏方式空前的統一,都認為筑是一種擊弦演奏樂器。
今人寫筑的演奏方式的文獻有:岳巖的《瑟筑》;柳羽的《考筑》;項陽的《筑及相關樂器辨析 》《從筑到箏》《五弦筑研究—西漢長沙王后墓出土樂器研究之一》;楊和平的《古樂器筑研究綜述》;馮潔軒的《中國最早的拉弦樂器“筑”考》;徐忠奎《古代樂器筑的形制研究綜述》。從文章中可以看出,學者們目前認為筑有三種不同的演奏方式:1.演奏者一手持筑頸,一手執竹尺(竹片、竹弓)擊弦,筑的一頭著地,演奏時筑身與地面有不大的夾角;2.演奏者將筑近似豎抱,演奏時一只手握住筑體,或者底端,另一端斜靠在肩頭,一只手執竹片等器物擊弦;3.演奏者將筑近乎平放在身前,演奏時一只手按弦,一只手拿竹片擊弦而發音。
學者項陽在他的《從筑到箏》《筑及相關樂器辨析》《軋箏考》《化石樂器挫琴的啟示》幾篇文章中,多次提出筑是我國弓弦樂器的先驅的說法。他認為:“筑由于自身形制較小,弦數較少,以至于后來不能滿足音樂表現的需求,所以慢慢被其他樂器所取代。”由擊弦變成拉弦演奏的軋箏就是由筑演變而來的,進而產生“筑族樂器”說。嬗變出的軋箏影響了后世奚琴、胡琴等弓弦樂器的發展。因此,筑是弓弦樂器的鼻祖。
從綜述可以清晰地看出,筑在先秦至漢代時期的發展比較興盛,文獻記載也比較多,漢代以后,文獻數量急劇下降,今人文獻中也鮮有關注其在漢后的發展。從先秦到漢末,筑這件樂器只流傳了一千多年,便銷聲匿跡,它留下了太多的謎團,等待我們去探索與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