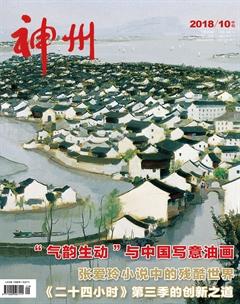張愛玲小說中的殘酷世界
韓靖超
摘要:張愛玲筆下的殘酷世界——塵世的喧囂煩擾、生命的瑣屑卑微、生存的慘傷無奈、命運的不可理喻,凝聚成層層疊疊法挫敗感、失落感、荒誕感、蒼涼感,無所不在地籠罩著她作品中的每一個故事和每一個人物。筆者以張愛玲長篇小說《半生緣》和中篇小說集《傳奇》為研究對象,從母愛的謊言、父權的虛偽和愛情的荒蕪三方面來淺談張愛玲小說中的殘酷世界。
關鍵詞:張愛玲;殘酷;愛;缺失
在文藝理論范疇中,悲劇作為一種最高藝術形式,專注于表現人類的痛苦、災難與不幸。所謂悲劇意識,是人經由對自身悲涼處境的深沉思考而生成的對生命悲劇性的體驗與認知。人的欲望本能與生存困境的悲劇性沖突,是生成悲劇意識的淵源,屬于無可逃脫的永恒劫數。張愛玲小說著重表現的便是這種永恒的人生悲劇性,講述現代人如何在黑暗中墜落毀滅,用殘忍冷酷的筆調展現一個暗淡無光的世界。
一、母愛的謊言
長久以來,母親一直以溫柔、善良、慈愛的形象出現,母愛也被賦予理想與神圣的光環,然而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則顛覆了傳統的母愛神話,向讀者展示了母愛的虛幻與女性命運的困窘悲涼。張愛玲作品往往是描寫令人失望母女關系,例如《傾城之戀》中女主角白流蘇在受到兄嫂排擠后希望母親為她做主時,母親卻站在兄嫂這一邊要女兒回離婚的婆家做寡婦,這使流蘇失望地意識到“她所祈求的母親與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短篇小說《花調》中鄭川娥的母親為了不在丈夫面前暴露自己的私房錢,“鄭夫人忖度著”最終沒有拿出錢來給女兒買藥。
張愛玲說過:“極端病態和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我的小說里,除了《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這位曹七巧就是一位徹底瘋狂變態的母親。曹七巧在夫家備受歧視與排擠,自小癱瘓的丈夫更使其飽受情愛壓抑的痛苦,加上舊式大家庭勾心斗角的熏染,曹七巧早已心理扭曲變態,被黃金枷鎖緊緊套住,了無親情,殘忍惡毒。她自己得不到愛,也不允許別人得到幸福,即使是自己的親身骨肉。她對兒子放任自流,逛窯子、捧戲子、抽大煙,逼死兒媳婦;而對于女兒則是更殘忍的報復與控制,強迫女兒在裹腳,因為一條床單逼著女兒退學。女兒長安“漸漸放棄了一切上進的思想”,終于,“她的言談舉止越來越像她母親了”,成為一棵“鹽腌過的雪里紅”。她狀似無意地對女兒意中人說:“她再抽兩筒就下來了。”這樣不動聲色的文字卻產生驚心動魄的效果,作為母親的七巧不僅對自己的女兒沒有一絲愛護,反而用陰謀斷送了女兒的終身幸福,這便是一個淬著毒汁的母親形象。以至于長安最終“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二、父權的虛偽
自古以來,文化標榜的父親形象是堅強、剛毅、偉岸,是家庭與社會的支柱,然而張愛玲筆下的父親卻無不暴露虛偽與脆弱的的本質。《琉璃瓦》中姚先生把他美麗的女兒們比作“琉璃瓦”,對于女兒們的前途有“極周到的計劃”。小說在開篇就寫道“要他靠女兒吃飯,他卻不是那種人”,與之后姚先生的做法形成巨大的諷刺。姚先生把長女嫁給自己所在印刷廠大股東的獨生子,卻在女兒哭訴丈夫有外遇時不聞不問;把次女推薦到機關做女秘書,卻在女兒與“一個三等書記”過從甚密時冷言冷語;給三女物色了杭州富家青年相貌丑陋,卻在女兒自由戀愛時破口大罵父親與子女的關系已經不是靠親情而是靠利益手段來維持了,血緣之愛蕩然無存。
在《茉莉香片》中,聶傳慶家中“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陽光曬著,滿眼的荒涼。”“他父親聶介臣,汗衫外面罩著一件油漬斑斑的雪青軟緞小背心,他后母蓬著頭,一身黑,面對面躺在煙鋪上。”在這所陰森大宅里的男主人公聶傳慶是個精神抑郁、性格孤僻的人,“已經被作踐得不像人”。傳慶生在聶家悲哀、壓抑,可他別無選擇,像他母親一樣成為一只繡在屏風上的鳥,“打死他也不能飛下屏風去”。“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給蟲蛀了,死還是死在屏風上。”聶家父子的關系幾近仇敵了,傳慶被他父親制造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殘廢,面對父母、同學及一切現實中的人,他都感到自卑渺小,整日自怨自艾。對現實與父親的憎恨,讓他幻想言教授曾經可能成為自己的父親,讓他嫉妒陽光善良的言教授女兒,而當這一切破碎時他走向萬劫不復。
三、愛情的荒蕪
愛情是文學作品永恒的主題,也是無數美好情感的代表,但張愛玲卻往往從兩性關系、婚姻關系中來發掘人性的自私、虛偽、殘忍與卑鄙。
初看《傾城之戀》這個題目,我誤以為這是一篇哀婉纏綿、浪漫詩意的愛情故事,讀后才發現文本實則充斥著無聊的高級調情與極盡心計的男女進退攻守。白流蘇對于范柳原的真心從一開始就是不相信的,不過是為了擺脫她那齷齪不堪的家庭,期望通過范柳原這個華僑富商、人們眼中的“標準夫婿”來做自己的救命稻草,不愿付出真心卻想求一個太太的頭銜。到香港后,范柳原整日與白流蘇廝混在一起,他不過是需要“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來成為自己的情婦,范柳原對她忽冷忽熱,時而激將時而壓迫,甚至讓白流蘇回到上海承受家庭的壓力再乖乖回到自己身邊心甘情愿地做情婦。“然而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盤打得太仔細了,始終不肯冒失。”《傾城之戀》是張愛玲筆下唯一一部有較圓滿結局的愛情故事,但若不是香港淪陷,這注定是一場愛情“宮心計”里的悲劇,“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城市傾覆了。”
張愛玲描寫了上海與香港都市男女千瘡百孔的愛情,在她的筆下是一群迫于生計尋找婚姻而沒有愛情的女人。《心經》中段綾卿說:“任何人……當然這‘人字是代表某一階級與年齡范圍內的未婚者……在這范圍內,我是‘人盡可夫的!”一語道出女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過活的現實,這話已然夠可憐可悲,但更諷刺的是最終段綾卿竟還是依靠了一個不適齡且已婚的男人。女人們為了生存而結婚,為了結婚而奔忙,做“女結婚員”是她們唯一的出路,她們在男權社會只能依附男人生存,于是婚姻就成了這依附關系的一紙合同。張愛玲借著范柳原之口道出了婚姻的本質——“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
在這樣沒有父慈母愛與甜蜜愛情的故事中,文中人物更鮮少有那種親切溫暖、積極向上的存在,殘酷感充斥作品的每一個角落;但悲劇的價值在于使人領會到邁克爾·伍德所說的“小說描寫的也許是黑暗的世界,但讓讀者留在光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