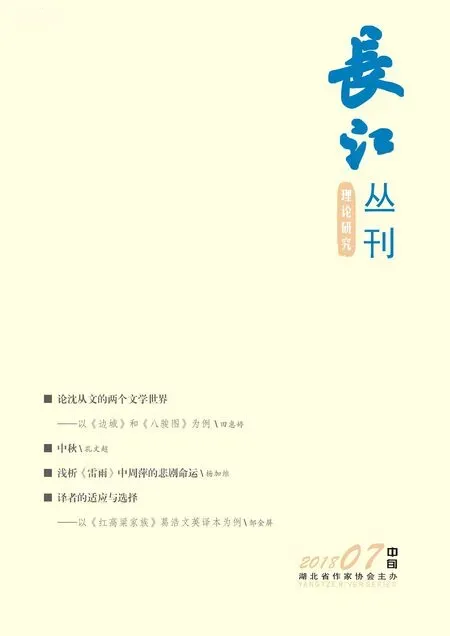一部跨體越界的小說佳作
——讀普玄《疼痛吧指頭》
■
一
普玄以前算是我的學生。他在華中師范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已在這所學校當老師了。然而現在,當我讀了他的長篇新作《疼痛吧指頭》之后,我覺得他已經成了我的老師。就這部長篇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我都要向普玄學習,當他的學生。我的這番話皆發自內心深處,如有半句戲言,吃魚卡刺,喝水塞牙,樹葉落在頭上砸個包。
坦率地講,剛收到這部作品時,我并沒有打算將它從頭到尾讀完。因為書名中帶一個吧字,過于時尚,不是我喜歡的類型。但是,當我讀了開頭一節之后,我便停不下來了,想停都停不下來。沒有辦法,我只好一股腦把它讀完,連吃午飯都手不釋卷。老實說,我已經很久沒這樣認真、這樣仔細、這樣用心地讀一部作品了。我是一個字一個字讀的,連標點都沒放過,有些句子和片斷還讀了好幾遍。在閱讀過程中,我的情緒一直處于亢奮狀態,有驚奇,有疑惑,有緊張,有焦慮,有崇敬,有欽佩,有感嘆,有唏噓,有激動,有不安,有悲憫,有同情,有憂傷,有郁悶,有苦澀,有辛酸……當然,更多的是疼痛。讀罷全篇,我的整個身心都被撼動了,仿佛四肢散架,肝膽裂縫,靈魂搖晃。掩卷沉思的那個晚上,我的心情久久無法平靜。直覺告訴我,普玄寫出了一部大書。我感覺到,這既是一部生活之書,又是一部生存之書,更是一部生命之書。
作為一個和文學打了三十幾年交道的人,由于曠日持久的閱讀,我對文學作品已經產生了輕度的審美疲勞,同時也滋生了一種愛挑剔的毛病。尤其在當下這個集體浮躁的文壇,精品意識日益淡薄,大部分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粗制濫糙,讓我口服心服的佳作可以說寥若晨星。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普玄的《疼痛吧指頭》卻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它像一頭被作者施以了什么魔法的魔鬼,魔力四射,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讓我欲罷不能,進而又感染了我,震撼了我,征服了我。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部無可挑剔的佳作。
二
關于佳作,每個讀者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標準。我認為的佳作,必須具備三個因素,一是真實感,二是沖擊力,三是可讀性。這個標準涉及到文學的三個維度,真實感是生活層面的要求,沖擊力是藝術層面的要求,可讀性是思想層面的要求。我之所以說《疼痛吧指頭》是一部佳作,正是因為它既有足夠的真實感,又有強烈的沖擊力,還有巨大的可讀性。也就是說,佳作所要求的三個必備因素,在普玄這部作品中應有盡有,并且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盡管人們看取佳作的標準不盡相同,但真正的佳作還是能夠引起廣泛認同的。據我所知,《疼痛吧指頭》在《收獲》長篇小說專號上甫一發表,便引起文壇特別關注,反響熱烈,好評如潮。不久,長江文藝出版社就將其出了單行本。緊隨其后,便是接二連三的見面會、分享會和報告會。各種媒體上有關這部作品的報道和評論,更是連篇累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報道和評論所講的,主要都集中在這部作品的真實感上面,對它的沖擊力和可讀性卻惜墨如金,甚至避而不談。究其原因,恐怕與評論界和新聞界對這部作品的文體定性有關。我發現,在評價和推介這部作品的時候,無論評論還是報道,首先都不約而同地給它貼上了一個非虛構的標簽。事實上,普玄自己也是這么限定的。我想,正是因為把它當成了一部非虛構作品,人們才有意或無意忽視了對其沖擊力和可讀性的全面研究和深入探討。
然而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事先給《疼痛吧指頭》貼上非虛構的標簽。雖然這個標簽很時尚、很流行、很受追捧,但將它貼在這部作品上很不恰當,或者說很不般配。我的意思是說,與這部作品的容量、意蘊、價值相比,非虛構這個標簽顯得太窄、太輕、太淺,不僅不能充分發現普玄這部作品給當下的文學現場帶來的異質和新意,反而還縮小了它的容量,減少了它的意蘊,降低了它的價值。我則認為,《疼痛吧指頭》是一部跨體越界的小說。所謂跨體,指的是跨越文學作品的各種體裁,即在小說中有機地挪用散文、詩歌、戲劇、影視、報告文學等各種體裁的藝術優勢;所謂越界,指的是跨越人文科學的各種界別,即在文學中適當地融進新聞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家族歷史學等各種界別的社會功能。普玄的這部作品,對小說寫作的跨體與越界進行了多向度的探索和全方位的嘗試,從而有效增添了小說的真實感,加強了小說的沖擊力,擴大了小說的可讀性。從文學創新的角度來說,這也正是《疼痛吧指頭》對小說創作做出的一個最大貢獻。
三
真實感是文學的生命之源,對小說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從生活與文學的關系來看,文學的真實感與生活的真實卻不是一回事。在很多時候,生活中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被作家直接搬進作品后并不一定具有真實感。原因在于,真實感不僅要求事件真實,還要求情感真實,更要求本質真實。對于這一點,普玄肯定是心知肚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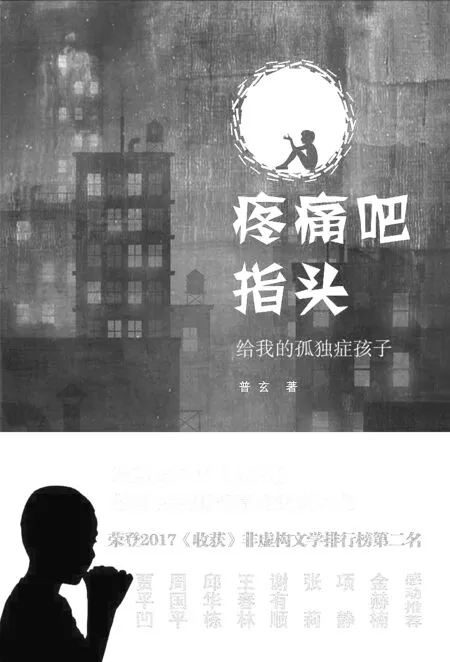
《疼痛吧指頭》
《疼痛吧指頭》所寫的事件,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事件真實顯然毋庸置疑。為了追求事件真實,作者還特意借鑒了新聞的寫法,比如對孤獨癥兒子失蹤的敘述,所采用的完全是新聞寫作中常見的事件追蹤形式,從一開始自己在周邊尋找,到登貼尋人啟事,再到懸賞,再到等消息,直到最后警察幫助找到兒子,其中每一個人物,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都真實可信。
但是,普玄并沒有停留于事件真實。作為一個優秀的作家,他知道情感真實對文學更為重要。因此,他便在敘述過程中不斷地從新聞視界跳回到文學視界,對事件的敘述也隨之由新聞筆法轉換為文學筆法。比如寫到等待失蹤兒子的消息時,作品中是這樣寫的:“丟孩子的人就是這么一點一點枯焦的。一個電話來,興奮,失望,又一個電話來,興奮,失望。一個電話來了,一個短信來了,孩子?男孩女孩?多高?在哪里?長什么樣子?眼睛多大?穿什么衣服?對了,指頭,最關鍵的,指頭被咬過沒有?”顯而易見,這段文字里充滿了文學修辭,有比喻,有反復,有張有弛,有詳有略,有快速的掃描,有緩慢的特寫……這些修辭在新聞里一般都十分罕見。特別是后面的問答,為了強化情感真實,作者毫不猶豫地將信息提供者的回答全部隱去,只保留了孩子父親一句趕一句的問話。正是由于文學修辭的強大力量,一個在孤獨癥兒子失蹤之后心急如焚、坐立不安、茫然無措的父親形象便躍然紙上,讓讀者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十指連心,什么叫血濃于水,什么叫骨肉深情。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在確保了這部作品的情感真實之后,普玄仍未止步。他突然在作品的第二部分變換了敘事人稱和敘事視角,人稱由第一人稱“我”變成了第三人稱“他”,視角也由孤獨癥孩子的爸爸換成了孩子的奶奶。這個變化不可小覷。它一下子把這部作品和所謂的非虛構拉開了距離,同時也暴露了作者的寫作野心。很顯然,普玄不滿足于只像非虛構作品那樣就事論事,而是希望對自己的經歷和體驗進行挖掘、拓展、放大、引申、提煉,進而去觸碰和窺探生活的某些真諦,或曰本質真實。值得欣喜的是,普玄的這個目的達到了。由于奶奶的人生更加坎坷,經驗更加豐富,視野更加開闊,作品中的殘疾人物很快便由一個增加到三個。除了原來不能說話的孤獨癥孫子,還出現了半聾半啞的老大和跛腳歪腿的爺爺。他們雖然輩份年齡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致殘原因不同,但卻有著相同的身份,即殘疾人。三個殘疾人構成了一個特殊的人物世界,同時也鑄造了一面人性的多棱鏡,清晰地照射出了各色人等和世道人心,讓我們看到了逃避與承受、放棄與堅持、絕望與生機,也看到了真假對峙、善惡較量和美丑博弈,更看到了屹立在弱者背后的那些強者,比如奶奶常五姐,比如孤獨癥孩子的爸爸,他們的強者精神、強者意志、強者性格,足以戰勝一切邪惡,克服一切苦難,驅趕一切不幸。
四
沖擊力是文學的藝術體現,在小說領域被稱為藝術張力。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活的改觀、文化的轉型,讀者對文學尤其是小說的訴求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可以說越來越多元,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吊詭,越來越刁鉆。為了滿足讀者日益上漲的閱讀訴求,作家們不得不及時反思、調整、更新自己的表達形式。
普玄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寫小說,卻不想在小說這棵樹上吊死,也沒有靜坐在小說之樹下守珠待兔。他深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于是趕了一個時髦,為自己的小說創作找了一個非虛構的幌子。其實,非虛構并非一種新鮮文體,說白了也就是早已有之的報告文學。不過,讀者都有一種喜新厭舊的心理,好比吃膩了土豆的人突然遇上了一盤馬鈴薯,感覺味道好極了,沒曾想馬鈴薯就是土豆。我以為,正是為了配合讀者的這種閱讀心理,普玄才放下身架借用了非虛構這一相對單純而容易操作的文體。當然,《疼痛吧指頭》也確實充滿了非虛構的元素,比如圍繞孤獨癥孩子所發生的一切,包括從最初患病到最終確診,從四處求醫到百般救治,從不幸失蹤到僥幸找回,從自家看護到他處寄養……這一系列的關鍵事件,都是用非虛構即報告文學常用的紀實形式呈現出來的。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部作品運用了較多的紀實形式就把它當成一個非虛構文本。不能否認,無論從作品的框架還是從作品的血肉來看,它都是一部典型的小說。比如在敘事秩序上,它運用了交互式結構。這種敘事結構只有小說中常用,在非虛構作品里是難得見到的。又比如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這部作品為我們刻畫了奶奶、爺爺、老大等多個血肉豐滿、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這樣的人物形象,也只有在小說中才能塑造出來,在非虛構作品里是不可能出現的。普玄之所以要在這部作品中大量運用非虛構的紀實手法,其目的只是為了增強小說的可信度,從而加大它的藝術沖擊力。
因為同樣的目的,普玄在這部作品中還借用了許多其他文體的表現形式。比如,作品寫到奶奶在半聾半啞的大兒子因挨斗下跪而失蹤后的反應時,作者馬上進行了時空切換,由大兒子的失蹤一下子寫到了孤獨癥孫子的失蹤。雖然失蹤的一個是兒子,一個是孫子,但奶奶在他們失蹤后的反應卻如出一轍。“她每天都不吃飯,她一定要等到大兒子出現。……幾十年以后,奶奶到省城給三兒子帶孤獨癥孫子,早上買早餐的時候,孫子跑丟了。奶奶很害怕很自責。她自責的辦法就是不吃飯。她要等到孫子出現再吃飯。”在這里,普玄明顯運用了電影中慣用的蒙太奇藝術,將發生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空間的事件,通過某些相似性因素而巧妙地剪輯到一起,對讀者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
又比如,孤獨癥孫子被奶奶接回老家之后,兒子放心不下,無法安心工作,三天兩頭跑去看。有一個雨天,兒子又來了,奶奶卻死活不開門。于是,門里門外便發生了一大段對話。“奶奶說,你又來干什么?兒子說,我看一眼就走。奶奶說,你擔心我還是擔心你兒子?兒子說,我主要擔心你。奶奶說,你媽有那么嬌嫩嗎?兒子說,我只是有點擔心。奶奶說,你認為我老了?兒子在門外默不作聲。奶奶說,我是老了,我有點經不起摔了,我老得連一個小孫子都弄不動了。”這段對話顯然借鑒了戲劇的對白藝術,每一句對話中都蘊含著豐富的潛臺詞,把母子兩人微妙而復雜的內心世界表現得淋漓盡致。我讀著這些對話,不禁心潮洶涌,熱淚盈眶,其沖擊力可見一斑。
還比如,爸爸在臘月三十連夜開車送孤獨癥兒子去奶奶家過年,路上突然遭遇大霧,作者這時運用了一段靜述:“濃霧一朵一朵落。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么漂亮的霧。濃霧好像不是從空中飄出來的,而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在江漢平原,在大洪山地區的冬季,地里面除了長糧食長蔬菜長花朵,怎么還長出一朵一朵濃濃的霧。這不是霧。這是美麗的云朵,飄動的漫畫,環繞的紗幔,輕柔的微風。這是另一個世界的迷人的香水。”這一段關于大霧的描寫,分明用了詩歌的修辭藝術,其中有比喻,有象征,有神奇的想象,有微妙的通感,對讀者具有強烈的沖擊力。
五
可讀性是文學的魅力所在,對小說來講尤其重要。小說的可讀性,看似簡單、淺顯,實則復雜、深奧。不過,我們不能把可讀性狹隘地等同于通俗性、故事性和傳奇性。這些只意味著好讀,即淺近、易懂、有趣、好看。但是,好讀并不完全等于可讀,它只是可讀性的一個方面。可讀性的另一個方面還要求耐讀,即耐人尋味、發人深省、常讀常新、百讀不厭。它要求文本必須具有較大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為讀者提供更多的參與意義建構的可能。按我的理解,小說的可讀性至少由三個層面構成:一是給讀者初次閱讀帶來的吸引力和興奮感;二是潛藏于文本深處的那種對讀者持久的誘惑力,即那些能夠激發讀者再次閱讀興趣和反復閱讀欲望的因素;三是文本暗含的可供不同讀者進行多種解讀的空間。
從上述標準來看,《疼痛吧指頭》無疑是一部極具可讀性的小說。它不僅好讀,而且耐讀。不過,我在這里不想去談它好讀的一面,因為這一面十分顯著。我只想從主題的角度出發,去分析一下這部作品耐讀的一面。主題是作品的深層意蘊,也被稱為作品的思想內涵。我明顯感覺到,普玄這部作品的主題是豐富的,是開放的,是多元的,具有廣闊的意蘊空間,可供不同身份、不同處境、不同訴求的讀者進行各自不同的解讀,甚至同一個讀者也可以讀出多個主題來。正因為如此,它擁有了耐讀的品質。
比如貫穿作品始終的“指頭”,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解讀。從生活的層面來說,指頭只是一種現象。孤獨癥孩子有一個習慣性、典型性、標志性動作,即咬自己的指頭。“這個不會說話的孩子十幾年來一直和他的指頭過不去,他的指頭上全是他自己撕咬的疤痕,他一著急一發怒就開始咬指頭。”可見,指頭在這里只是一種現象,雖說有點奇怪,但并無深意。再從文學的層面來說,指頭便成了一種意象。因為十指連心,父母大人便把孩子看成了自己的指頭。“這五個孩子,就是奶奶的五根指頭。其中奶奶寄希望最大也是最恨的,就是門外的第三根指頭,孤獨癥孩子的爸爸。”在這里,指頭已超越了它的本義,通過比喻和象征業已變成了內涵深厚的文學意象。如果從哲學層面來說,作品中有幾處關于指頭的描寫已經上升為一種寓象。其中有一處這么寫道:“很多事情,你只能由著它。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兒子要不聽話,孫子要咬指頭。”這里提到的指頭,不僅超越了生活,而且超越了文學,然后變成了一個寓象,擁有了廣泛而普遍的哲理意義。
再比如作品中的這個孤獨癥孩子,他在作者多角度、多側面、多視野的描述中也顯示出了多重意義。一方面,他是爸爸的一塊心病、一個負擔、一份疼痛;另一方面,他又是爸爸的某種寄托、某種神靈、某種福音。作品中有這樣一段十分精辟的議論:“我忽然明白,這根讓我疼痛讓我無奈讓我絕望的指頭,它一定會救我,帶我到另一個地方。這么多年來,就是它,我的指頭,我的孩子,它總是在我絕望的時候,在我無路可走的時候搭救我。”這番議論既有詩意,又有哲理,充滿了生活的辯證法,給讀者創造了多元解讀的空間,從而有效擴大了作品的可讀性。
上面寫了這么多,總而言之一句話:普玄的《疼痛吧指頭》是一部跨體越界的小說佳作。無論作為他從前的老師,還是作為他現在的學生,我都要向普玄表示衷心的祝賀。

曉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生于湖北保康,現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先后在《人民文學》《收獲》《花城》《作家》《鐘山》《天涯》等刊發表小說近500萬字。曾獲首屆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說獎、第二屆林斤瀾小說獎、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第五屆汪曾祺文學獎、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湖北文學獎。《花被窩》《酒瘋子》《三個乞丐》分別進入2011、2013、2015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