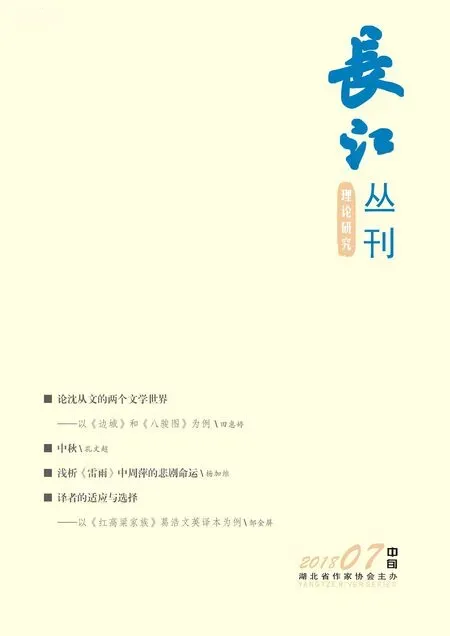詩(shī)之越境與越境之詩(shī)
——1920年代中國(guó)新詩(shī)在日本
■
在世界范圍內(nèi),沒(méi)有哪個(gè)國(guó)家像日本一樣從中國(guó)新詩(shī)誕生之初就對(duì)其表示出密切的關(guān)注。尤其是1949年以前,日本對(duì)中國(guó)新詩(shī)的譯介與接受過(guò)程顯示出極強(qiáng)的連續(xù)性、動(dòng)態(tài)性與同步性。迄今為止,對(duì)于“中國(guó)新詩(shī)與日本”這一課題,中日兩國(guó)學(xué)者已進(jìn)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其成就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以及中日比較文學(xué)研究中占據(jù)重要位置。而既有成果置重的是從“日本體驗(yàn)/日本因素”這樣的視角出發(fā),探討日本文化與近現(xiàn)代文學(xué)思潮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壇的發(fā)生、發(fā)展所產(chǎn)生的影響。然而,對(duì)于同時(shí)代的日本詩(shī)壇是如何譯介和接受中國(guó)新詩(shī)這一問(wèn)題,卻缺乏從譯介學(xué)的視角來(lái)考察其作品——何時(shí)?被誰(shuí)?經(jīng)由什么途徑?借助何種媒介?——譯介到日本的專(zhuān)門(mén)性考證和研究。這源于較長(zhǎng)一段時(shí)期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文學(xué)翻譯的認(rèn)知大多停留在一個(gè)語(yǔ)言符號(hào)轉(zhuǎn)換的技術(shù)性層面,并未對(duì)翻譯文學(xué)作為獨(dú)立文學(xué)形式之一種的審美價(jià)值、及其作為異文化(文學(xué))交流的中介價(jià)值給予足夠的認(rèn)識(shí)。然而,文學(xué)翻譯這一通過(guò)語(yǔ)言文字的轉(zhuǎn)換把原作引入到一個(gè)全新文化圈的行為本身,不僅僅只是文學(xué)作品的一種跨文化傳播樣態(tài),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學(xué)再生的創(chuàng)作形式。
具體就“中國(guó)新詩(shī)在日本”這一話(huà)題而言,1920年代活躍在日本詩(shī)壇的中國(guó)詩(shī)人黃瀛(1906~2005),就曾將以創(chuàng)造社為代表的同時(shí)代中國(guó)詩(shī)人的作品,翻譯成日語(yǔ)在《詩(shī)與詩(shī)論》等日本詩(shī)歌雜志上進(jìn)行發(fā)表。此外,還撰寫(xiě)了《中國(guó)詩(shī)壇的現(xiàn)在》(1928)、《中國(guó)詩(shī)壇小述》(1929)等理論文章向日本詩(shī)壇介紹中國(guó)新詩(shī)發(fā)展的最新?tīng)顩r。這一系列的翻譯和詩(shī)評(píng)活動(dòng),不僅有助于中國(guó)新詩(shī)在日本的介紹與傳播,也能提供一種域外視角幫助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原作之價(jià)值。正如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埃斯卡皮所言:“翻譯把作品置于一個(gè)完全沒(méi)有預(yù)料到的參照體系里”,“賦予作品一個(gè)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jìn)行一次嶄新的文學(xué)交流”,“它不僅延長(zhǎng)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本文聚焦于中日詩(shī)歌交流頻繁而集中的1920年代,通過(guò)對(duì)這位極具代表性的中日詩(shī)壇“越境者”黃瀛對(duì)中國(guó)新詩(shī)譯介情況的梳理和勾勒,簡(jiǎn)要探討1920年代中國(guó)新詩(shī)與同時(shí)期日本詩(shī)壇何以能夠產(chǎn)生共震的“接點(diǎn)”,揭示一段被埋沒(méi)的中日詩(shī)歌交流史話(huà)。
一、譯者:國(guó)籍/語(yǔ)言的“混血”
日本著名漢學(xué)家?jiàn)W野幸太郎曾經(jīng)在《黃瀛詩(shī)集跋》中談及黃瀛及其詩(shī)歌的文學(xué)價(jià)值時(shí)指出:“作為一個(gè)深諳日語(yǔ)之神秘的中國(guó)詩(shī)人,黃君理應(yīng)受到中國(guó)詩(shī)壇的尊重。”“深諳日語(yǔ)的中國(guó)詩(shī)人”這一稱(chēng)謂恰恰象征了黃瀛在日本詩(shī)壇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則首先體現(xiàn)在其出身的特殊性上。
黃瀛,1906年出生于重慶。其父黃澤民曾于辛亥革命前夕留學(xué)日本,回國(guó)后于重慶創(chuàng)辦了川東師范學(xué)校并擔(dān)任首任校長(zhǎng)。其母太田喜智,乃是日本千葉縣八日市場(chǎng)市人,18歲時(shí)從女子師范學(xué)校畢業(yè)后成為了當(dāng)?shù)氐男W(xué)教師。在日俄戰(zhàn)爭(zhēng)后她主動(dòng)應(yīng)聘日清交換教員,只身前往中國(guó)并與黃澤民結(jié)成跨國(guó)婚姻。1914年其父不幸去世,年僅八歲的黃瀛不得不跟隨母親移居日本千葉縣,進(jìn)入其母家鄉(xiāng)的普通小學(xué)開(kāi)始學(xué)習(xí)日語(yǔ)。雖然黃瀛開(kāi)始接受日式教育,但由于太田喜智保留了黃瀛的中國(guó)國(guó)籍,這也為他的求學(xué)之路帶來(lái)了種種困難和阻力。小學(xué)畢業(yè)之時(shí),雖然黃瀛以?xún)?yōu)異的成績(jī)考取了省立成東中學(xué),但卻被校方以不收中國(guó)學(xué)生為由而拒絕錄取。這種因日中兩國(guó)關(guān)系的惡化所帶來(lái)的對(duì)于中國(guó)人的歧視風(fēng)潮使黃瀛從小就飽嘗了作為“混血兒”的身份之尷尬與苦悶。不得已的情況下,他進(jìn)入東京私立正則中學(xué)學(xué)習(xí)。1923年他回國(guó)赴天津探親之時(shí)正好發(fā)生了關(guān)東大地震故而不得不留在中國(guó)。他以插班生的身份進(jìn)入青島的日本人中學(xué)讀書(shū)。日語(yǔ)表達(dá)日漸成熟的他,也從此時(shí)開(kāi)始了寫(xiě)詩(shī)的嘗試。本就有口吃毛病而不善交流的黃瀛如同找到了情緒宣泄的閘口一般,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一發(fā)而不可收。據(jù)黃瀛自己回憶,此時(shí)期內(nèi)“最多時(shí)每天能寫(xiě)多達(dá)20首詩(shī),而平均每周約能創(chuàng)作40首左右。”此外,他還大量閱讀了高村光太郎的《道程》、中川一政的《見(jiàn)なれざる人》等日本詩(shī)人的詩(shī)集。經(jīng)過(guò)不斷的努力投稿,1923年他的《早春登校》因獲得了詩(shī)歌雜志《詩(shī)圣》編選者赤松月船、中野秀人、橋爪健等人的青睞而得以在當(dāng)年第三號(hào)上刊載。而同期刊載的還有從中國(guó)廣州投稿的詩(shī)人草野心平的詩(shī)作《無(wú)題》。這一歷史的偶然,不僅給予了黃瀛以職業(yè)詩(shī)人之身份從事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信心和勇氣,同時(shí)也促使他寫(xiě)信給了彼時(shí)在廣州留學(xué)的草野心平,從而開(kāi)啟了二人貫穿一生的友好交誼。
受到專(zhuān)業(yè)肯定和詩(shī)友鼓勵(lì)的黃瀛,開(kāi)始更為積極地向日本的文藝期刊廣泛投稿。僅1924年10、11月兩個(gè)月間,就有四篇作品獲刊在《東京朝日新聞》的“學(xué)藝”專(zhuān)欄中,其專(zhuān)欄負(fù)責(zé)人也正是曾經(jīng)作為《詩(shī)圣》審稿人之一的中野秀人。而在該專(zhuān)欄中同時(shí)期發(fā)表詩(shī)歌的不僅有黃瀛推崇的高村光太郎,也有剛開(kāi)始書(shū)簡(jiǎn)往來(lái)的詩(shī)友草野心平。在日本雜志上偶爾露臉的黃瀛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的沉潛和努力,終于于次年的1925年開(kāi)始獲得日本詩(shī)壇的廣泛關(guān)注。這源于當(dāng)時(shí)在詩(shī)壇上頗具影響力的“詩(shī)話(huà)會(huì)”會(huì)刊《日本詩(shī)人》(新潮社)計(jì)劃在當(dāng)年二月號(hào)中將公開(kāi)征集詩(shī)歌中的優(yōu)秀作品以《第二新詩(shī)人專(zhuān)號(hào)》的形式集結(jié)出版,加以宣傳和推介。在白鳥(niǎo)省吾、千家元麿和荻原朔太郎等10位詩(shī)歌大家擔(dān)任評(píng)委、從二百六十多篇詩(shī)作遴選出的最優(yōu)秀10首作品中,黃瀛的《朝の展望》(《清晨的展望》)不僅榜上有名,而且以第一名的身份榮登該卷卷首。選者之一的荻原朔太郎在發(fā)表于同年11月號(hào)《日本詩(shī)人》上的詩(shī)評(píng)中論及黃瀛之詩(shī)時(shí)指出黃瀛是“實(shí)為有著一副樂(lè)感敏銳耳朵的詩(shī)人”,“而黃瀛對(duì)日語(yǔ)有著很好的聽(tīng)感,想起來(lái)恐怕也源于他是外國(guó)人的緣故吧”。
1925年從青島中學(xué)畢業(yè)以后,黃瀛說(shuō)服了他的母親和家人獨(dú)自從青島出發(fā)、經(jīng)由神戶(hù)回到東京,再度開(kāi)始了日本留學(xué)生活。回到日本東京后,黃瀛于1926年考入日本文化學(xué)院,一年后中途退學(xué)又轉(zhuǎn)入陸軍士官學(xué)校。求學(xué)期間的1930年,他正式出版了第一本個(gè)人詩(shī)集《景星》。1931年回國(guó)從戎,結(jié)束了短暫的二度日本生活。這一時(shí)期,黃瀛正是通過(guò)自己的日語(yǔ)詩(shī)歌寫(xiě)作,不僅獲得了日本詩(shī)壇的認(rèn)可和接納,而且極大的治愈了他原本作為陰影創(chuàng)傷的“混血”之痛。正如亦師亦友的奧野幸太郎所說(shuō):“黃君(按:指黃瀛)之所以成其為黃君,乃是因?yàn)樗麩o(wú)論用中文寫(xiě)詩(shī)還是用日語(yǔ)寫(xiě)詩(shī),都毫無(wú)差異”,“他正是借助了日本語(yǔ)言,才得以保持了與詩(shī)歌世界的聯(lián)系”。
二、譯作:越境/審美體驗(yàn)的“交響”
身為“混血兒”的身份特殊性,也直接體現(xiàn)在了他詩(shī)歌創(chuàng)作之外的詩(shī)歌翻譯活動(dòng)中。作為能同時(shí)熟練使用中日兩國(guó)語(yǔ)言的詩(shī)人,黃瀛強(qiáng)烈感受到需要向日本詩(shī)壇發(fā)信的使命感。在他看來(lái),雖然“中國(guó)的詩(shī)壇比日本詩(shī)壇更有活力”,但對(duì)于“如今中華民國(guó)的文學(xué),在日本是并不明了其狀況的”,故而主張“日本的外國(guó)詩(shī)人研究應(yīng)該更加關(guān)注中國(guó)”。1925年至1930年間,黃瀛不僅作為一名以日語(yǔ)來(lái)創(chuàng)作的“混血”詩(shī)人活躍在日本詩(shī)壇,并且還積極地將同時(shí)代中國(guó)的諸如胡適、郭沫若、馮乃超、王獨(dú)清、蔣光慈等重要詩(shī)人的詩(shī)作翻譯成日語(yǔ)在日本詩(shī)歌雜志上進(jìn)行發(fā)表。而這種主動(dòng)通過(guò)詩(shī)歌翻譯來(lái)參與中日詩(shī)壇的交流的行為,使黃瀛消除了對(duì)自身“混血”身份的焦慮感,而將其“中間者”的尷尬成功地轉(zhuǎn)化為自身在詩(shī)壇立足時(shí)作為一種“橋梁”和“中介”的獨(dú)特優(yōu)勢(shì)。
從時(shí)間跨度上來(lái)看,黃瀛從1925年11月開(kāi)始譯介發(fā)表中國(guó)新詩(shī),最初選擇的是在新詩(shī)初創(chuàng)期具有開(kāi)拓性的胡適與康白情的詩(shī)歌。而1925年也正是黃瀛開(kāi)始在日本詩(shī)壇嶄露頭角的年份。隨后的一段時(shí)間,黃瀛將更多的精力集中于自身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和詩(shī)壇活動(dòng)。直到1928年開(kāi)始,重新進(jìn)入譯詩(shī)的高產(chǎn)期,但持續(xù)至1931年就戛然而止。而這個(gè)時(shí)間段也與黃瀛第二次留日的時(shí)期(1925~1931)正好吻合。在此期間,黃瀛總計(jì)譯介了32首新詩(shī)、詩(shī)人自傳1篇以及詩(shī)歌評(píng)論2篇,涉及十五家詩(shī)人。涉獵范圍之廣,譯介數(shù)量之多,在1920年代的日本詩(shī)壇可謂獨(dú)樹(shù)一幟。譯介詩(shī)作刊載具體情況如下表:
日本詩(shī)歌雜志上所刊黃瀛翻譯中國(guó)詩(shī)歌一覽
(1925
~1930
)
除在詩(shī)歌雜志上刊載譯詩(shī)以外,黃瀛還擔(dān)任了為金星堂出版社所出《現(xiàn)代世界詞華選》中“中華民國(guó)詩(shī)歌”部分的編選工作。他除了將已經(jīng)發(fā)表在《詩(shī)與詩(shī)論》上的郭沫若《黃河與揚(yáng)子江的對(duì)話(huà)》和發(fā)表在《詩(shī)神》上章衣萍的《醉酒歌》、蔣光慈的《北京》、馮乃超的《紅紗燈》以及王獨(dú)清的《Now I am Choric man》這四首譯作再度收入以外,還增加了兩首陸志韋和聞一多的詩(shī)歌譯作。
綜觀以上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其中同一位詩(shī)人有3首及其以上譯作的分別是:蔣光慈7首、王獨(dú)清6首、郭沫若3首、章衣萍3首、馮乃超3首。而其中以“詩(shī)抄”為題,推出了個(gè)人專(zhuān)題系列的則有蔣光慈、王獨(dú)清和郭沫若三人。由此可見(jiàn),黃瀛所關(guān)注的詩(shī)人絕大多數(shù)是創(chuàng)造社的主要成員,而且大多詩(shī)人都與日本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在日本留學(xué)長(zhǎng)達(dá)十年之久的創(chuàng)造社發(fā)起人之一郭沫若自不待言。被黃瀛譯介次數(shù)最多的蔣光慈曾經(jīng)因患肺結(jié)核而于1929年8月赴日本休養(yǎng)。在東京期間他組織了太陽(yáng)社東京支部,并曾與日本左翼作家藏原惟人等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yán)碚摵透锩膶W(xué)問(wèn)題。而擔(dān)任過(guò)《秦鏡報(bào)》主編的王獨(dú)清,也曾因報(bào)館被查禁和躲避襲擊追捕而在姻兄的安排下于1915年亡命日本三年。1919年末回到上海后為《時(shí)代新報(bào)》的“學(xué)燈“、“少年中國(guó)”等欄目及《救國(guó)日?qǐng)?bào)》的“新文化”撰寫(xiě)文章。詩(shī)人馮乃超本身就是出生于日本橫濱的一個(gè)華僑子弟。曾于1920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xué)校預(yù)科,后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學(xué)校學(xué)習(xí)。1923年家庭因遭遇關(guān)東大地震而損失慘重,遭遇變故。正如關(guān)東大地震改變了黃瀛的人生軌跡一樣,這場(chǎng)災(zāi)難也使馮乃超從富家子弟變成一介平民,日后成為促使他走上文學(xué)道路的契機(jī)。馮乃超不僅學(xué)生生活全部在日本度過(guò),而且前后在日本累計(jì)生活了24年之久。1928年4月更是將他在日本讀書(shū)期間創(chuàng)作的詩(shī)歌集結(jié)為《紅紗燈》,由上海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出版。
黃瀛雖然國(guó)籍是中國(guó)人,但因?yàn)閺男〗邮苷?guī)日式教育以及母親言傳身教的影響,他的思想意識(shí)與審美標(biāo)準(zhǔn)也深深烙下了日式的情趣和印記。黃瀛曾對(duì)郭沫若的詩(shī)歌成就給予了高度肯定,認(rèn)為“作為現(xiàn)代中國(guó)出現(xiàn)的文學(xué)家,他是魯迅一樣值得引以為傲的詩(shī)人”。


《詩(shī)神》雜志
他在介紹中國(guó)新詩(shī)的文章《中國(guó)詩(shī)壇的現(xiàn)在(中國(guó)詩(shī)壇の現(xiàn)在)》中也指出從新詩(shī)的初創(chuàng)期到無(wú)產(chǎn)階級(jí)詩(shī)歌勃興之間還有一個(gè)抒情詩(shī)的時(shí)代,其中就以郭沫若的《瓶》、馮乃超的《紅紗燈》與穆木天的《旅心》為代表。黃瀛對(duì)馮乃超的詩(shī)集《紅紗燈》可謂推崇備至,并敏銳地覺(jué)察到了其中所具備地頹廢感傷的色彩,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在外國(guó)人眼里,或許會(huì)從《紅紗燈》中看到某些過(guò)剩的感傷情調(diào)”,“無(wú)論其表現(xiàn)或形式,都充滿(mǎn)了新鮮感”,“我認(rèn)為它也處于中國(guó)詩(shī)壇的前列”。黃瀛在日本期間曾與馮乃超相識(shí)并保持著書(shū)信往來(lái),而巧合的是馮乃超曾于1925年在東京神田區(qū)中國(guó)基督教青年會(huì)上結(jié)識(shí)了學(xué)友穆木天。后來(lái)回憶二人的交往以及穆木天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時(shí)說(shuō):
這個(gè)曾經(jīng)立志要當(dāng)工程師希望工業(yè)救國(guó)而且又具備學(xué)習(xí)理科課程素質(zhì)的青年,經(jīng)歷過(guò)封建大家庭的解體,又經(jīng)歷了中興的資產(chǎn)階級(jí)家庭的沒(méi)落。他備嘗這種由富變窮的痛苦,感到身世飄零,不得不拋棄工業(yè)救國(guó)的理想。彷徨歧路中,選擇了搞文學(xué)的道路。(中略)詩(shī)歌變成他寄托個(gè)人憂(yōu)思、失戀的悲哀和身世凄涼的工具。《旅心》集里留下詩(shī)人不盡的鄉(xiāng)愁,故國(guó)的思戀。
馮乃超這段對(duì)穆木天的追憶文字,事實(shí)上也適用于黃瀛的飄零身世。《旅心》與《紅紗燈》都誕生于日本,兩部詩(shī)集多描寫(xiě)感傷與頹廢的情緒,常表達(dá)愛(ài)情的失意和生命瞬間的惆悵,都帶有日本文學(xué)“物哀”的情調(diào)。葉渭渠在《日本文學(xué)思潮史》中認(rèn)為:“‘物哀’是將現(xiàn)實(shí)中最受感動(dòng)、最讓人動(dòng)心的東西(物)記錄下來(lái),寫(xiě)觸‘物’的感動(dòng)之心、感動(dòng)之情,寫(xiě)感情世界。而且感動(dòng)的形態(tài),有悲哀的、感傷的、可憐的、也有憐憫的、同情的、壯美的。也就是說(shuō),對(duì)‘物’引起感動(dòng)而產(chǎn)生的喜怒哀樂(lè)諸相。”事實(shí)上,《紅紗燈》與《旅心》在諸多藝術(shù)技巧方面,如對(duì)物像的纖細(xì)描繪,對(duì)朦朧哀傷情調(diào)的追求,對(duì)自然界聲色的敏感,對(duì)詩(shī)歌音樂(lè)節(jié)奏的執(zhí)著都表現(xiàn)出對(duì)日本文化的廣泛吸收和借鑒。創(chuàng)造社諸君與日本或深或淺的淵源,以及自己與馮乃超、穆木天相似的人生經(jīng)歷和體驗(yàn),必然引起黃瀛內(nèi)心的“交響”,成為去關(guān)注他們?cè)姼枋澜绲闹匾蛩刂弧?/p>
三、譯“場(chǎng)”:作為詩(shī)壇“公器”的《詩(shī)神》
在梳理完譯者經(jīng)歷與譯作構(gòu)成之后,我們需要進(jìn)一步思考究竟是什么樣的環(huán)境導(dǎo)致黃瀛1920年代日本滯留時(shí)期內(nèi)進(jìn)行了大量而獨(dú)特的詩(shī)歌翻譯活動(dòng)?而要解釋這一問(wèn)題,必須梳理清楚支持黃瀛進(jìn)行翻譯活動(dòng)并為之提供公開(kāi)發(fā)表舞臺(tái)的“媒介”(期刊)和“場(chǎng)域”(詩(shī)人交際網(wǎng)絡(luò))。這些因素一方面促使了翻譯活動(dòng)的發(fā)生和開(kāi)展,另一方面無(wú)疑也左右了翻譯活動(dòng)的伸延路向。
“場(chǎng)域”作為布迪厄社會(huì)學(xué)的核心概念之一,主要是指“具有自己獨(dú)特運(yùn)作法則的社會(huì)空間”,“從分析的角度來(lái)看,一個(gè)場(chǎng)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guān)系的一個(gè)網(wǎng)絡(luò)(network),或一個(gè)構(gòu)型(con-figuration)。”簡(jiǎn)言之,“場(chǎng)域”是相對(duì)獨(dú)立的社會(huì)空間,每個(gè)場(chǎng)域有其獨(dú)立的運(yùn)作規(guī)則,但也與其它場(chǎng)域之間相互關(guān)聯(lián)。具體到不同歷史語(yǔ)境下的翻譯活動(dòng)中,譯介的過(guò)程也有其獨(dú)特的關(guān)系系統(tǒng),諸如譯者、出版商、策劃人、讀者、批評(píng)家等在翻譯實(shí)踐中形成了一種特定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從而生成了不同于其他場(chǎng)域的有其自身獨(dú)特規(guī)則的翻譯場(chǎng)域。通過(guò)前文對(duì)黃瀛發(fā)表譯作媒介的梳理,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譯介活動(dòng)主要集中在1929年與1930年。而在此期間,刊載于《詩(shī)神》雜志上的新詩(shī)譯作除開(kāi)“中國(guó)民歌”專(zhuān)題以外多達(dá)20首,占到了他個(gè)人譯詩(shī)數(shù)量的三分之二,其中還包括了“王獨(dú)清詩(shī)抄”與“蔣光慈詩(shī)抄”兩個(gè)詩(shī)人專(zhuān)題。《詩(shī)神》作為黃瀛個(gè)人譯作發(fā)表高峰期所選擇的發(fā)表舞臺(tái),對(duì)二者關(guān)系的梳理可以從媒介場(chǎng)的角度幫我們進(jìn)一步理解黃瀛的新詩(shī)譯介與翻譯場(chǎng)域的相互構(gòu)建。
《詩(shī)神》是一本由廣島出生的詩(shī)人田中清一于1925年9月出資創(chuàng)刊并由聚芳閣出版每月一號(hào)發(fā)行的月刊詩(shī)歌專(zhuān)門(mén)雜志。《詩(shī)神》雖然名義上由田中清一主宰,但在第三卷十二號(hào)之前實(shí)際主要由田中的好友福田正夫擔(dān)任顧問(wèn)和負(fù)責(zé),由神谷暢和辻本浩太郎擔(dān)任實(shí)際的編輯工作。昭和二年年末開(kāi)始則主要由清水暉吉負(fù)責(zé)編輯。從第四卷一號(hào)開(kāi)始,借田中去東京之際,福田將編輯大權(quán)移交給了田中,由他親自參與雜志的編輯和建設(shè)工作。事實(shí)上,在田中真正完全接手之前的過(guò)渡時(shí)期,從昭和三年七月至昭和四年一月期間,該雜志短期由宮崎孝政主持。昭和四年一月開(kāi)始,田中清一完全正式參與該雜志的編輯,并得到了宮崎孝政的輔佐。在此期間,《詩(shī)神》不斷擴(kuò)大版面和容量,前后發(fā)行七年后于1932年停刊。由《詩(shī)神》核心成員對(duì)刊物發(fā)展方向和定位的闡釋可以看出,該刊物同人有意識(shí)地要將其打造為詩(shī)壇具有“公器”色彩的詩(shī)歌雜志,在不分流派、不搞團(tuán)體、不論主義的理想下繁榮詩(shī)壇的創(chuàng)作,并積極介紹海外詩(shī)歌發(fā)展?fàn)顩r。
《詩(shī)神》雜志在福田主持的初期階段,比較重視民眾詩(shī)派的詩(shī)歌作品,詩(shī)論方面福士幸次郎連載發(fā)表的《田舎のモノローグ》受到了廣泛的關(guān)注。清水暉吉接班之后,則大量推介了他的同鄉(xiāng)荻原恭次郎的詩(shī)歌。其后在師從室生犀星的詩(shī)人宮崎孝政主持下,偏向于重視書(shū)寫(xiě)普通民眾生活的敘情詩(shī)以及當(dāng)時(shí)較為流行的童話(huà)和民謠。田中清一接手主宰之后,則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該雜志詩(shī)歌“公器”的色彩,廣泛運(yùn)用他在詩(shī)壇的人脈關(guān)系,積極與當(dāng)時(shí)流行的《詩(shī)與詩(shī)論》、《詩(shī)現(xiàn)實(shí)》等詩(shī)歌雜志以及以《銅鑼》、《亞》等詩(shī)歌雜志為陣地的詩(shī)歌同人團(tuán)體建立互動(dòng)關(guān)系,發(fā)表他們的詩(shī)歌作品。與此同時(shí),該雜志還積極翻譯海外詩(shī)歌作品,設(shè)立了海外詩(shī)壇的專(zhuān)欄予以介紹。譯介比較集中的國(guó)家及其相對(duì)翻譯作品較多的詩(shī)人情況如下:
蘇俄:黑田辰男、村松正俊、升署夢(mèng)、村田春海、尾瀨敬止等
法國(guó):前田鐵之助、佐藤正彰、堀辰雄、北川冬彥、三好達(dá)治等
德國(guó):阪本越郎、小出直三郎、木下杢太郎、片山敏彥等
意大利:佐藤雪夫、神原泰、巖崎純孝等
英國(guó):佐藤清、野口米次郎、山宮允、阿部知二等
美國(guó):草野心平、田中清一、野口米次郎等
中國(guó):黃瀛、井東憲等
正是在這樣的場(chǎng)域中,作為“少數(shù)派”的外國(guó)詩(shī)人黃瀛也得到了肯定和重用。而作為積極關(guān)注詩(shī)壇時(shí)代動(dòng)向的舉措,大力推介中國(guó)無(wú)產(chǎn)階級(jí)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的代表作品以及后期創(chuàng)造社詩(shī)人的普羅詩(shī)作就成為一拍即合之時(shí)代“共鳴”。而伴隨著這些形式各異、視角不一的中國(guó)普羅詩(shī)歌的譯介和傳播,作為革命文學(xué)之一端的近代中國(guó)詩(shī)壇“無(wú)產(chǎn)階級(jí)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也跨越國(guó)界進(jìn)入日本文壇的視野。如同周作人對(duì)日本和歌、俳句等“小詩(shī)”的譯介一樣,活躍在1920年代日本詩(shī)壇的中國(guó)詩(shī)人黃瀛在通過(guò)對(duì)中國(guó)新詩(shī)的譯介,也為中日兩國(guó)詩(shī)壇之間架起了一座彼此來(lái)去往還的共時(shí)性橋梁,有助于中日兩國(guó)詩(shī)歌在獲得一種時(shí)代的共鳴與交響。作為現(xiàn)代中日詩(shī)歌交流史上一個(gè)有代表性的橫截面,卻也不容我們忽視。

裴亮,日本九州大學(xué)博士,現(xiàn)任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珞珈青年學(xué)者。研究方向?yàn)橹袊?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日近現(xiàn)代比較文學(xué)。近年來(lái)主要致力于以“越境”與“譯介”的視角展來(lái)開(kāi)中日近現(xiàn)代文學(xué)交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