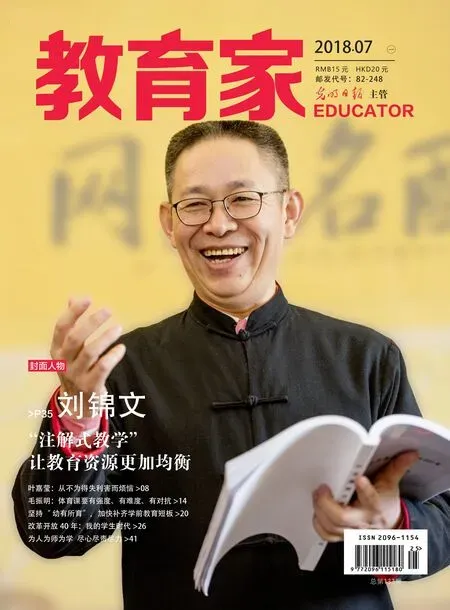“注解式教學”的信息化呈現與“教育進化論”
文 |

研究中國的教育傳承首先得從《論語》說起。《論語》不僅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寶庫,也是一個中華學術與教育傳承的百花園。園里名師薈萃,百花爭妍,“注”書立學,前后相繼,薪火相傳。
注解之學是一種文化傳承
從“子曰”“問于孔子”等初始答問發端到孔門弟子仲弓、子游、子夏匯撰《論語》成書之后,關于《論語》的解讀、考據、辨偽從未間斷,圍繞《論語》的大辯論此興彼伏,且大多以對《論語》進行注解的形式展開。歷史上解讀《論語》的“注”作可謂汗牛充棟,馬融、鄭玄、何晏、皇侃、朱熹等《論語》的注解者先后各領風騷數百年。
圍繞《論語》的注釋大致沿著這樣的脈絡發展,其他主要經典也一如《論語》,大同小異。我國早期的典籍和文獻的基本特點是文辭簡約,詰屈聱牙,晦澀難讀。清代大學者戴震為此發出了“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的感嘆。經過秦末大一統的爐火洗禮和書同文的變革,漢代人閱讀典籍都感到非常困難,何況唐宋人。因此,通過注解對文本進行訓釋就變得必不可少。
浩瀚經典文章,注解是捷徑。注其音、解其義、辨其物、溝通古今語言就成為歷代學者們無法回避的任務。古代學者注解的形式有傳、章句、箋 、注、義疏等多種形式,并在漫長的學術發展歷史中得到了進化。給古書作注解是歷代注經師為后學鋪路修梯、指導后人學習古代典籍的重要途徑。
孔子師徒對中華古典注解之學貢獻巨大。歷史上第一個為注釋之學垂范的學者應該是孔子,孔子給《周易》作的“傳”稱為《易傳》,就是為《易經》的經文作的解讀。《春秋》一書言簡義深,讀者必須通過“傳” 才能讀懂。左丘明的《左傳》就以“傳”的方式為我們講述了有血有肉的春秋故事,左丘明因此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傳注大師。孔子的弟子、孔門文學科的高足子夏開辦私塾,講習《詩》,發明了章句。東漢末的經學大師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成為箋注的首創者。
早期的注解經傳分離,獨立成篇,閱讀時必須經傳兩讀,一邊看傳注書,一邊對照經書。造紙技術的進步為注解體例的創新提供了物理條件。漢代學者馬融在為《周禮》作注時在經書的行間插入夾行,稱為“夾注”,顯然是在紙本書上注解的。馬融之后的注家一般都“就經為注”,經傳合二為一。南北朝出現了以皇侃《論語義疏》為代表的義疏體例,這種體例因受到南朝佛教講經的影響又稱為“講疏”。講疏是一種新型注釋形式,不僅訓釋詞義,串講句義,而且申述全篇大意,尤其注重對舊注作進一步的解釋和發揮。到了宋代,注解之學經歷了一次升華,朱熹的《論語集注》不僅注重探求經文的本義,更注重義理的闡發,通過注釋來表達自己的理學思想。
注解之學在清代進入了高潮,以被譽為“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師”孫詒讓編注的《周禮正義》的問世為標志,中國的古典注解之學完美收官。
注解是一種教學方式和教育傳承
通過注解,中國學人在潛移默化中發展了一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教學方式。前代先師通過注解為學習者答疑傳道解惑,后學者可以通過注解與前代先師溝通與對話,可以擇其善者而從之,選其不善者而改之,優化注解,師承無間斷。筆者把這種教育傳承方式命名為“注解式教學”,這是中國先哲們在教育上的一項發明創造。
通過對古籍注解歷史脈絡的深入梳理,筆者發現,注經師大多都有辦學的實際需要,有開塾辦學、立院講學的經歷,在官學傳道,在私塾授業。他們的經歷印證了注書與辦學是相隨相行的。孔子、曾子、子夏、孟子、鄭玄、朱熹等都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名師,從學者動輒數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人心向往之。
注經師們 “注”書立說、解經注經的目的首先是服務于教學,然后把編寫的“教案”不斷優化上升為教科書和專著,刊行于世,傳之后人。孔子刪選《詩》《書》、編寫《易傳》、因史記作《春秋》都是在其晚年完成的,那時孔子已經設壇講學了,“六經”不過是孔子將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作為傳授弟子的教科書而已。可見,編寫注本也是古人編寫教材的一種方式。
一部中國古代學術史就是一部不斷進化的注解史,注解之學經過歷代學者的經營已成蔚然大觀。先哲們通過不懈的努力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注本,每一部經書的注本都是一個不小的書系,以注解的方式為我們積累了豐厚的學術遺產,讓今天的我們能夠站在巨人的肩上前瞻后顧,暢游學海;每一個注本后面都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大學堂隱而藏之,一朝登堂入室,必見大師云集,學者冠蓋。
“注解式教學”的現代化
從教學的角度看,朱熹畢一生精力編寫的《四書章句集注》堪為教學者的載體、學習者的標本。 沿著這個思路,我們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按照“注解式教學”的教學思維研發了融入多媒體批注的注解式課程制作平臺——名獅秀課件優化平臺,用極具新意的設計和渲染功能讓常規的文字、普通的圖片、通用的動畫和視頻發揮出奇妙的教學效能,制作出了精美的注解式課程。
在一個精心設計的注解式課程中,教師通過調動課件中或明示或隱藏的文字注釋、圖片示例、音頻解說、動畫或視頻的形象化解讀等多維度認知手段,運用多媒體素材中所含的聲、光、色彩、影像等多種信號刺激學生的感官反應,強化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內化,并將某些高度邏輯化、抽象化的知識巧妙地轉化為具體的、形象直觀的知識,加深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從而使知識的轉移更加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學習者通過觸發隱藏的多媒體注解按鈕實現對課文和知識點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在一個注解式課程單元中,能夠囊括一個教師對該課的全部教學設計、教學思維和教學理念,毫不損失教學的深度和廣度。
“注解式教學”深刻揭示“教育進化論”
在“注解式教學”的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教學的主體和客體經常處于角色轉換的狀態,就像兩個互相作用的齒輪,主動輪和從動輪的地位并非始終如一,從動輪由于慣性前沖經常給主動輪帶去推力,使主動輪不時處于從動狀態,從動輪經常變成了主動輪。
由此,我們發現了“教育進化論”,使我們對教育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教學者以“所學也有涯”作用于“欲學也無涯”被迫經常處于從動的狀態,孔子晚年經常處于不理解學生的從動狀態,是為例證。從《論語》一書的師承關系中,清晰可見學習者作為一個被動的“整體”總是超越教學主體并繼續完成主體未完成的任務,教學者因經常處于客體的位置而被迫主動適調,使自己迅速再次處于主體狀態。學習者經常反哺教學者,教學者經常被學習者推著不斷擴大認知的深度和廣度而進入教學的新境界。“三人行,必有我師”這一古訓也深刻地詮釋了這一點。這就是“教育進化論”。中國古典的注解式學術體系圍繞著一部《論語》的教與學不斷進化,從本質上印證了“教育進化論”,師生教學相長,以師者授業解惑為先導,后學者不斷深化認知為繼,一代代學人不懈地描繪著“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壯麗景觀。

劉錦文(中)和他的同事們
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使參與教學的各個主體處于最佳狀態,從而實現教育效能的最大化。信息化時代要求教學者快速適應“教育進化論”以創造更有價值的教學,要求教學者不斷發現教學需求,并通過設計更好的教育機制把教學需求落實在下一輪全新的教學過程中。教學者把需要講解的知識通過素材的方式提前注解在課程中,為學生的知識大廈預筑一個堅實的基礎層,充分調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讓學生在講課前提前獲得共同的“基本認知”。這種前導式、常住式的教學,大大拓展了教師的教學空間,把教師從基本認知的教學中“解放”出來,讓教師有更多的時空與學生開展對話與互動,讓學生們有更多的空間去交流與思考,讓傳統的主客體教學理論升華為自主任務驅動下的共同主體理論,讓教師和學生像兩個互動的齒輪一般教學相長。
一節好課,如一方井田,備耕越是精細,產出和收獲才會越豐盛。這是對中國優秀的“注解式教學”傳統的最好詮釋。
“注解式教學”推動電子教材的升級
“注解式教學”所引發的“教育進化論”,要求進一步“進化”教學的載體。我們嘗試著把“注解式教學”與教材革新結合起來,嘗試著用注解式課程開發平臺發展新一代電子教材,進而重新定義了電子教材的呈現標準和電子課本的閱讀標準。我們認為,電子教材并不僅僅是把紙質課本簡單地快照式電子化,更主要的是對課本內容進行深度加工,以文字、圖片、音頻、動畫、視頻等多種形式,多角度、多維度地解讀課本,讓學習者和課本注釋者互動,隨機精選導出生成性注釋資源,發掘更多疊加的教學價值和人文內涵。
在新一代電子教材中,編者也是教學者,教師可以在同行大師注解的基礎上對課程進行再注解,從而生成該教師的個性化教材,隨時通過移動端分享給任一學習者,還可進一步對接數字化校園,整合學習者的大數據,采集部分優秀學子的學習心得,使新一代電子課本具有生成性資源融入功能,真正開啟教育的“易”時代,徹底改變課本的閱讀方式和使用方式,提升教材的使用價值。
注解式電子教材最核心的價值是對學生自主學習、個性化學習、探究性學習的支撐和優質學習資源的共享。通過知識呈現的顆粒化、學習空間的碎片化、課程內容的個性化,讓教學進入一個自在王國。
做到了這一點,我們的課堂教學就可以升華到有高附加值的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的理想境界。我們已經感受到,用注解式課程開發平臺制作的電子教材就像活生生的老師一樣,為學習者課前預習、課中有效學習、課后復習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給翻轉課堂、教學點、私播課(SPOC)等教學場景帶來了全新的巨大增值。
“注解式教學”將催生更美的教學生態,注解式課程將成為未來最有價值的教學資源,“注解式教學”的信息化呈現也必將成為教學方式變革的最具代表性的思維與技術。
“注解式教學”開啟了傳統文化典籍信息化注解之旅,讓我們通過信息化手段全維度解讀古典文化,讓更多的中華典籍可以通過多媒體注解“親和”地接近普通讀者。
未來,學生們在課本里會遇見更美的老師,老師們在荷塘里會看到更美的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