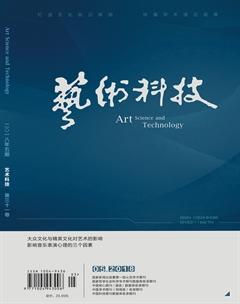游戲與敘事
郭磊
摘 要:游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后,對于互動與敘事一直存在兩種相悖的觀點。一種認為敘事是線性表達,與交互性的游戲并不兼容;一種則認為游戲是一種絕佳的敘事媒介載體,很多游戲甚至將“講故事”作為游戲的核心。業界對于游戲性與故事性也在各種類型的游戲中作出了嘗試,為傳統敘事媒體帶來了更為豐富的敘事手法,甚至拓寬了游戲與敘事的邊界。
關鍵詞:游戲敘事;游戲學;敘事
對于游戲(本文中對于游戲的定義并非廣義的游戲,僅特指“電子游戲”)的研究自21世紀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后,游戲剔除“電子海洛因”屬性,以一種文化或者美學的形式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就與敘事有著糾纏不清的關系。眾多的學者在各自領域內對游戲與敘事的關系作出了不同的詮釋。盡管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也在很多方面達成了共識——敘事并不是游戲的必備條件,但是敘事能夠為游戲帶來非常大的樂趣,特別是某些特定類型的游戲,如角色扮演、動作冒險、互動小說(影片)等,都有豐富的敘事方式。
我們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電子游戲(Video Game)在出現之初,確實是沒有敘事屬性的,如坦克大戰、俄羅斯方塊等游戲,它們都僅僅是游戲規則+圖形的機制,玩家在游戲中體驗下達指令獲得機器反饋,游戲設計者的關注點則放在游戲機制與美術上。這時,敘事是被排除在游戲之外的。即使是有敘事的一些早期經典游戲中,如以拯救公主為主線劇情的《超級馬里奧兄弟》,敘事也僅僅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裝飾,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使游戲角色的行為合理化,玩家的注意力多在游戲機制上,而不會關注敘事本身。許多學者持此觀點:“互動與敘事是幾乎相反的;敘事跟隨在作者的導演之下,而互動依賴于玩家的意志。”[1]講故事的需求與互動的需求存在直接的沖突。故事路徑的分歧會導致一個不那么令人滿意的故事;而限制玩家的行動自由則可能導致一個不那么令人滿意的游戲。[2]
這兩種觀點都直接將互動與敘事對立起來,試想,如果部分觀眾不喜歡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劇結局,而決定讓他們復活一起幸福生活,那么這部莎士比亞的戲劇還能夠流傳至今嗎?所以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觀點是成立的,甚至可以說游戲與敘事是不可調和的。敘事本質上是線性的(雖然存在非線性敘事,但是在結構上敘事依然是線性的),而交互則是非線性的,兩者對于時間的詮釋是不同的,他們之間存在矛盾。游戲指向交互,而敘事指向引導。讀者在閱讀時或與玩家游戲時,他們與故事世界或游戲世界的關系是不同的,游戲玩家總是參與到游戲當中,而讀者或者觀眾在面對敘事媒介的時候則更加被動。
那么是不是游戲就真的不需要敘事呢?當今的現實情況似乎并非如此。無論在PC游戲、主機游戲還是移動端游戲,“講故事”的需求在游戲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很多大型MMORPG游戲直接使用文學或影視作品改編,關于游戲劇情的討論在現在獲得了更多的關注,甚至在很多游戲中,“講故事”已經成為核心環節。利潤,2018年發售的由Quantic Dream開發,并由索尼互動娛樂發行在PlayStation 4平臺的冒險游戲《底特律:變人》,就運用了非常特殊的敘事方式,游戲中有多個可玩的角色,且他們的死并不影響故事的發展,因此角色死后并不會有“游戲結束”的消息。《底特律:變人》的故事會根據玩家的選擇進行分支,而玩家覺得在某些抉擇點作出的決定不好的時候,其可以回溯到該點重新選擇。在這部游戲中,游戲的劇情走向完全是由玩家控制的,玩家根據意愿作出不同的選擇,帶來不同的結局。可以說,這是一部完全以敘事為導向的游戲。
在游戲的敘事中,文學類的敘事手法是游戲敘事最早使用的方法,如《仙劍奇俠傳》。早期的游戲中,以大量文本的方式來交代故事背景、游戲進程,這種手法直接將文字內容搬到游戲中。隨著游戲的發展,單純的文字類敘事就顯得單調枯燥,也容易引起玩家的反感。電影類的敘事手法更多地運用到游戲中,這種手法通常使用過場動畫的方式交代重要的劇情故事線,在游戲進行過程中運用布景或者對話的方式來渲染氣氛。相較于文字類的敘事方法,這種方式更容易給玩家帶來沉浸感,不會脫離游戲的整體氛圍。
游戲中“講故事”的手法要遠比傳統的敘事性媒體更加豐富與多變,我們根據互動的特性對這些敘事手法進行歸納,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幾種敘事結構。
第一,嵌入式敘事。這種敘事結構相對單一,編劇將劇情策劃好,玩家按照劇情的編排線性地進行游戲。在這種結構中,玩家沒有改變劇情的權利,其更接近于傳統的文學類或影視敘事,也可以稱為線性敘事。
第二,應變性的敘事。這種敘事方式與嵌入型的敘事相反,玩家在游戲世界中的自由度更大,可以作出的選擇也更多。在如今的開放性世界,游戲多以這種方式為主,玩家可以自主選擇不同的玩法體驗不同的劇情,如《塞爾達傳說:荒野之息》
第三,模塊化的敘事。模塊化的劇情指游戲設計師在不同的劇情節點設置了不同的點讓玩家選擇,在自由度上處于嵌入式敘事與應變性敘事之間,具有更多的選擇與結局,在主線劇情之外有更為豐富的支線劇情,如《巫師3》。
這些多樣的敘事方法為傳統的敘事媒體帶來了更讓人沉浸的體驗。可以說,不論我們是否承認游戲與敘事有直接關聯,游戲都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敘事媒介。但需要注意的是,游戲雖包含在互動的概念之下,但是不能簡單地將互動敘事學理解為“游戲敘事學”。互動敘事學包含了互動小說、互動電影等多種數字媒體形式,并非單指游戲,它的范圍更廣。
那么,是否可以簡單地將游戲與敘事直接綁定在一起呢?這是個難以得到統一認識的論題,無論是游戲學派還是敘事學派都給出了自己的理論證明,站在他們的角度,這些也都是成立的。Henry Jenkins在Game Design as Narrative Architecture中提出:雖然分歧巨大,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得到一些共識:第一,不是所有的游戲都敘事;第二,很多游戲都會有敘事的意愿;第三,敘事分析并非游戲所必需的,即使對敘事學本身來說也是如此;第四,游戲的體驗要比一個故事的體驗更為豐富;第五,如果一個游戲講故事,那么講述的方式不太可能和別的媒體使用相同的敘事方式。
游戲絕不僅僅是一個敘事的媒介,它帶來的體驗要遠比單純的閱讀或觀影更為豐富。游戲或者敘事的未來發展也絕不僅僅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那樣。同樣以《底特律:變人》為例,游戲除了選擇的支線之外,整個游戲流程就完全只是選擇操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將之歸納到純粹的游戲之列嗎?筆者更愿意認為,《底特律》是一個游戲性很棒的互動電影,甚至可以說假如一部電影愿意拍出這么多的支線結局的話,那么不需要游戲這個載體它也能存在。
再以Playdead工作室出品的Inside來說,其所運用的敘事手段也完全有別于傳統的游戲、文學或電影。游戲的整個流程中并沒有出現文字、對話、動畫這種傳統的敘事方式,游戲場景通過美術設計所展現出的形式感與氛圍帶來了更優秀的情感體驗,設計者并不試圖通過直接的文字或動畫來表現自己的理念,解密的方式、場景與關卡的設計都巧妙地與故事主題、游戲機制相融合,鼓勵玩家借助想象去主動生產故事。
對于游戲與敘事,游戲“重新定義了敘事的表達方式”,認為游戲與敘事沒有任何區別則忽略了兩者的本質屬性,雖然這種區別并不明顯。敘事與游戲機制也并不是對立的,游戲學這門學科是跨學科綜合性的。
參考文獻:
[1] Ernest Adams . Three Problems For Interactive Storytellers[J]. Gamasutra,1999.
[2] Greg Costikyan . Where Stories End and Games Begin[J]. Game Developer,2000:4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