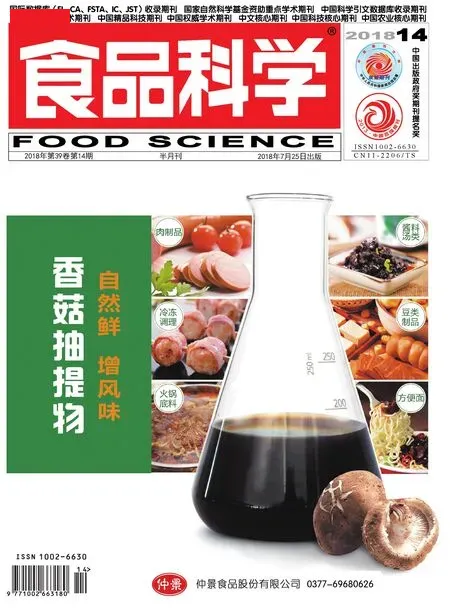葡萄園土壤中釀酒酵母的分離鑒定及其發(fā)酵葡萄酒香氣成分分析
馮 濤,王旭增,王一非,孫 敏,姚凌云,徐志民
(1.上海應(yīng)用技術(shù)大學(xué)香料香精技術(shù)與工程學(xué)院,上海 201418;2.路易斯安拉州立大學(xué)食品科學(xué)系,美國 路易斯安那 巴吞魯日 70802)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葡萄酒逐漸在我國被普遍接受。同時(shí)出于綠色釀造和健康飲用的理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己在家中釀制葡萄酒,不僅能夠享受到綠色釀造的樂趣,還能品嘗到天然無添加的葡萄酒。家庭自釀多采用鮮食葡萄作為釀酒原料,酵母菌是生產(chǎn)葡萄酒的主要微生物菌群,是葡萄酒發(fā)酵過程中的關(guān)鍵因素,葡萄酒的釀造都是在酵母菌的作用下,采用自然發(fā)酵或者純種發(fā)酵,將葡萄原料中的各種潛在成分在酒中充分表現(xiàn)出來[1],因此葡萄酒酵母篩選歷來很受重視[2]。
目前的市售酵母中,針對鮮食葡萄發(fā)酵的家釀葡萄酒酵母種類較少,鮮食葡萄釀酒酵母菌株主要篩選自葡萄的果皮、土壤或是在葡萄自然發(fā)酵過程中篩選。徐建東等[3]從鮮食葡萄龍眼的葡萄皮及種植土壤中篩選出一株低醇酵母菌株F12,譚海剛等[4]從鮮食葡萄紅提等的葡萄園土壤中篩選出耐乙醇酵母菌株QY29,葛含靜[5]從鮮食葡萄戶太八號(hào)的醪液中分離出起酵快、發(fā)酵穩(wěn)定的酵母菌株S37,以上篩選出的酵母菌株均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在多年種植鮮食葡萄的園區(qū)中,有多種天然酵母與其相伴而生,經(jīng)長期的自然選擇和進(jìn)化演變,逐漸形成一批適合鮮食葡萄發(fā)酵的天然優(yōu)勢酵母,從中可以篩選出具有優(yōu)良品質(zhì)的鮮食葡萄酒酵母[6],這種具有獨(dú)特風(fēng)格的釀酒酵母顯得非常重要[7]。在葡萄栽培以及釀酒歷史悠久的歐洲,尤其是在名酒產(chǎn)地,目前仍然利用優(yōu)越的天然酵母群進(jìn)行發(fā)酵。我國的各大葡萄酒廠十分重視自己酵母的選育,如山東煙臺(tái)張?jiān)a劸乒具x育的7318、7448酵母等[8],郭志剛等[9]利用都善紅葡萄分離篩選葡萄酒酵母,發(fā)酵都善紅葡萄釀制成了具有特色的名酒“樓蘭古酒”。這些酵母為葡萄酒特色和品牌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10]。
中國的鮮食葡萄產(chǎn)量已連續(xù)多年為世界第一,但是鮮食葡萄加工業(yè)相對落后,對釀酒上的研究更少[11],除了鮮食葡萄皮薄肉質(zhì)硬、出汁率低以及含糖量低等因素外,缺乏針對鮮食葡萄發(fā)酵的釀酒酵母[12],同樣是鮮食葡萄發(fā)酵酒的香氣和風(fēng)味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篩選出一種針對鮮食葡萄酒發(fā)酵、產(chǎn)生優(yōu)良香氣的釀酒酵母尤為必要。因此從天然酵母中,篩選出針對鮮食葡萄發(fā)酵的家釀葡萄酒酵母是一項(xiàng)十分有意義和有價(jià)值的工作。本實(shí)驗(yàn)通過從葡萄種植土壤中對鮮食葡萄釀酒酵母的篩選方法和釀造酒的香氣分析進(jìn)行探索,為今后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積累經(jīng)驗(yàn)和理論支持。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與試劑
醉金香葡萄購于上海松江區(qū),采摘于2016年8月份,含糖量16.8%,總酸0.61%,平均粒質(zhì)量13 g。土壤樣品分別由上海奉賢、上海崇明、上海松江、湖北武漢、浙江紹興、山東菏澤、遼寧鐵嶺等地葡萄園土壤中采集得到。
安琪葡萄酒酵母 上海市安琪酵母有限公司;帝伯仕葡萄酒酵母 山東煙臺(tái)帝伯仕自釀機(jī)有限公司;GBS酵母DNA試劑盒 南京捷倍思生物基因技術(shù)有限公司。
馬鈴薯葡萄糖瓊脂(potato dextrose agar,PDA)培養(yǎng)基:馬鈴薯9.0 g/L,葡萄糖22.0 g/L,瓊脂13.0 g/L,按上述配方配好后加熱溶解,pH 6.5±0.2,121 ℃滅菌20 min;酵母浸出粉葡萄糖(yeast peptone dextrose,YPD)培養(yǎng)基:酵母膏1%,蛋白胨2%,葡萄糖2%,按上述配方配好后加熱溶解,pH 6.5±0.2,121 ℃滅菌20 min。
1.2 儀器與設(shè)備
LDZX-KBS高壓蒸汽滅菌鍋 上海申安醫(yī)療器械廠;DHP-9052型電熱恒溫培養(yǎng)箱 上海益恒實(shí)驗(yàn)儀器公司;SPX-150B-Z恒溫培養(yǎng)箱 上海博迅有限公司;DHG-9145A恒溫干燥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GL-21B高速冷凍離心機(jī) 上海安亭科學(xué)儀器廠;SelectCycler II聚合酶鏈?zhǔn)椒磻?yīng)(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儀 上海巴玖實(shí)業(yè)有限公司;7890A/5975C型氣相色譜-質(zhì)譜(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聯(lián)用儀 美國Agilent公司。
1.3 方法
1.3.1 葡萄園土壤中釀酒酵母的分離活化
富集酵母菌[13]:取土壤樣品10 g,加入到200 mL無菌水中,在28 ℃的恒溫培養(yǎng)箱中200 r/min培養(yǎng)20 min。
酵母菌分離:取上述培養(yǎng)液1 mL進(jìn)行梯度稀釋,分別吸取10-3、10-4和10-5梯度的稀釋液200 μL涂布于PDA平板[14],在28 ℃恒溫培養(yǎng)箱中培養(yǎng)48 h后挑取菌落染色鏡檢,篩選酵母菌,經(jīng)2~3 次劃線分離[15],得到酵母純培養(yǎng)物。
酵母菌活化:將上述酵母純培養(yǎng)物接種至YPD液體培養(yǎng)基中28 ℃振蕩培養(yǎng)24 h,培養(yǎng)物6 000 r/min離心10 min[16],重復(fù)兩次得到酵母,4 ℃冷藏備用。
1.3.2 26S rDNA鑒定
利用GBS酵母DNA提取試劑盒提取酵母菌的DNA,以DNA基因組為模板,以真菌26S rDNA D1區(qū)通用引物NL1(5’-GCATATCAATAAGCGGAGGAAAAG-3’)和NL4(5’-GGTCCGTGTTTCAAGACGG-3’)為引物,進(jìn)行PCR擴(kuò)增[17]。
PCR擴(kuò)增采用50 μL體系:ddH2O 18 μL,10 μmol/L引物NL12 μL,10 μmol/L引物NL42 μL,dNTPs(2.5 mmol/L)1 μL,5 U TaqE酶25 μL,酵母菌DNA模板2 μL。
PCR擴(kuò)增程序:95 ℃預(yù)變性10 min;94 ℃變性1 min;54 ℃退火1 min;72 ℃延伸1.5 min,36 個(gè)循環(huán);最后72 ℃延伸5 min。
擴(kuò)增產(chǎn)物進(jìn)行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測序并與NCBI數(shù)據(jù)庫進(jìn)行BLAST同源性序列比對分析[18]。根據(jù)同源序列的比對結(jié)果,從GenBank數(shù)據(jù)庫下載相應(yīng)模式菌株,利用MEGA 7.0軟件計(jì)算菌株進(jìn)化距離[19],運(yùn)用NJ(Neighbor-Joining)法構(gòu)建分離出的生香酵母菌的系統(tǒng)發(fā)育樹。
1.3.3 葡萄汁發(fā)酵
稱取1 kg“醉金香”白葡萄,洗凈破碎后得到葡萄醪,加入1 L發(fā)酵罐內(nèi)并添加調(diào)硫片(200 mg/L)。將發(fā)酵罐于20~25 ℃靜置,使葡萄皮中的呈香、呈味物質(zhì)浸漬到葡萄醪,24 h后用比重計(jì)(量程1.0~1.1)和溫度計(jì)分別測其相對密度和溫度,并測定其清汁糖度,根據(jù)所測糖度補(bǔ)充葡萄糖,將糖度調(diào)節(jié)至25 °Brix[20]。將酵母分別按照107CFU/mL接入葡萄醪,于28 ℃恒溫培養(yǎng)箱中發(fā)酵,每組實(shí)驗(yàn)重復(fù)3 次。每天定時(shí)測定葡萄醪的相對密度變化,當(dāng)酒液的相對密度接近0.997連續(xù)2 d保持不變即視為發(fā)酵完成,終止發(fā)酵[21],將酒液進(jìn)行澄清,過濾處理后放入低溫環(huán)境(12 ℃)貯存。發(fā)酵結(jié)束后,根據(jù)GB/T 15038—2006《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中的基本指標(biāo),測定葡萄酒樣的基本理化指標(biāo)(總糖含量、總還原糖含量、乙醇體積分?jǐn)?shù)、總酸含量、總揮發(fā)酸含量、總二氧化硫含量)。
1.3.4 感官評定
建立感官評定小組,由12 位經(jīng)過培訓(xùn)的人員[22](6 男6 女,年齡范圍為25~30 歲)組成,培訓(xùn)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ISO13300-2-2006[23]制定,評定方法按照J(rèn)ackson[24]的感官環(huán)境和操作步驟進(jìn)行,并引用Rutan等[25]的感官分析方法,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建立對葡萄酒的呈香感官描述(表1)。評定方法為9 分嗜好法,0~9 分表示風(fēng)味逐漸增強(qiáng),其中0 分代表沒有被察覺,9 分代表風(fēng)味強(qiáng)度最大。每種發(fā)酵酒感官評定3 次,取平均值。

表1 葡萄酒香氣評價(jià)[25]Table1 Flavor descriptions of wine
1.3.5 發(fā)酵酒中揮發(fā)性香氣成分的提取檢測
固相微萃取[26]:取5 mL發(fā)酵酒于15 mL頂空瓶中恒溫(55 ℃)水浴,并向頂空瓶中加入20 μL 2-辛醇(600 mg/L),用蓋子密封后插入75 μL CAR/PDMS萃取頭,保持30 min。
G C條件[27]:H P-I N N O WA X毛細(xì)管色譜柱(60 m×0.25 mm,0.25 μm);初始溫度40 ℃,保留2 min,以5 ℃/min的速率升至230 ℃,保留15 min;檢測器溫度250 ℃;載氣He,流速1 mL/min,不分流進(jìn)樣。MS條件:四極桿溫度150 ℃;離子源溫度230 ℃;接口溫度250 ℃;電子電離源;電子能量70 eV;質(zhì)量掃描范圍10~450 u。
定性分析:利用全離子掃描質(zhì)譜圖[28],參考NIST11譜圖庫資料進(jìn)行分析,并與文獻(xiàn)報(bào)道的保留指數(shù)(retention index,RI)相比較,或與同條件下該物質(zhì)的標(biāo)準(zhǔn)品的RI和MS圖像比較,以確定某物質(zhì)。定量分析:利用2-辛醇內(nèi)標(biāo)法進(jìn)行定量。計(jì)算如式(1)、(2)所示:

式中:tx為揮發(fā)性物質(zhì)的保留時(shí)間/min;tz為與揮發(fā)性物質(zhì)碳原子屬相同的正構(gòu)烷烴的保留時(shí)間/min;z為揮發(fā)性物質(zhì)的碳原子數(shù)。

式中:wi為揮發(fā)性物質(zhì)含量/(mg/kg);ms為內(nèi)標(biāo)物含量/μg;Ai為揮發(fā)性物質(zhì)峰面積;As為內(nèi)標(biāo)物的峰面積;m0為發(fā)酵酒樣品質(zhì)量/g。
1.4 數(shù)據(jù)分析
通過測定香氣物質(zhì)的香氣活力值(odour active value,OAV)評定發(fā)酵酒的關(guān)鍵香氣成分。OAV為特定化合物樣品氣味的重要指標(biāo),其數(shù)值等于化合物的濃度與水中的嗅覺閾值的比值[29]。
分析OAV大于1的化合物與酵母發(fā)酵酒的相關(guān)性,采用Unscrambler 9.7進(jìn)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PCA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進(jìn)行中心化與標(biāo)準(zhǔn)化(1/Sdev)處理,顯著差異水平取P小于0.05[30],模型采用Full Cross-Validation進(jìn)行校正。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釀酒酵母的分離篩選
從各地的葡萄園土壤樣品中經(jīng)過多次分離純化,得到16 株菌,其中3 株為霉菌(Mould),3 株為放線菌(Actinomycesbovis),6 株為熱帶念珠菌(C.tropical),通過對菌株觀察和鏡檢,有4 株初步確定為酵母菌株(圖1),以下簡稱S1、S2、S3、S4。從分離結(jié)果可以看出(圖1),酵母菌菌落都為圓形,乳白色,其中S2、S3、S4三株菌表面不光滑,S1表面光滑。細(xì)胞的生殖方式都為芽殖,S1、S3兩株菌具有圓形和橢圓形兩種形態(tài),S2、S4只有橢圓形態(tài)。


圖1 酵母菌株菌落形態(tài)及細(xì)胞形態(tài)Fig.1 Colony and cell morphology of four yeast isolates
2.2 酵母菌屬的鑒定結(jié)果

圖2 S1、S2、S3酵母系統(tǒng)發(fā)育樹Fig.2 S1, S2, S3 yeast phylogenetic tree
將S1、S2、S3、S4這4 株酵母測序數(shù)據(jù)在GenBank數(shù)據(jù)庫中進(jìn)行同源序列搜索匹配(BLAST),建立系統(tǒng)發(fā)育樹[31]。S1、S2、S3結(jié)果如圖2所示,菌株S1和釀酒酵母(S. cerevisiae strain S2-39)具有較高的同源性,相似度為99%;菌株S2和釀酒酵母(S. cerevisiae strain NL5)具有較高的同源性,相似度為99%;菌株S3和釀酒酵母(S. cerevisiae strain CTBRL87)具有較高的同源性,相似度為100%。菌株S4結(jié)果如圖3所示,異常威克漢姆酵母(Wickerhamomyces anomalus culture-collection CBS:262)具有較高的同源性,相似度為100%。結(jié)合以上比對結(jié)果,將S1、S2、S3三株酵母鑒定為釀酒酵母(S. cerevisiae),將S4鑒定為異常威克漢遜酵母(W. anomalus)。

圖3 S4酵母系統(tǒng)發(fā)育樹Fig.3 Phylogenetic tree of yeast S4
2.3 發(fā)酵酒的主要理化指標(biāo)分析
比較不同的酒樣可以看出,不同酵母發(fā)酵的葡萄酒各項(xiàng)指標(biāo)均存在差異(表2),乙醇體積分?jǐn)?shù)從高到底依次為S3>S1>S4>S2>安琪>帝伯仕。殘?zhí)橇浚偺呛浚┛梢苑从辰湍笇μ堑睦媚芰Γ诔跏继嵌认嗤那闆r下,發(fā)酵結(jié)束后殘?zhí)橇康停f明酵母對糖的轉(zhuǎn)化利用率高,則發(fā)酵能力強(qiáng)[32]。由表2可以看出,總糖含量和總還原糖含量均與乙醇體積分?jǐn)?shù)相對應(yīng),表明菌株利用糖類的能力較強(qiáng),發(fā)酵徹底。總酸含量可以判定酵母的產(chǎn)酸能力,酸類物質(zhì)是酒中的主要呈味物質(zhì),其含量對酒的色澤和風(fēng)味具有一定的影響[33]。6 種酒樣總酸含量為S4>S3>S2>安琪>S1>帝伯仕,總揮發(fā)酸含量為S1>S4>S2>帝伯仕>S3>安琪,說明菌株產(chǎn)酸水平高于商業(yè)酵母。二氧化硫作為抗氧化劑和微生物抑制劑,在葡萄酒發(fā)酵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34]。但是過量的二氧化硫會(huì)破壞食品中的營養(yǎng)物質(zhì),并對人體造成危害[35]。經(jīng)過檢測(表2),發(fā)酵酒中總二氧化硫含量均符合GB/T 15038—2006(≤250 mg/L)。
初步估算零層板厚度為250mm,可以作為上部結(jié)構(gòu)嵌固端考慮,因此,上部模型可以將-0.5m定為嵌固端進(jìn)行結(jié)構(gòu)計(jì)算。在確定各主受力構(gòu)件尺寸之后,可以進(jìn)行下一步基礎(chǔ)設(shè)計(jì)。

表2 理化指標(biāo)分析結(jié)果Table2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of wines
2.4 發(fā)酵酒揮發(fā)性香氣成分分析
利用頂空固相微萃取GC-MS聯(lián)用技術(shù)對篩選出的4 種酵母發(fā)酵酒進(jìn)行揮發(fā)性成分分析,并用市售安琪酵母和帝伯仕酵母發(fā)酵酒作為對比。共檢測到45 種共8 大類香氣化合物(表3),包括酯類15 種,醇類12 種,萜烯類5 種,醛類5 種,酸類4 種,酮類3 種,酚類2 種。6 種發(fā)酵酒中共有的揮發(fā)性化合物為:乙酸乙酯、丁酸乙酯、己酸乙酯、辛酸乙酯、乙酸異戊酯、異丁醇、異戊醇、苯乙醇,2,3-丁二醇、2-辛酮等,可鑒定為6 種發(fā)酵酒中的主要香氣物質(zhì),與文彥[36]的研究相符合。

表3 6 種發(fā)酵酒的揮發(fā)性成分及相對含量Table3 Volatile components and their contents in wines

續(xù)表3
由表3可知,S1發(fā)酵酒中共檢測出33 種揮發(fā)性化合物,其中酯類11 種,醇類9 種,酸類4 種,醛類3 種,酮類3 種,烯萜類2 種,酚類1 種,比安琪酵母發(fā)酵酒多10 種(十二酸乙酯、十四酸乙酯、十六酸甲酯、十六酸乙酯、苯乙酮、香葉基丙酮、檸檬烯E、β-柏木烯、2-甲基丁醇、2-乙基己醇),比帝伯仕酵母發(fā)酵酒多5 種(乙酸異丁酯、十四酸乙酯、十六酸甲酯、壬醛、癸醛)。酯類物質(zhì)產(chǎn)生于酵母或細(xì)菌代謝及葡萄酒陳釀,賦予葡萄酒果香和花香[37],十四酸乙酯具有甜奶油的氣味,十六酸乙酯具有水果和香草的氣味[38],乙酸異丁酯具有生梨和覆盆子的香氣[39]。醛和酮主要是由酸的脫羧和醇的氧化形成[40],香葉基丙酮具有花香和熱帶水果香的氣息[41],壬醛具有瓜香和堅(jiān)果香,癸醛具有橘皮的香味。
S2發(fā)酵酒中共檢測出38 種揮發(fā)性化合物,為6 種發(fā)酵酒中物質(zhì)種類最多的酒樣。其中酯類13種,醇類10 種,酸類4 種,醛類3 種,酮類2 種,烯萜類4 種,酚類2 種,比安琪酵母發(fā)酵酒多15種(十二酸乙酯、十四酸乙酯、十六酸甲酯、十六酸乙酯、2-甲基丁醇、2-乙基己醇、壬醛、香葉基丙酮等),比帝伯仕酵母發(fā)酵酒多10種(乙酸異丁酯、十四酸乙酯、十六酸甲酯、乙酸苯乙酯、檸檬烯E、β-柏木烯、2,6-二叔丁基對甲酚等)。烯萜類和雜環(huán)類物質(zhì)的含量較低,但對增加葡萄酒風(fēng)味的豐富性起重要作用[42],檸檬烯E屬單萜類化合物,具有類似檸檬的味道[43]。多酚類化合物是葡萄中重要的抗氧化類化合物[44],2,6-二叔丁基對甲酚具有輕度樟腦氣味。
相對于商業(yè)酵母,S3發(fā)酵酒中庚酸乙酯、乙酸異丁酯、乙醇、丙醇、正己醇、乙酸含量明顯高于商業(yè)酵母,尤其是乙醇含量,居6 種酵母發(fā)酵酒之首;S4發(fā)酵酒中苯乙醇和乙酸含量明顯高于商業(yè)酵母,其乙酸含量為6 種發(fā)酵酒中最高。
結(jié)合以上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相對于商業(yè)酵母,篩選酵母發(fā)酵產(chǎn)生的獨(dú)有的化合物,尤其是S1和S2發(fā)酵酒中,均包括十二酸乙酯、十四酸乙酯、十六酸乙酯、2-甲基丁醇、2-乙基己醇、壬醛、癸醛、檸檬烯E、β-柏木烯等,說明從土壤中篩選的釀酒酵母,發(fā)酵鮮食葡萄產(chǎn)生更多以上化合物。
2.5 關(guān)鍵揮發(fā)性化合物OAV
僅通過香氣物質(zhì)的種類和相對含量,無法準(zhǔn)確鑒定各種化合物對發(fā)酵酒香氣的貢獻(xiàn)大小,因此引入OAV,進(jìn)一步探究發(fā)酵酒中的關(guān)鍵揮發(fā)性香氣物質(zhì)。Allen等[45]研究發(fā)現(xiàn)OAV大于1的化合物對酒的風(fēng)味貢獻(xiàn)顯著,且OAV越大對香氣貢獻(xiàn)程度越高,但OAV小于1的物質(zhì)并非對香氣不起作用,這些物質(zhì)往往起協(xié)香作用。對GC-MS的檢測結(jié)果計(jì)算OAV,結(jié)果如表4所示,共有15 種物質(zhì)OAV大于1,被認(rèn)為是發(fā)酵酒香氣的關(guān)鍵組分,其中8 種物質(zhì)OAV大于10,5 種物質(zhì)(丁酸乙酯、己酸乙酯、庚酸乙酯、辛酸乙酯、癸酸乙酯)OAV大于100,2 種物質(zhì)(丁酸乙酯、癸酸乙酯)OAV大于1 000。這些物質(zhì)被認(rèn)為是發(fā)酵酒中必不可少的香氣物質(zhì),且其全部為酯類,說明酯類是發(fā)酵葡萄酒中的特征香氣物質(zhì),與Styger等[46]的研究結(jié)果一致。

表4 6 種酵母發(fā)酵酒中揮發(fā)性物質(zhì)的OAV(OAV>1)Table4 OAV of volatile substances in six wines (OAV > 1)
2.6 揮發(fā)性化合物主成分相關(guān)性分析
為進(jìn)一步明確6 種酵母發(fā)酵葡萄汁香氣成分的差異,以及香氣物質(zhì)的呈香關(guān)系,采用PCA模型對實(shí)驗(yàn)結(jié)果進(jìn)行相關(guān)性分析。如圖4所示,第1象限中,與S1發(fā)酵酒香氣物質(zhì)相關(guān)的是癸酸乙酯、苯乙醇、辛酸、癸酸,這些物質(zhì)的香氣描述符合花香、玫瑰香、甜水果香等[49],與其在S1發(fā)酵酒中OAV較高相對應(yīng);第2象限中,對S2發(fā)酵酒貢獻(xiàn)較大化合物有丁酸乙酯、庚酸乙酯等,這些物質(zhì)具有葡萄、香蕉、櫻桃的果香氣味[37],同時(shí)在S2發(fā)酵酒中具有較高的OAV。以PC1為基準(zhǔn),S1發(fā)酵酒明顯區(qū)別于其他酒樣;以PC2為基準(zhǔn),S2明顯區(qū)別于其他酒樣[50],說明S1和S2發(fā)酵酒的香氣評價(jià)最好。S3發(fā)酵酒和安琪酵母發(fā)酵酒PCA結(jié)果接近,同時(shí)對兩者貢獻(xiàn)較大的香氣物質(zhì)有乙酸乙酯(葡萄和櫻桃香)、丁酸乙酯(蘋果香)、乙酸異戊酯(香蕉香),說明兩種發(fā)酵酒的果香,尤其是蘋果、葡萄以及香蕉的香氣比較接近[51]。

圖4 15 種OAV大于1的揮發(fā)性化合物對前兩個(gè)主成分的PCA圖Fig.4 PCA of 15 volatile compounds with OAV greater than1 to the fi rst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圖5 6 種酵母發(fā)酵酒香氣評價(jià)圖Fig.5 Radar map of aroma evaluation of6 wines
3 結(jié) 論
從上海崇明、浙江紹興、山東菏澤、武漢4 個(gè)地區(qū)的葡萄園土壤中成功分離出4 株酵母菌,通過光學(xué)顯微鏡觀察對比,并用26S rDNA D1/D2區(qū)域序列比對及構(gòu)建系統(tǒng)發(fā)育樹分析,結(jié)果表明:S1、S2、S3為釀酒酵母,S4
為異常威克漢遜酵母。將4 株酵母對同一種鮮食葡萄醉金香進(jìn)行發(fā)酵,并用市售安琪酵母和帝博仕酵母發(fā)酵酒作為對照。對發(fā)酵酒的揮發(fā)性香氣成分使用頂空固相微萃取進(jìn)行收集,并結(jié)合GC-MS聯(lián)用儀進(jìn)行分析,共檢測到45 種共8 大類香氣成分,包括醇類12 種,酯類15 種,烯萜類5 種,醛類5 種,酸類4 種,酮類4 種,酚類2 種。相對于商業(yè)酵母發(fā)酵酒,S1發(fā)酵酒能夠產(chǎn)生更高含量的辛酸乙酯、癸酸乙酯、十二酸乙酯,S2發(fā)酵酒中癸酸乙酯、苯乙醇、辛酸、癸酸、香葉基丙酮、2,6-二叔丁基對甲酚、4-乙烯基-2-甲氧基苯酚含量較高,S3發(fā)酵酒具有高的乙酸乙酯含量和乙醇含量,S4發(fā)酵酒具有更高的乙酸含量。本實(shí)驗(yàn)探究了篩選酵母和商業(yè)酵母在發(fā)酵鮮食葡萄醉金香產(chǎn)香方面的差異,為今后篩選鮮食葡萄發(fā)酵酵母的方向作出了展望,也為對鮮食葡萄的基因改良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