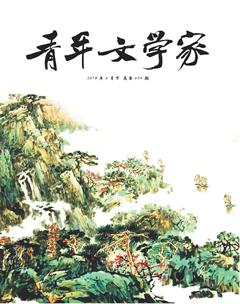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摘 要:從弗萊的圣經原型批評與霍米巴巴的混雜理論視角出發,解析《一粒麥種》中水的象征意義,具體表現為小說中水意象的繼承性、矛盾性、反抗性。小說中的水繼承《圣經》里力量、重生和懲罰的含義,同時也體現和《圣經》水意象之間差異性。差異的重復性書寫進而揭示受殖者在矛盾狀態中顛覆的可能性,即受殖者在矛盾含混的混雜文化中實現對殖民權威的抵抗。
關鍵詞:水意象;繼承性;矛盾性;反抗性
作者簡介:袁劉芳(1993-),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師范大學2016級研究生碩士,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8--02
一、引言
恩古吉·瓦·提安哥是肯尼亞著名的小說家和文學評論家,其作品是非洲反殖民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粒麥種》通過寫叛徒莫果在肯尼亞獨立慶祝大會前發生的故事,揭示了肯尼亞人對待殖民主義者采取的不同態度。小說設置懸念和伏筆,采用意識流手法以及借用《圣經》故事,著重刻畫了英雄基希卡和叛徒莫果。其中,《圣經》中的水意象作為一個重要載體貫穿了整個故事,和人物命運息息相關。作者巧妙借用水的特性與意象展現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
二、《圣經》與水:水能載舟
水意象頻繁出現在恩古吉的《一粒麥種》中,構成一個潛在的原型模式。這一模式主要受到西方殖民者文化代表《圣經》的影響。
水作為生命之源,孕育著生命力和創造力。《創世紀》中神創世除了第四天創造日月星辰沒有提到水,其余的都提及到水。之后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創世紀》,1:2)再到上帝創造的伊甸園,里面有魚有蝦有水草,滋潤著園里的生物同時還分四道流出去。此處,水在上帝手里展現其力量與不凡,同時也給世界帶去生機。其次,水和生命息息相關的聯系還出現在摩西出生的時候。為了躲避法老的追殺,摩西母親將他藏到了河水邊的蘆葦叢中,無意中正在洗澡的法老女兒所救,并取名“摩西”,希伯來語表示“從水中拉出來”。在《一粒麥種》中,水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在第一章作者描寫了莫果去到挖地的情景。土地上空蕩蕩的,“一切東西都顯得格外干枯凋萎”[1]8,他舉起鋤頭挖地,“一粒塵土掉進他的左眼……揉了揉眼睛,眼睛疼得流出了淚水”[1]8。面對毫無生機的土地,莫果自問在緊急狀態以前土地對他的那種魅力哪里去了。干枯的裂地,流出的淚水。借挖地之景表達了飽受殖民摧殘的肯尼亞人現狀。之后生命之源出現了,威雅基帶領人們拿起了武器,他“流出的鮮血里,有一顆種子在發芽生長,于是產生了一個政黨。這個政黨的主要力量來自于這片土地的血肉聯系”[1]15。澆灌土地的水此刻化成了鮮血去滋潤土地。緊接著,像摩西一樣引領民眾前往迦南地的基希卡出現了:“基希卡說到流血時,簡直就像說到從河里汲水一樣輕松”[1]19。水給予他們力量去與殖民者抗衡,一滴接一滴的水澆灌著肯尼亞人民的自由之樹。
其次,水象征洗禮與再生。據《新約圣經》記載:耶穌曾三次顯示其神性,第二次受洗禮時,“圣靈”和鴿子降在他頭上,顯示他為上帝的兒子。經過洗禮的耶穌呈現出新的身份,救世主。一方面,水在這里有洗滌功能,洗刷人類身上的罪;另一方面,洗禮意味著舊生活的結束與新生活的開始。水的重生還體現在上帝用大洪水毀滅世界。洪水摧毀一切生靈的同時,也凈化了萬物。小說主要體現中,莫果為了活命背叛基希卡,罪惡一直糾纏他。他渴望能接受洗禮重新開始新的生活。除此外,當描寫到獨立后的肯尼亞城市時,街上人群指手畫腳談論一股股不住噴射的泉水成為一道特別的風景。展現了肯尼亞遭受殖民者摧殘后即將來臨的新生活。除此外,當人們在慶祝獨立大會時,眾人說落雨是保佑了得來不易的自由。這象征著整個肯尼亞獨立后的重生,雨水的出現是整個民族新生活的開始。但這時的莫果卻一個走在大雨中,想要借此洗刷罪惡。到此,《一粒麥種》展現水能載舟的能力。除了繼承《圣經》中水所代表的力量這一點,小說也展現出水的破壞力。
三、《圣經》與水:水能覆舟
小說中的水意象除了上述對《圣經》原型的繼承,另一個主要的象征就是罪與罰。這也是小說中一個明顯的隱喻。弗萊就說過“洪水本身既可以從神憤怒和報復的意象意義上看成是惡魔意象,也可以看成拯救意象”[2]191。小說中的莫果投入敵人懷抱,充當了殖民主義者的幫兇,背離了信任他的肯尼亞民眾。開篇作者設置懸念到底是誰背叛了基希卡,但是最后結尾才揭曉答案。這一過程中,水多次出現暗示莫果的恐慌與不安,更重要的是指向莫果所犯的罪和將要面對的懲罰。無論白天黑夜,還是獨處或者面對當地人,他都無法擺脫或者忽視無處不在的水。這也解釋了他為什么會老是注意到河邊的女人們,但是又不靠近。因為河水時刻提醒著過去的罪行。“莫果想不起錐刺皮肉的釘子鞋,卻始終記得潑在水泥地上的水”[1]213。比起肉體的傷,內心惶恐使他無法平靜。
到這里讀者們會發現,雖然作者采用意識流手法將水意象穿插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卻用這些分散的水珠一點一點凝聚了整部《圣經》的水原型。而作者真正的用意在于水折射出了繼承的雙重性和矛盾的雙重性。繼承雙重性體現在小說繼承水的積極意義,同時還有水的消極意義。“大洪水既是邪惡的摧毀力量,又是拯救人類重新開的契機”[3]。水對莫果是罪惡的象征,對基希卡卻是民族獨立的希望;水對莫果是懲罰的枷鎖,對肯尼亞人是對得來不易自由的賜福。這也正如弗萊說的那樣,水可以 “看成是惡魔意象,也可以看成拯救意象”[2]191。因而,水的積極或者否定,取決于站在誰的角度來看,恩古吉就洞悉到這一點。當文中同時展現水的正面與反面形象,就彰顯出了其矛盾性。而且這一矛盾性是雙重的:一方面透露出《圣經》的矛盾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圣經》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矛盾性。滋潤土地的鮮血在帶給肯尼亞獨立的同時,也帶去災難。鮮血成了殖民者暴行的見證,水成了與《圣經》連接的載體。事實上,水除了繼承西方文化的象征《圣經》,更重要的是利用水象征的矛盾性來指向西方殖民者。
四、《圣經》與殖民地:水的矛盾性
弗萊在《偉大的代碼—圣經與文學》中提到,各種意象構成了啟示世界的一部分。這個用想象力創造出來的理想世界,是人類一直追尋的現實世界,“也是圣經作為一種 ‘啟示形式向人們展示的世界”[2]182。在向人類展示未來藍圖的時候“我們必須把這個啟示結構放在它的語境之中”[2]182。因而,當我們把小說中的水與《圣經》結合時,不能忽略小說本身的殖民語境來孤立的談論水的意義。所以有必要將水意象放到《圣經》所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肯尼亞人的關系中去探究。水作為上帝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用來造物、洗禮、施恩或者懲罰,都充分發揮了連接上帝與世人的重要載體。恩古吉借用這一載體意義,將水指向圣經。而《圣經》是殖民文化的象征與標志,并且在殖民教化過程中占據了主要的地位。它要求受殖民者模擬與接受的同時還蘊含了西方權威的統治與欲望。但是當這本象征著殖民者身份的書放到被殖民地肯尼亞時,肯尼亞人巧妙地將“那本英語書”混雜了,使得殖民權威處于含混矛盾的狀態,進而實現顛覆的可能性。
對于殖民者來說,巴巴認為殖民主體身份的內部原本矛盾導致了其不穩定性,這根源于殖民者主體自我設定的穩定身份是建立在對殖民地的征服、播撒或者延異中體現出來的。這意味著“宗主國文化的殖民地征服與旅行過程就是一個宗主國文化的原初身份被他者這介入、自身不斷被他者化延遲的‘差異的重復的不穩定過程”[4]82。《一粒麥種》重復了圣經中水的原型,但卻有別于它。因為作者更多的映射是彰顯出水的矛盾性。除此外,“殖民者主體身份的不穩定性還進一步受到受殖民者的‘模擬的擾亂”[4]88。矛盾狀態導致了殖民政策既同化又區別的矛盾的態度。西方殖民者自身的矛盾映射在小說中就成了水的矛盾性,這也是作者為什么在水的雙重繼承性背后隱匿了其雙重矛盾性。小說在繼承水雙層意象的同時又繼承水的矛盾,實際上,不論是對哪一方面都是在“模擬”《圣經》文化。模擬后的水除了是上帝的工具,也成了肯尼亞澆灌自由之樹的生命水。模擬的結果是產生了幾乎一模一樣卻又完全不同的肯尼亞人,正如從小接受殖民者《圣經》教育的基希卡反被培養成抗爭殖民者的革命英雄。因此,“模擬成了殖民權利與知識最難以捉摸同時又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5]。一方面,殖民者需要受殖民的模擬來確立至高無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從來不希望受殖者和自己完全一樣而取消了自己的殖民特權。而受殖者們一邊在崇拜或者模擬宗主國的同時,也發現了宗主國本身的弊端,在加以模擬后實現顛覆權利的可能性。在這個過程中,那本被永久物化了的英語書《圣經》,“顯示出殖民話語的弱點及其面對‘模擬性顛覆時的脆弱”[4]104。正如水意象顯示《圣經》自身矛盾性的同時也成了受殖民者模擬后的微觀抵抗方式,一滴一滴腐蝕了西方殖民權威的文化符號。
五、結語
《一粒麥種》中運用了大量水的意象來展現人物的心理活動,追其根源會發現與圣經原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然而這樣的聯系之中存在著某種差異性。這樣的差異性是由于殖民背景所導致的。作為被殖民文化的代言人,作者借《圣經》中水的矛盾性,加以繼承后,最終在繼承與矛盾中展現肯尼亞民族反抗的可能性。正是在這種差異的重復過程中,西方霸權地位被動搖,同時給受殖者帶來了顛覆的機會。
參考文獻:
[1]詹姆士·恩古吉. 一粒麥種[M]. 楊明秋,泗水,劉波林譯. 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
[2]諾思洛普弗萊. 偉大的代碼—圣經與文學[M]. 郭振益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3]劉意青. 《圣經》文學闡釋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3.
[4]羅如春. 后殖民身份認同話語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5]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