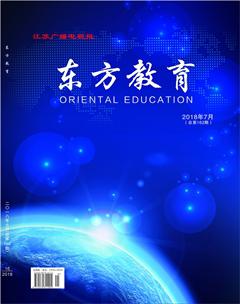墨子思想對當代德育的啟示
樊如一 常亞男
摘要:墨子思想中蘊含著科學的思維方式,他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后來覺得其禮煩擾,厚雜雇財,終于背周道而用夏政。“非樂”、“非命”、“非不扣不鳴”、“節用”等等觀點都是墨子對儒家學說與主張的懷疑與批判而提出的,但是墨子并非全然否定孔子,對于其有理而不可更動的觀點,墨子都會稱贊。而且,他在教育學生的過程中,不只是教授學生前單的理論知識,而是讓學生“名知”與“取如”相結合,引導其面向生活實踐,在知行合一的前據遠用辨別的邏輯思維進行說理,從而使學生觀念發生轉變。
關鍵詞:墨子思想;德育;兼愛
墨子姓墨名翟,據相關考證,大約出生于春秋末年孔子后孟子前,魯國人,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開創了墨子學說。墨子學說最具代表的就是“墨子十論,按《墨子》書的順序分別是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養、天志、明鬼、非樂、非命。”
1、墨子思想中值得當代德育借鑒的理論
1.1墨子思想的宗旨——實現天下相愛、尚同之政、尚賢使能
1.1.1兼相愛、交相利:愛無等差,視人如己
儒家是反對兼愛的,儒家講“仁愛”,最重“親親之殺”,他們所講的愛,是有層次、有厚薄、有分別的。但是墨子認為這種“仁愛”,尚無法祛除自私自利的心。墨子的“兼愛”,便是要祛除人們自私自利的心,他要人們以理智克服感情,視人身如己身。并不是很難做到的事,只是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兼愛的難以實行,并不在理論本身,而是在于人心;世人不愿吃自己兼愛的苦,卻情愿享別人兼愛的福。世人盡管反對兼愛但遇到利害關頭的時候,便要去選擇能夠兼愛的朋友和他共事。其實,世人如能祛除自私自利的心,視人如己,兼愛并不難行。天下一些人在言論上反對兼愛,在選擇時卻選取兼愛的朋友,這豈不是言行相反嗎?
世人反對兼愛的學說,但遇到利害關頭的時候,便要去選擇真能兼愛的人和他共事,而世人批評墨家的話,只說是“善而不可用”,真是沒道理!世人不愿兼愛于人,卻希望別人兼愛于己,這是墨學進行上的一處不可沖破的難關。
1.1.2尚同之政:上行下效
墨子認為在當時“亂”的原因有四個:一是義與不義的標準不統一。二是人倫的禮節混亂,這種禮節是什么呢?墨子說:“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三是沒有正長出來按義、禮的標準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即“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焉”。此外,墨子認為還有一個使天下亂的原因,即:在上者義,不了解人民的是非善惡,不能賞善罰暴。墨子說:“上之為治矣,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茍不明于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眾必亂。”。針對上述亂的原因墨子提出了:“是故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立為天子,便從事乎一同下之義。”。
1.1.3尚賢使能:培養兼士
如果賢人不在國君的身邊,就是不賢的人在左右了。不賢的人在左右,他們所稱贊的,不會是真賢明的人;他們所懲罰的,也不會是真兇惡的人。國君尊信這些人來治理國家,所賞的也一定不會是賢人,所罰的也一定不會是惡人。如果所賞不是賢人,所罰不是惡人,賢人就得不到獎勵,惡人就肆無忌憚。古時候的昏君:桀王、紂王、幽王、厲王,他們國家的滅亡,就是用一些不賢的人在左右的緣故。
1.2墨子思想的實現途徑——教育
1.2.1有教無類:大眾化的全民教育
墨子主張每個人都應當接受教育,即“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膚徒步之士”。他的教育對象不僅包括“王公大人”,也包括“農與工肆之人”,真正做到了“有道者勸以相教”。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與權利。他的這種教育思想體現了教育公平觀。與孔子提出的“有教無類”培養社會上層人物的精英教育思想相比,墨子的“有教無類”更為徹底、更接地氣,把受教育對象擴展到整個社會階層。他對教育對象受教前的品行及出身、天性、資質、等級、貧富、貴賤等并無明確規定,對所有自愿“修德進業者”均予以教誨。[1]
1.2.2不扣亦鳴:老師、學生共同努力
儒家主張君子若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而墨子作為一個積極的力行主義者,反對儒家的這種守舊的行事原則,他將人比作鐘,認為如果沒有外力的干預,個人是不會主動的去學習的,因此他希望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和老師都能在這方面不斷的改進自己,做到“不扣亦鳴”。
1.2.3素絲說:環境的重要性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日: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認為人性生來就像素絲一樣。后天的環境就如同染料,人性與教育環境的關系就如同染料與絲線的關系,教育環境對教育者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因其環境和教養的不同,結果或善或惡。如果人們不斷地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學校環境、家庭環境和道德風尚,就會對受教育者起到“近朱者赤”的作用,反之,如果處在不好的環境中,受教育者就會出現“近墨者黑”的結果。
1.2.4三表法:以直接經驗、間接經驗、社會效果為準繩
墨子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是在認識論方面。他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為依據。墨子從這一樸素唯物主義經驗論出發,提出了檢驗認識真偽的標準,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通“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實”、“利”綜合起來,以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和社會效果為準繩,努力排除個人的主觀成見。[2]
1.3墨子思想的現實回歸——實踐
1.3.1知行合一
墨子最看不起那些光說不練的人,也最厭惡那些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偽君子,所以他要“言行合一”;他仰慕治水的夏禹,很能發揮夏禹的刻苦精神。他生活節儉,甘于粗衣惡食,為救世拯民而奉獻自己。他反對戰爭,但又不忍見弱肉強食的場面,因此他將弟子組成一支維護和平的十字軍,參與各種濟弱鋤強的行動。在先秦各種學派的領袖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位有像墨子這樣的實踐苦干的精神的。墨子與孔子盡管理想不同,作法不同,但他們為求世界的和平所做的努力是相同的。他們的精神同樣博得后世學者的贊揚。
1.3.2非命觀
墨子的“非命”論,是從“天志”“明鬼”的宗教思想體系發展而來的,他所反對的是充塞當時社會麻醉人心已久的“命定”之說。他既堅信天帝、鬼神,但又不信命運,乍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其實并不然。胡適之先生有一段話說得很清楚,他說:“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來墨子不信命定之說,正因為他深信天志,正因為他深信鬼神能賞善而罰暴。墨子以為天志欲人兼愛,不欲人相害,又以為鬼神能賞善罰暴,所以他說能順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禍。禍福全靠個人自己的行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來的,并不由命定。”。[3]
墨子以為“命”是:“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主張有命的人說:“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天則天。雖強勁何益哉?”(非命上篇)這種命定之說,會使人民依賴命運而不努力工作,因而阻礙政治、社會的進步,所以墨子斥為“非仁者之言”。而偏偏這種不仁的“執有命者,以裸于民間者眾”(非命上篇),因而使國家“不得富貴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所以墨子極力反對有命之說。[4]
1.3.3節用
墨子的節用思想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它們主要是一些消費行為所應遞循的道德規范。第二,墨子在注重節用的同時,也強調生產之重要性。他以為要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使一切人民皆能維持一定的消費水平,就心須加強生產。第三,節用的主張主要是針對當時的統治階級而言的。尚儉節用,本為先秦各學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體力行,自奉甚儉,還制定了具體的標準和內容,對消費行為予以規約,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封建統治階級。[5]墨子的節儉以“國家百姓人們之利”為旨歸,體現其無私奉獻和自我棲牲的精神。墨子這一節用的思想已經超越了純經濟學的意義,閃爍著倫理智慧之光。
2、墨子思想對當代德育的啟示
2.1注重社會、家庭、學校環境的重要性
俗話說得好“環境造就人”,環境能影響人,可以熏陶人,也能潛移默化地改變一個人,它能從多個側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孩子的成長和發展,并支配著孩子思想道德行為。良好的環境能成就一個人,而不良的環境也將會給一個人的成長帶來負面作用,當然這里的環境既指家庭環境、也指學校環境和社會環境。
2.2培養兼愛天下的義利觀
在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覺總結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既要抓物質文明建設,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也就是說眠要重視物質利益,要大力發展好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又要重視愿想道德的提高,要加強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教育,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文化,在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各種拜金主義,以權謀私、經濟犯罪等等丑惡現象廣泛蔓延。因此在新時期、更要重視“利”和“義”的統一,兩個文明一起抓,既要講物質利益,也要講利國利民利他人的道德,使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單方面地強調那場面都是錯誤的。要以“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最高價值標準,努力為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多做貢獻。
2.3提倡勸之賞罰、威之刑罰的德育方式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賞罰也不能例外,我們要善于把賞罰同思想政治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于賞罰的全過程之中。每項賞罰政策出臺時,應當結合實際,向群眾講明白制定賞罰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事業的發展,保證工作任務的完成,也是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使大家統一認識,端正態度,樹立爭上游、爭先進的良好風氣,防止出現不擇手段獲取獎賞的做法。同時也要處理好貫罰同思想政治工作的關系。賞罰具有倡是禁非、懲惡揚善的作用,這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作用相同,但絕不能因此而用賞罰來代替思想政治工作。
2.4養成經世致用的學習態度
學習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將知識與理論應用于現實,付諸實踐,而知識分子則應以“士大夫”的身份積極入世,將建功立業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與目標。《禮記·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這一過程,就是將經世致用的理想轉化為現實。
參考文獻:
[1]梁啟超.墨子學案[M],北京:商務印書館,1921.
[2]任繼愈.墨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3]陳克守先生,桑哲.墨學與當代社會[M].中國社會科學,2007.
[4]黃釗.中國古代德育思想史論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5]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6]陳谷嘉,朱漢民.中國德育思想研究[M].江蘇: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
樊如一,女,青海西寧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思政教學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倫理學。
常亞男,女,思想政治教育與傳統文化,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與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