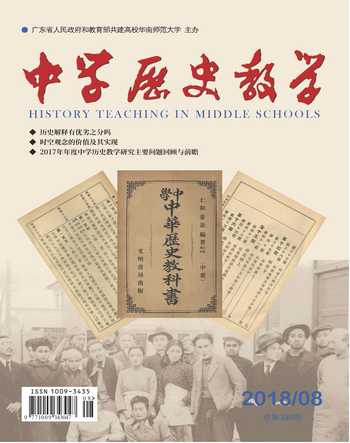淺談邏輯方法在歷史論證題中的運用
花遠杰 萬靈
高考歷史論證題(第41題或42題)是歷史考試改革的實驗田,自2011年以來,試題圍繞著題目命制形式、材料呈現方式、考查的角度等不斷創新,一直備受師生矚目。具有轉折意義的年份是2016年,之前試題多是“提取信息并進行說明”,近乎簡答題;但2016年以來試題要求明確寫出所擬論題、進行闡述。在評分標準上要求“觀點明確、論據準確、史實合理、論證充分、邏輯嚴密、表述準確”,這是歷史論證題的典型作答要求。因此,能否進行有效的邏輯論證成為解答本題的關鍵因素,本文擬從邏輯方法的角度探討有效論證的途徑,期望對我們的復習備考工作有所啟發。
王雄指出:“單純看‘論證,主要指邏輯論證,歷史學科中的論證就需要有史實為證據。邏輯論證依靠演繹推理、歸納推理等。”[1]所謂邏輯論證就是由一個或幾個已知為真的判斷,通過推理來確定另一個判斷的真實性或虛假性的思維過程。論證由論題、論據和論證方式三個部分構成。論題就是論證中需要確定其真實性的判斷,它是論證的對象,它所要回答的是“論證什么”的問題;論據就是論證中來確定論題真實性的判斷,它是論證的理由或依據,它所回答的是“用什么來論證”的問題;論證方式是由論據推出論題所用的推理形式,它是聯系論據與論題的邏輯紐帶,它所要回答的是“怎樣論證”的問題。邏輯論證的基本方法是歸納與演繹兩種推理方式的靈活運用。
一、論題的提出——歸納推理
論題,即論證的對象,是論證活動的中心,論題明確是論證試題要求的首要條件,運用歸納推理得出明確的論題是解決此類問題的常見方法。歸納推理“是一種以個別性或特殊性判斷為前提推出一個以普遍性判斷為結論的推理”[2]。通俗的講,就是從個性(特殊)到共性(一般)的推理過程。歸納推理有兩種形式:完全歸納推理和不完全歸納推理。如果用S代表某類對象,以S1,S2,S3,…Sn,代表S類的個別對象,用P代表對象的某種屬性,那么其常見的形式為:
S1是P;S2是P;S3是P…… Sn是P; S1,S2,,S3,Sn是S類的全部對象(或部分對象);因此所有S都是P 。
以2017年全國Ⅱ卷為例:
——據(英)約翰·哈薩德《時間社會學》等
從材料中提取兩條或兩條以上信息,擬定一個論題,并就所擬論題進行簡要闡述。(要求:明確寫出所擬論題,闡述須有史實依據。)
【分析】 試題緊緊圍繞“鐘表的演變”這一主題,通過年表的形式展現古代、中世紀末期、近代早期、1850年前后、20世紀初、20世紀50年代、21世紀初七個時間段中鐘表演變的不同特征。此題要求考生從材料中提取兩條或兩條以上信息,提煉出論題,并結合所學知識進行論證,進而考查考生發現歷史問題、論證歷史問題的能力。鐘表的演變與社會生活、生產勞動、科學技術等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密切相關,相互作用。此題用歸納法很容易就得出結論:通過中世紀末期的機械鐘、近代早期的懷表、20世紀50年代的原子鐘、21世紀初的智能手表四段史實可得出科技進步推動鐘表的發展;通過近代早期鐘表是奢侈品、1850年前后英國各個階層都有鐘表兩個史實可得出工業革命與鐘表的普及;通過近代早期伽利略發明游絲、20世紀50年代原子物理學原理兩點史實可得出物理學的進步與鐘表的發展等。
教師在指導學生運用歸納推理得出結論的過程中,要注意兩點,一是被考察的對象要盡可能多;二是范圍盡可能廣,否則就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錯誤。得出明確的結論是展開論證的前提,進行有效的論證是展現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關鍵,演繹推理是進行有效論證的常見方法。
二、有效的論證——演繹推理
演繹推理是“以一般性原理的判斷為論據來論證以特殊性或個別性知識的判斷表達的論題。”[3]通俗的講,就是由共性(一般)到個性(特殊)的推理過程。三段論是演繹推理最常見的形式,三段論即由兩個含有一個共同項的性質判斷作前提得出一個新的性質判斷為結論的推理。三段論都包括小項、大項、中項三部分,結論的主項是小項(小前提),用S表示;結論的謂項叫做大項(大前提),用P表示;兩個前提中所共有的項叫做中項,用M表示。其形式結構可表示為:所有M是P;所有S是M;所以,所有S是P。
運用演繹推理,能對歸納法所得出的論題有效的論證,仍以2017年全國Ⅱ卷為例:
【論題】科技進步推動鐘表的發展
【論證】中世紀末期生產力技術落后,機械鐘只有時和刻;近代早期隨著文藝復興的興起和自然科學的產生,伽利略通過長期實驗研究發明了懷表;隨著三次科技革命,生產力顯著提高,尤其是原子技術的發展,到20世紀50年代產生了原子鐘,鐘表的精確程度大大提高;到21世紀初,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具有計時、信息處理、導航、監測等多種功能的智能手表產生。這表明科技進步推動了鐘表的發展。
【分析】在此論證過程中,科技進步是結論的主項,即S;鐘表發展是結論的謂項,即P;兩個結論共有的中項是不同時間段的發展,即M。論證結構為所有M是P(中世紀晚期、近代早期、20世紀50年代、21世紀初四個時間段都是鐘表演變的歷程);所有S是M(中世紀晚期科技成果、近代早期科技成果、20世紀50年代科技成果、21世紀初科技成果是不同時間段科技發展的表現);所以,所有S是P(從科技進步推動鐘表的發展;這一結論正確)。
在全國卷的答案示例也同樣有演繹推理的運用,以2016年Ⅱ卷為例:
【觀點】中國為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貢獻。
【論述】中國古代的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印刷術四大發明經絲綢之路傳到歐洲。這一傳播促進了歐洲的社會發展,火藥的傳入推動了歐洲火藥武器的發展;指南針促進了地理大發現;造紙術和印刷術促進了歐洲文化的發展,為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提供了條件。
【分析】從此參考答案中,我們能發現其邏輯推理形式完全符合演繹推理的要求。具體如下:中國是結論的主項,即S;為世界文明發展做出的貢獻是結論的謂項,即P;兩個結論共有的中項是文明,即M。所有M是P( 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等文明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所有S是M(中國的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四大發明為代表是文明;)所以,所有S是P(中國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貢獻這一結論正確)。
教師在指導學生運用邏輯推理進行有效論證時,要注意靈活運用邏輯推理的基本原理,必須確保前提真實與推理形式正確。在每一個有效的推理中,其前提與結論之間必須保持聯系,因此教師在運用歸納與演繹推理中還應遵守相應的規則。
三、論證中的規則
人們在論證過程中,要保證論證的合理,必須遵守一條基本原則,即充足理由律。也就是說在論證中,如果一個論題被確定為真,該論證就一定要為其提供充足理由,否則,該論題就不能被確定為真。除此之外還遵循以下規則:
1.論題必須清楚明確。
論題是論證的對象,是要說明的問題,是論證活動的核心。論題的明確不僅包括思想上要明確,也包括表達上要明確。因此在表達上盡量選用意義明確的語詞,必要時還需要進行簡明扼要的解釋。例如“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李鴻章既是愛國者又是賣國賊”等這樣的論題就是不明確,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混亂局面。
2.論題前后必須保持一致。
論題是論證的中心,一旦有了明確的論題,就要緊緊抓住它,整個論證過程都要圍繞它進行,前后保持一致,不得中途任意轉換。常見的有擴大論題、縮小論題、脫離論題、缺乏論據四種錯誤。例如,某考生在論證“中國古代科技對世界做出重大貢獻”這一結論時,將“中國古代科技”擴大到“中國科技”;或將“中國古代科技”縮小到“造紙術”;或直接脫離“中國古代科技”的范圍,選取古代文學、書法等方面進行論證;或直接沒有論據。這些都違反了這一原則,都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
3.論據必然能推出結論。
杜威指出:“歸納與演繹是思維的雙向運動,兩者密不可分。”[4]因此,運用歸納法是檢測演繹推理是否正確的重要手段。這就需要論據必須真實可信、論據必須充足、論據與結論之間必須有內在聯系、推理形式必須正確。例如:論題與論據不相干、論據不足、違背三段論推理原則。這些都違反這一原則,犯了“推不出”的錯誤。
四、日常教學中的啟示
歷史論證題主要考查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陳志剛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講邏輯推理能力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能力”[5],教師在日常教學中應當采取一些措施以培養學生這種能力以更好的應對第41題(或42題)的能力要求。
關注學生的思維過程。教師應創造條件,使學生直接參與學習過程,讓他們在獨立思考、親自實踐中掌握新知識,而不是簡單的灌輸式教育。在得出結論的過程中,教師可呈現多個歷史知識,讓學生在多個史實中找到一個共同規律,然后得出結論;同時也可呈現相互矛盾的結論,采用啟發式教育,引導學生在新舊知識的沖突中,激發學生思維的興趣,進入積極的思維狀態,進而培養學生演繹推理的能力。
重視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可采用問題教學法的相關策略,通過創設情境、設計問題、層層遞進地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在解決一個個問題中逐漸提升自己的分析、歸納、概括、抽象的能力,同時教師加強史論結合的教學,在日常教學中培養學生用史論結合的論證方式解決歷史問題。
注意貫徹邏輯學的相關知識。邏輯學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地位不斷提升。1977年版的《英國大百科全書》把邏輯學列為五大學科之首。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邏輯學不斷的發展,在命題考試中也多有體現。教師應熟知邏輯學的基本原理,讓學生養成根據一定的邏輯規則進行論證的習慣,推理形式正確,合乎邏輯。尤其是要掌握歸納與演繹兩類邏輯最常見的方法,采取一定措施對學生的邏輯思維進行反復訓練。讓學生能夠從邏輯的角度提高自己的論證能力。
總之,無論全國卷歷史論證題的命制形式、作答要求變化多么頻繁,但其解答方式離不開歸納與演繹邏輯的靈活運用,教師如果能夠從邏輯方法上下功夫,將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解題能力。
【注釋】
[1]王雄:《中學歷史教育心理學》,長春:長春出版社,2012年,第194頁。
[2][3]蔡賢浩:《形式邏輯》,武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9頁,第197頁。
[4]杜威:《我們如何思維》,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65頁。
[5]陳志剛,周武兵:《從高考文綜41題解題題談歷史辯證邏輯方法的運用》,《歷史教學》(上半月)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