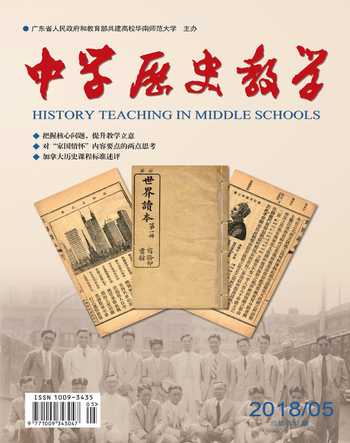高中歷史教學應注重時序觀念的動態發展
劉劍
馬克·布洛赫指出,“歷史的時間”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現實,它一直向前,不可逆轉。正是在時間的長河中,潛伏著各種事件,也只有在時間的范圍內,事件才變得清晰可辨。……這種真正的時間,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1]這種將時間看作一個連續統一且不斷變化的時間觀,應該如何落實到高中歷史教學中去呢?筆者認為,何成剛等提出的“歷史教學語境下的時序觀念”值得借鑒,即“在歷史敘述中樹立時間意識,學會運用時間術語來進行歷史陳述;在歷史分析時要重視資料文獻中時間的價值與作用;在時間的背景下把握歷史的變遷與延續、原因與結果”。[2]
高考文綜全國卷非常重視考查“在時間的背景下把握歷史的變遷與延續、原因與結果”,2017年文綜全國Ⅰ卷第25題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原題:
表1為西漢朝廷直接管轄的郡級政區變化表。據此可知
A.諸侯王國與朝廷矛盾漸趨激化
B.中央行政體制進行了調整
C.朝廷解決邊患的條件更加成熟
D.王國控制的區域日益擴大
此表采用大事年表的形式,反映了朝廷直接管轄的郡級政區的變化,從高帝劉邦時中央政府控制的15郡到武帝時的108郡、國,表明西漢中央政府在近90年的時間內,通過削藩、平定七國之亂、頒布推恩令等一系列措施,清除了王國勢力的威脅,加強并鞏固了中央集權,從而為中央政府集中精力來解決邊患、特別是匈奴的威脅提供了條件。
高考結束,筆者詢問學生,發現有相當多的人做錯了此題,究其原因,學生只能看到西漢中央政府清除了王國勢力的威脅,加強并鞏固了中央集權,但是想不到這為朝廷解決邊患提供了有利條件,也就是看不到歷史的變遷與延續。這說明我們在平常上課時,必須加強這方面的訓練。
如何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變遷與延續的理解,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其一,利用大事年表。長期以來,我們只是用大事年表來記憶重大歷史事件,探討同一時期內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卻忽略了同一事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變化和影響。可喜的是,這種情況已有改觀。2017年7月在成都舉行的“學科素養與歷史教學”全國學術研討會上,由北京101中學陳昂老師執教的公開課《商鞅變法——強國之道的再省思》,就體現了這種思考。
通常教師在講授《商鞅變法》一課,對于其影響一般采用教材的表述,如“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壯大了國力,為秦國的富國強兵和接下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秦國以至中國歷史的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3]這種結論性的表述過于籠統,難以留下深刻印象。陳昂老師則獨辟蹊徑,解決了這一問題。
首先,出示商鞅變法之后的大事年表:
十年:行法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曰:相秦不以百姓為事
秦俗日敗。……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二十年:車裂商君……遂滅商君之家(前338年)
百年:長平之戰,坑趙卒四十萬
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前260年)
滅周,遷九鼎于咸陽(前256年)
百三十年:六王畢,四海一(前221年)
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百五十年:(劉邦約法三章)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
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前206年)
二百二十五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134年)
三百年: 漢宣帝:霸王道雜之(前73-前48年)
二千年: 百代都行秦政法
然后,從“百年視角”、“千年視角”兩個視角進行考察,讓學生思考、探究、討論,從歷史長河中把握歷史的變遷與延續,很好地落實了時空觀素養的培養。[4]
其二,避免歷史人物的“概念化”、“臉譜化”。歷史人物縱觀其一生,思想、活動總是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的,不能拿其某一階段的表現當成其一身的寫照。以前在講授《啟蒙運動》涉及康德的思想時,筆者出示康德“一天起居生活時間表”:[5]
本想以此表來說明康德的自律思想,不料學生在課后則認定康德就是一個刻板、毫無生活樂趣之人。謝文郁指出:“人們津津樂道的康德晚年那像鐘表一樣呆板而準確的生活節律,以此說明康德思想的嚴密性和精確性。于是,我們獲得這樣一個康德印象:沒有生活趣味、沒有生存關注、沒有情感發泄、在思想上精益求精、除了思辨還是思辨等等。這是一個概念化了的康德。康德作為思想家是活生生的。”[6]
的確,康德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比如他熱衷于社交,即使在他養成了像鐘表一樣呆板而準確的生活節律之后,也是如此——康德64歲時,“雖然康德在家里開伙,并定期邀請朋友到家里共進晚餐,但是那并不表示他從此不再出外用餐。如前所述,星期天他通常在馬瑟比家吃飯。博羅夫斯基說:‘他是上流社會宴會里的常客,也時而出席好友愉悅的晚宴,午餐的邀請幾乎是來者不拒,晚餐的邀請則幾年來都沒有再接受過。”[7]
有鑒于此,筆者在處理這一問題時,補充了兩則材料:
材料一 康德作為一個教師,必須講授許多課以維持生活。……康德后來曾經敘述:“在1770年,我因為升任邏輯與形而上學的教授,而必須在七點開始講課。當時我雇了一個仆人來叫醒我。”在那以前,康德從未在八點以前上課。因此,康德的生活規律性有一部分是拜政府之賜。早起并不是他自己的選擇,而是因為公務。
——[美]曼弗雷德·庫恩著,黃添盛譯:《康德傳》
材料二 朋友與舊識是康德想留在哥尼斯堡的原因之一。康德在他的出生地覺得很自在。長久以來,他經常獲邀參加當時重要家族的餐宴或聚會,在凱澤林克的官邸中與貴族交游,與哥尼斯堡的商賈與俄國軍官保持來往。……他的“優雅”與文質彬彬的舉止,在學者當中十分少見。
——[美]曼弗雷德·庫恩著,黃添盛譯:《康德傳》
這兩則材料,一則用以說明康德也不是完美之人,其生活節律有一部分是外在壓力(材料中的“拜政府之賜”)所致;二則用以說明康德不是一個刻板之人,他在社交圈里很受歡迎。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對“時空觀念”的解釋是:“在特定的時間聯系和空間聯系中對事物進行觀察、分析的意識和思維方式。任何歷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發生的,只有在特定的時空框架當中,才可能對史事有準確的理解。” [8]筆者認為,在理解“特定”這個詞時,不能將其靜態化,必須注重時序觀念的動態發展。
【注釋】
(法)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程郁譯:《為歷史學辯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3頁。
何成剛、沈為慧、陳偉壁:《歷史教學中時序觀念的培養》,《歷史教學》2012年第1期。
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歷史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歷史選修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7頁。
陳昂:《歷史的回響——“商鞅變法:強國之道的再省思”一課的再省思》,《中學歷史教學參考》,2017年第9期。
陳偉國:《高中歷史新課程教學札記(六)啟蒙運動》,《中學歷史教學》,2009年第3期。
(美)曼弗雷德·庫恩著,黃添盛譯:《康德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頁。
(美)曼弗雷德·庫恩著,黃添盛譯:《康德傳》,第379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