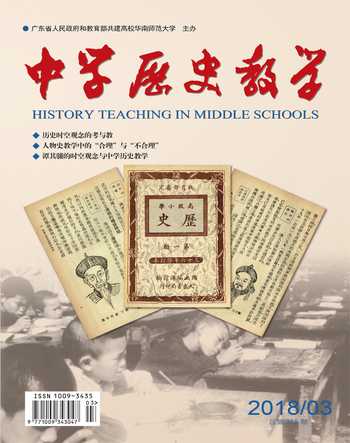化解高中思想史教學教條化和簡單化傾向的策略選擇
冀強
在歷史學的眾多分支學科中,思想史是一門需要更多理論思辨的學科。但受制于思維習慣、學術素養和教材體例,教師在講授思想史內容時很容易出現教條化和簡單化的傾向:從固有模式出發,以概念解釋概念,思想史教學很可能是索然無味、乏善可陳。如何化解思想史教學中的教條化、簡單化傾向一直是一些一線教師長期思考的問題,也是一些一線教師為之努力的方向。在此,筆者就以人教版必修三《三民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一課的部分教學案例為例簡單談談化解高中思想史教學簡單化和教條化傾向的策略選擇和方法路徑。
一、回歸思想者本身:消除歷史教學教條化的有效途徑
“任何一種社會思潮和思想體系的產生,都有社會歷史的原因,不是憑空出現的。因此我們在學習和研究中應當注意歷史和邏輯的統一。”[1]一套成熟的思想體系往往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反映。在講授思想史時,教師大多會從社會背景入手進行分析。這種分析方法固然是一種很好的解釋路徑,卻忽視了思想者本身的思考,極易出現思想史教學中“人”的缺失,從而使思想史教學模式化、教條化。
實際上,任何思想的形成,除去社會環境外,還與思想者個人的思考路徑有著很大的關聯,思想史有著自身的發展脈絡。“思想史本身也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領域,有它內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它的發展過程中找到從上一個階段轉變到下一個階段的線索。”[2]對一套成熟的思想體系而言,其形成過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著自身的發展脈絡,是思想者在長期思考之后對社會問題的抽象概括和理性總結。在這一過程中,思想者本人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三民主義”的理解是本課的教學重點。在講述三民主義的缺陷——孫中山為什么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口號時,教師總是用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來概括其基本缺陷。這種表述是階級史觀下的一句經典概括,也是分析近代歷史的基本方法,有其合理性。但在教學中如若簡單使用、頻繁使用很容易使思想史教學呈現出教條化、模式化的傾向,更無法說明三民主義的復雜性和思想者思考問題的廣度和深度。
孫中山是偉大的政治家,而非純粹的理論家。政治家的特征是既有政治原則又能隨環境和時局的變化采取隨機應變的策略,從而以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達到自己和集團的政治目的。孫中山之所以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口號,就是出于對現實政治的考慮。
第一,這是一種革命策略的考慮。孫中山不是不反帝,而是等國家強大后再反帝。“我們現在要脫離奴隸的地位……推翻滿清二百多年來的專制統治,恢復我漢室的山河,再把國家變強盛;那時自然可以和外國講平等了。”[3]
第二,這也是對歷史教訓的汲取。“今日之中國何以必須革命? 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于義和團一役, 二萬洋兵攻破北京。”[4]八國聯軍侵華幾乎使中國亡國,殷鑒不遠,制定這樣的策略實際上是對歷史教訓的深刻借鑒。
第三,這也是一種現實的無奈。1895年,孫中山籌劃廣州起義失敗后便遭清政府通緝,被迫長期流亡海外,穩固的國內革命根據地始終無法建立起來。孫中山不得不在海外,尤其是在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從事革命活動。因此,作為革命者的孫中山不可能在其革命綱領中明確提出反帝口號。
在實踐中,正是這種暫時的妥協策略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創造了一定的有利條件,它讓帝國主義未能找到干涉中國革命的借口。
可見,孫中山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口號是革命者對現實深入思考的結果,而非簡單的理論概括。一句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顯然無法說明歷史的復雜性,也無法還原思想者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
思想是人的產物,“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5]所以,講授思想史時一定要回到歷史的現場,“神入”歷史人物,“使學生置身于歷史發展的環境中去觀察歷史,站在歷史人物的立場上去研究歷史,從而把握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信仰、動機等,并理解他們思想的發展變化……”[6]對思想史的講授而言,教師如能帶領學生神入歷史,讓“人”回歸思想本身,從思想者本身來解讀思想史將會對思想史內容有著一番新的認識。
二、回歸原始文本:化解歷史教學簡單化的重要方法
一般說來,我們所面對的思想體系,都是思想者經過理論思辨、理性思考而得出的最終結論。實際上,任何一套完整思想體系的形成都有其清晰可見的邏輯路徑、發展脈絡。但受制于教材體例,這種邏輯路徑、發展脈絡并沒有被清晰地呈現出來,而是語焉不詳、概念模糊,僅有一個相對簡單的結論。教師在處理這樣的內容時,如若僅以書本上的內容為主,以概念來解釋概念,思想史教學就容易出現簡單化的傾向。學生自然無法體會到思想者思考問題的完整性和嚴密性。
盡管我們已無從得知而且也不可能重現思想者的理論思維過程,但是借助于思想者留下來的原始文本,我們依然可以體會到思想者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從原始文本出發恰是化解高中思想史教學簡單化傾向的重要途徑。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為了消除資本主義弊端,縮小貧富差距而提出的思想主張。這也是三民主義中最難理解的一部分內容。在講述該部分內容時,教師一般會用“土地國有、核定地價、漲價歸公”這12個字來概括民生主義的基本內涵。但如何“核定地價”?為什么漲價部分一定要歸公?民生主義如何消除貧富不均?教師對于這樣的問題很少或者基本沒有涉及。教師講解淺嘗輒止,學生對這部分內容的理解自然也是一知半解,課堂教學的簡單化傾向非常明顯。但若在教學中引用孫中山論述民生主義的原始文本,這一問題便會迎刃而解。以下便是筆者選取的文本資料:
材料一:地價都是由地主報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許多人以為地價由地主任意報告,他們以多報少,政府豈不是要吃虧么……但是政府如果定了兩種條例,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又可以照價收買……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地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愿多報,也不情愿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
——孫中山《三民主義》[7]
如何“核定地價”?通過對材料的分析可以得知“核定地價”是由地主申報來完成的。但地價申報會出現申報不實的現象,為了避免地主的申報不實,孫中山主張按地主申報的“地價”購買土地,地主自然不會少報;另外,孫中山還主張按地主申報的價格來征稅,地主自然不會多報。權衡利弊,地主所報的地價既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而是一個實在的土地價格。
材料二: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后,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后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于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中國的工商業幾千年都沒有大進步,所以土地價值常常經過許多年代都沒有大改變。如果一有進步,一經改良,像現在的新都市一樣,日日有變動,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后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
——孫中山《三民主義》[8]
為什么說漲價的部分一定要歸公?通過對材料的分析可以得知地價的上漲源于社會事業的進步,工商業的發展,而社會事業的進步和工商業的發展則是眾人努力經營的結果。所以說漲價部分應歸之于大眾,而非私人占有,即所謂的“漲價歸公”。
材料三:文明城市實行地價稅,一般貧民可以減少負擔,并有種種利益。像現在的廣州市,如果是照地價收稅,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經費便有著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雜稅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來水和電燈費用,都可由政府來負擔,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負擔。其他馬路的修理費和警察的給養費,政府也可向地稅項下撥用,不必另外向人民來抽警捐和修路費。
——孫中山《三民主義》[9]
為什么說“漲價歸公”會使貧富差距縮小?通過對材料的分析可以得知土地收入是一筆巨大的財政收入。政府可以依靠這筆收入從事公共事業建設,減少一般民眾的賦稅負擔,從而縮小貧富差距。
可見,民生主義并非“平均地權”四個字那么簡單,而是有著自身的邏輯路徑。通過這樣的文本展示和教學分析,民生主義的邏輯路徑便被清晰地呈現出來,從而加深了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化解了思想史教學中的簡單化傾向。
歷史論著是前人研究的心得,它為我們提供了入門的線索和理解的基石。“這是一種參考,但不能代替閱讀史料。只有通過搜集和檢閱史料,才能發現前人認識的偏差,才能發現新的意義和新的領域。”[10]對思想史的教學來說亦當如此,回歸原始文本方可看清思想的本質,掌握發展的脈絡。
從思想者本身和原始文本出發解讀思想史的本質就是教師利用史學的學術性、教師的專業性促使學生學科素養的提升,并促進學生發展。在這樣的課堂中,學生獲得的是對歷史的真實體悟,而不是游離于歷史邊緣的空洞說教。筆者深切地感受到,這樣的教學設計確實抓住了學生的心理,課堂氣氛良好、學生參與度較高。思想史教學的教條化和簡單化傾向在這樣的課堂教學中迎刃而解。
【注釋】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原序》,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4頁。
余英時:《論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32頁。
陳旭麓、郝盛潮:《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頁。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6頁。
錢穆:《國史新論》,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298頁。
虞森:《編選歷史故事,“神入”歷史人物——以人教版選修4<秦始皇>為例》,《歷史教學》(上半月刊)2015年第3期。
孫中山:《三民主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4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第194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第195頁。
李良玉:《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江蘇社會科學》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