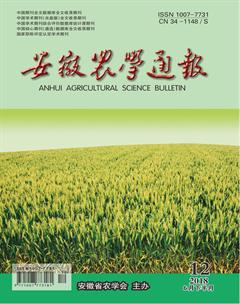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耕地集約利用評價(jià)
石健
摘 要:為準(zhǔn)確認(rèn)識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耕地集約利用狀況,以張家界市為例,采用變異系數(shù)法與綜合指數(shù)法相結(jié)合的方法計(jì)算耕地集約利用綜合指數(shù),根據(jù)計(jì)算結(jié)果對其時(shí)序變化進(jìn)行評價(jià)分析,并運(yùn)用ArcGIS平臺進(jìn)行空間分析,以期為其他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耕地集約利用評價(jià)的研究提供參考。
關(guān)鍵詞:耕地集約利用;變異系數(shù)法;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張家界市
中圖分類號 F301.24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8)12-0057-4
Study on the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Shi Jia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this paper takes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and uses the method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dex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Then,evaluates and analyses the time serial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and makes a spatial analysis by using ArcGIS t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other underdeveloped areas.
Key words: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Underdeveloped areas;Zhangjiajie City
我國正處于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黃金時(shí)期,二、三產(chǎn)業(yè)的大力發(fā)展使大量農(nóng)村勞動力“棄地進(jìn)城”,造成農(nóng)村土地的拋荒與閑置。城市擴(kuò)張也不可避免地占用耕地,加上部分地區(qū)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自然災(zāi)害,導(dǎo)致耕地減少,土地消耗不斷高漲[1-3]。在對環(huán)境不施加壓力的前提下,加大耕地的集約利用度,在同等面積或者更小面積的耕地上獲得更多的產(chǎn)出,是未來保障糧食安全、解決“三農(nóng)”問題的有效途徑[4-5]。對耕地的集約利用情況進(jìn)行評價(jià),有助于認(rèn)清耕地集約利用現(xiàn)狀及規(guī)律、促進(jìn)耕地高效利用,同時(shí),對于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和新型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都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6]。
學(xué)術(shù)界專門針對耕地集約利用評價(jià)方面的研究比較豐富[3-10],但大部分學(xué)者是以宏觀區(qū)域或社會經(jīng)濟(jì)較發(fā)達(dá)地區(qū)為研究尺度,較欠缺對中、微觀層次或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實(shí)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張家界市為例,選用變異系數(shù)法計(jì)算耕地集約利用度,為區(qū)域農(nóng)業(yè)發(fā)展提供依據(jù),同時(shí)為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耕地集約利用評價(jià)的研究提供科學(xué)指導(dǎo)。
1 研究方法
1.1 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 耕地利用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要對耕地集約利用進(jìn)行評價(jià),需要根據(jù)耕地的特征,構(gòu)建1個(gè)多方位、多視角的指標(biāo)體系。本文從“投入—利用—產(chǎn)出”的角度入手,從投入強(qiáng)度、利用程度、產(chǎn)出效益、可持續(xù)利用狀況4個(gè)方面構(gòu)建起指標(biāo)體系,依據(jù)科學(xué)性、可比性原則,通過反復(fù)論證,最終選擇12個(gè)具體指標(biāo)作為指標(biāo)層[10](表1)。
1.2 指標(biāo)的標(biāo)準(zhǔn)化及權(quán)重的確定 通過變異系數(shù)法與綜合指數(shù)法相結(jié)合的方法,計(jì)算耕地集約利用綜合評價(jià)指數(shù)。變異系數(shù)法是1種客觀賦權(quán)法,具有較強(qiáng)的客觀性和數(shù)學(xué)理論依據(jù),概念清晰、計(jì)算簡便、容易掌握,有利于克服主觀賦權(quán)法的主觀性所帶來的偏差。
1.2.1 指標(biāo)的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 由于本文選擇的指標(biāo)量綱不統(tǒng)一,因此不能直接比較,為消除不同量綱對研究結(jié)果的影響,需對各項(xiàng)指標(biāo)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采用極差標(biāo)準(zhǔn)化的方法消除指標(biāo)的量綱[3]。
[ Xij=(Xij-minXj)/( maxXj-minXj )] (1)
[Xij=(maxXj-Xij)/(maxXj-minXj)] (2)
式(1)為正效應(yīng)指標(biāo)的標(biāo)準(zhǔn)化,式(2)為負(fù)效應(yīng)指標(biāo)的標(biāo)準(zhǔn)化。式中,[X'ij]表示標(biāo)準(zhǔn)化后的指標(biāo)值,[Xij]表示第i個(gè)樣本中第j個(gè)指標(biāo)的原始值,[maxXj]表示第i個(gè)樣本中指標(biāo)的最大值,[minXj]表示第i個(gè)樣本中指標(biāo)的最小值。
1.2.2 變異系數(shù)
[Sj=i=1n(X'ij-Xj-)2/(n-1)] (3)
[Sj]表示第j個(gè)指標(biāo)標(biāo)準(zhǔn)化后樣本值的變異系數(shù);[xj]表示第j個(gè)指標(biāo)標(biāo)準(zhǔn)化后的樣本平均值;n為樣本個(gè)數(shù)。
1.2.3 權(quán)重
[Wj=Sj/i=1mSj] (4)
Wj表示第j個(gè)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0≤[Wj]≤1);m為樣本中的指標(biāo)個(gè)數(shù)。
1.3 綜合評價(jià)指數(shù) 耕地集約利用是眾多指標(biāo)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每個(gè)單項(xiàng)指標(biāo)都從不同側(cè)面反映了耕地的利用狀況,因此,根據(jù)上述公式得到的變異系數(shù)和權(quán)重值,運(yùn)用綜合指數(shù)法可以得到耕地集約利用綜合評價(jià)指數(shù)。
[A=i=1nWjXij] (5)
2 實(shí)證研究
2.1 研究區(qū)域概況 張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我國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國家“扶貧攻堅(jiān)”工作實(shí)施的重點(diǎn)地區(qū)。全市下轄2區(qū)2縣,包括永定區(qū)、武陵源區(qū)、慈利縣和桑植縣,有7個(gè)街道、32個(gè)鎮(zhèn)、47個(gè)鄉(xiāng)、15個(gè)民族鄉(xiāng)。截至2015年,張家界常住人口152.40萬人,其中城鎮(zhèn)人口67.99萬人,城鎮(zhèn)化率為44.60%,低于全省50.89%的城鎮(zhèn)化水平;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2.94萬元,低于全省4.30萬元的平均水平,全市第一產(chǎn)業(yè)增加值為51.90億元,占全省1.56%,二、三產(chǎn)業(yè)增加值為395.80億元,占全省1.64%;全市總用地面積96.53萬hm2,其中耕地面積為11.99萬hm2,占全市土地總面積的12.42%,人均耕地面積為0.08hm2。
2.2 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主要數(shù)據(jù)包括人口數(shù)據(jù)、耕地?cái)?shù)據(jù)和其他社會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來源于歷年湖南省統(tǒng)計(jì)年鑒、湖南省農(nóng)村統(tǒng)計(jì)年鑒、張家界市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耕地集約利用評價(jià)指標(biāo)數(shù)據(jù)通過計(jì)算得出。
3 結(jié)果與分析
3.1 指標(biāo)權(quán)重分析 根據(jù)公式(1)-(3)計(jì)算出指標(biāo)權(quán)重(表2),可以看出在整個(gè)指標(biāo)層中,對耕地集約利用影響較大的因素有人均耕地、勞動力投入指數(shù)、機(jī)械化指數(shù)、勞均產(chǎn)值、化肥施用指數(shù)等。在準(zhǔn)則層中,耕地集約利用水平影響重要性順序?yàn)橥度霃?qiáng)度>產(chǎn)出效益>可持續(xù)利用狀況>利用程度,表明耕地投入強(qiáng)度對張家界市的耕地集約利用貢獻(xiàn)率最大,加大耕地投入力度是促進(jìn)耕地集約利用的重要途徑。
3.2 時(shí)間特征分析 由圖1可以看出,耕地投入強(qiáng)度總體有所上升,從2005年的0.104上升到2015年0166,投入強(qiáng)度的峰值出現(xiàn)在2009年,為0.193,2009年之后呈緩慢下降趨勢,主要原因在于2009年之后張家界市農(nóng)業(yè)勞動力減少,對耕地的資金、設(shè)備、技術(shù)等的投入不夠;耕地利用程度從2005年的0.020增長到2015年0.255,在這10年間雖存在較小的起伏,但并沒有影響整體上的增長趨勢;耕地產(chǎn)出效益與耕地利用程度的變化趨勢較為一致,從2005年的0.017增長到2015年0.241;耕地可持續(xù)狀況總體上來說變化不大,但在2009—2010年期間出現(xiàn)快速上升現(xiàn)象,到達(dá)研究年段的峰值,為0.136,2010年之后發(fā)展?fàn)顩r趨于平穩(wěn);根據(jù)可持續(xù)狀況曲線走勢可將2005—2015年中的變化可分為3個(gè)階段:逐年減少階段(2005—2009年)—快速回升階段(2008—2010年)—緩慢下降階段(2010—2015年)。
從圖1的耕地集約利用綜合指數(shù)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其變化經(jīng)歷了持續(xù)增長(2005—2007)—快速下降(2007—2008)—急劇上升(2008—2010)—緩慢增長(2010—2015)的發(fā)展過程。究其原因,2008年之前由于旅游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城鎮(zhèn)化水平的提高,張家界市大量農(nóng)業(yè)人口轉(zhuǎn)為城鎮(zhèn)人口,農(nóng)業(yè)從業(yè)人員的減少,加上資金、設(shè)備、技術(shù)等的投入較低,糧食產(chǎn)量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總值均下降,導(dǎo)致耕地集約利用水平也快速下降;2008年之后張家界市在國家政策與政府的作用下,加大資金、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等的投入,不斷改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狀況,使耕地集約利用水平得到較大的發(fā)展;2010年之后,張家界市的耕地投入強(qiáng)度、利用程度、產(chǎn)出效益和可持續(xù)狀態(tài)均變化不大,使耕地集約利用水平一直處于平穩(wěn)狀態(tài),但穩(wěn)中有升。整體而言,張家界市耕地集約利用水平呈上升狀態(tài),從2005年的0.273增長到2015年的0.773,且仍有持續(xù)上升的良好態(tài)勢。
3.3 空間特征分析 根據(jù)張家界各區(qū)(縣)的耕地集約利用綜合指數(shù),運(yùn)用SPSS19.0軟件的K-均值聚類法將2005—2015年各區(qū)(縣)的耕地集約利用度分為4個(gè)層次:不集約(A≤0.3)、基本集約(0.3≤A≤0.45)、中度集約(0.45≤A≤0.7)和高度集約(0.7≤A),并使用ArcGIS軟件繪制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的空間格局圖(圖2)。
從表3及圖2可知,2005年張家界市各區(qū)(縣)的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總體較低,介于0.237~0.303之間,平均值為0.328,永定區(qū)、武陵源區(qū)、桑植縣3個(gè)地區(qū)耕地集約利用綜合指數(shù)均低于0.3,處于不集約利用狀態(tài),慈利縣耕地集約利用度略超過0.3,處于基本集約利用狀態(tài);2015年各區(qū)(縣)耕地集約利用水平與2005相比有較大的提升,介于0.683~0.793之間,均值為0.754,總體上為高度集約;在各區(qū)(縣)中,永定區(qū)耕地集約利用水平最低,為0.683,桑植縣最高,為0.793。從表3可以看出,張家界市4個(gè)區(qū)(縣)耕地資源的集約利用水平總體上均呈增加趨勢,但各地區(qū)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增長幅度最大的地區(qū)為桑植縣,從2000年的0.237增長到2015年的0.793;增長幅度最小的是永定區(qū),10年間僅增長0.400。究其原因,桑植縣自然條件比較優(yōu)越,農(nóng)業(yè)比較效益較高,加之近年來桑植縣增加了對耕地的投入水平和利用水平,耕地集約利用狀態(tài)從2005年的不集約利用轉(zhuǎn)變?yōu)?015年基本集約。而永定區(qū)作為市轄區(qū),其城鎮(zhèn)化發(fā)展相對較快,農(nóng)業(yè)效益比較低,耕地集約利用水平雖有所提升,但由于投入力度不足、產(chǎn)出效益較低,導(dǎo)致增長速度緩慢。
4 結(jié)論與討論
(1)從耕地集約利用指標(biāo)權(quán)重來看,準(zhǔn)則層的耕地投入強(qiáng)度對張家界市耕地集約利用貢獻(xiàn)最大;指標(biāo)層的人均耕地指數(shù)、勞動力投入指數(shù)是耕地集約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
(2)從耕地集約利用時(shí)間變化來看,4個(gè)分類指數(shù)在2005—2015年均呈增長狀態(tài),綜合指數(shù)整體上也呈上升狀態(tài)。但根據(jù)綜合指數(shù)曲線變化來看,表現(xiàn)出階段性特征:持續(xù)增長(2005—2007)—快速下降(2007—2008)—急劇上升(2008—2010)—緩慢增長(2010—2015)。
(3)從耕地集約利用空間變化來看,各區(qū)(縣)耕地集約利用水平隨時(shí)間的推移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地區(qū)之間的增長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本文初步揭示了張家界市2005—2015年耕地集約利用的時(shí)空變化特征,對區(qū)域耕地集約利用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導(dǎo)意義,與此同時(shí),也充實(shí)了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耕地集約利用評價(jià)的實(shí)證研究。然而由于土地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更新,導(dǎo)致時(shí)間序列內(nèi)耕地面積統(tǒng)計(jì)口徑有一定變化,對研究結(jié)果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指標(biāo)體系和研究方法的完備性需要進(jìn)一步探討與完善。
參考文獻(xiàn)
[1]劉彥隨,喬陸印.中國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耕地保護(hù)制度與政策創(chuàng)新[J].經(jīng)濟(jì)地理,2014(04):1-6.
[2]祝宇成,王金滿,秦倩,等.城鎮(zhèn)化對耕地集約化節(jié)約利用的影響[J].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6(09):512-516.
[3]竇妍,南靈.基于PSR框架的耕地集約利用評價(jià)及驅(qū)動力研究——以關(guān)中地區(qū)為例[J].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2011,32(05):615-618.
[4]王國剛,劉彥隨,陳秧分.中國省域耕地集約利用態(tài)勢與驅(qū)動力分析[J].地理學(xué)報(bào),2014,69(07):907-915.
[5]]胡永進(jìn),張鳴峰.基于SOM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模型的耕地利用集約度分區(qū)研究——以湖北省為例[J].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3,41(11):391-394.
[6]白璞,童紹玉,彭海英.安徽省城鎮(zhèn)化對耕地集約利用的影響[J].經(jīng)濟(jì)研究導(dǎo)刊,2016(11):16-19.
[7]王國剛,劉彥隨,陳秧分.中國省域耕地集約利用態(tài)勢與驅(qū)動力分析[J].地理學(xué)報(bào),2014(07):907-915.
[8]鄧楚雄,李曉青,向云波,等.長株潭城市群地區(qū)耕地?cái)?shù)量時(shí)空變化及其驅(qū)動力分析[J].經(jīng)濟(jì)地理,2013,33(06):142-147.
[9]于元赫,李子君.山東省耕地利用集約度時(shí)空變化及政策啟示[J].中國土地科學(xué),2017,31(04):52-60.
[10]鄧楚雄,謝炳庚,李曉青.長沙市耕地集約利用時(shí)空變化分析[J].農(nóng)業(yè)工程學(xué)報(bào),2012,28(1):230-237.
(責(zé)編:王慧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