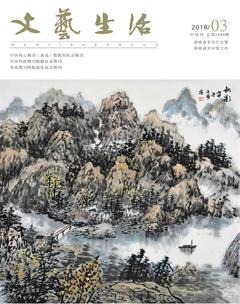《古詩十九首》中“厚”的美感淺析
高燕
摘要:從《古詩十九首》是東漢后期丈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歷史地位和審美價值。從“厚”的美學范疇上來看,《古詩十九首》語言的自然性與文人性互為表里,相輔相成,表現出“大巧若拙”的語言風格。主人公強烈又真實的感情,一步步隨著客觀情境生動的描寫而展開,真情融于實景,形成“真誠不偽”的情感表達。
關鍵詞:古詩十九首;厚;美感
中圖分類號:1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08-0117-02
一、“大巧若拙”的語言風格
“大巧若拙”這一命題最早在《老子》第四十五章出現:“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藝術的理想境界是有巧而不見其巧,大巧若拙,體現著一種返歸本源的樸厚之美。這種“厚”的美感主要來源于道家的自然美學觀,體現在詩歌語言上,就是指語言的自然。
《古詩十九首》自然的語言風格歷來為人所稱道。最有名的要數陸時雍《古詩鏡》的那一句“深衷淺貌,短語長情。”短短的八個字,高度概括了《古詩十九首》的語言風格和抒情風格。其中“淺貌”和“短語”,體現了《古詩十九首》語言的高度概括力和自然純樸、單純清新的風格。謝榛《四溟詩話》更生動詳細地論述道:“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矣。”又說“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
但一首詩歌的語言,如果只有“自然”,那就只能達到“若拙”,卻不見“大巧”了。筆者認為,《古詩十九首》語言風格之“厚”并不只有上面所說的“自然”之厚,更有“文學”之厚。“自然”體現著“厚”之美學觀中的“樸厚”之美,“文學”則體現著“醇厚”之美。自然在外,醇厚在內,內外共同作用,使詩歌的語言平淡中見深意,更經得起推敲,方是《古詩十九首》語言之魅力所在。這才是真正的“大巧若拙”。
以《行行重行行》一首為例: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朱自清先生為這首詩加了8個注釋,分別是“生別離”、“涯”、“道路阻且長”、“胡馬二句”、“相去二句”、“浮云二句”、“思君令人老”、“努力加餐飯”。其中7個有典籍出處,2個套用樂府歌詞。套用歌詞的這兩句為“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和“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分別套用的是《古樂府歌》“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句,以及蔡邕《飲馬長城窟行》“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句。“努力加餐飯”一句,既有典故出處,又有套用樂府歌詞現象。
由此可見,《行行重行行》一首有很明顯的引用典籍與化用歌辭的痕跡。其中,運用典故以及使用有典籍出處的文人性用語,是文人詩的顯著特征之一。典故的運用與文學性的措辭,增強了詩歌的力量,使整首詩體現出“詞短意長”、“深衷淺貌”的語言風格,也就是《古詩十九首》的“醇厚”體現。
筆者認為,對一種語言“醇厚”與否的判定,主要取決于語言單位面積內所包含的信息量的大小。信息量越多,語言的意蘊就越深厚。文學典故的運用,并不是一種簡單的等量代換,典故本身還包含著極為復雜的情感體驗。這種情感體驗,一部分來自于它目前所處的詩歌語境,另一部分則來源于它的出處。讀者在閱讀運用了典故的文學作品時,不僅會受到作品本身的影響,還會在潛意識中受到來自典故“本事”——即典故出處的影響。例如,《行行重行行》中的“生別離”一句,來自于《楚辭·九歌·少司命》的“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那么讀者在讀到這一句的時候,不僅會想到詩中提到的游子和思婦,還會聯想起《楚辭》中以“悲”為美的楚調,想到在祭祀活動中匆匆降臨人間又馬上要離去的少司命,體會到她面對離別時的不舍與難過。這種情感體驗,反過來又加深了我們對詩中游子思婦“生別離”的認識與同情。
依據朱自清先生的《古詩十九首釋》和馬茂元先生的《古詩十九首探索》,對《古詩十九首》中有典籍出處的地方做一個簡單的分析:《青青陵上柏》中所用的“陵上柏”、“碉中石”、“遠行客”的比喻,都是典籍中比較常見的,本身的情感取向與意義內涵都有比較明顯的指向;《西北有高樓》中“無為杞梁妻”和“但傷知音稀”兩句分別引用了杞梁妻善哭和伯牙子期的典故;《涉江采芙蓉》中“涉江”本是《楚辭》的篇名,所敘正是屈原流離轉徙的情景;采芳草送人,是古代的習俗,于《詩經》中多有描寫;“蘭澤多芳草”引用《招魂》“皋蘭披徑兮斯路漸”,有傷春思歸的暗示;《明月皎夜光》首句,一面描寫景物,一面暗示悄悄的勞心,《詩經·月出》篇中就有“明月皎兮……勞心悄兮”的說法;“促織”“東壁”也是描寫寒秋的常見意象;《東城高且長》中“晨風懷苦心”二句也更有出處,隱喻對當下處境的憂心與人生短暫的悲哀……《古詩十九首》中文人味之濃郁的,語言之醇美,由此可見了。
《古詩十九首》的文人性用語方式使其能夠用盡量簡練的文字包含更為深刻的內容,帶來了厚重的情感體驗。對民間語言習慣的吸收與運用,直白的敘述方式,又給《古詩十九首》包上了一層拙樸的外衣。這不僅沒有削減《古詩十九首》的藝術價值,反而擴大了《古詩十九首》的受眾層面,形成了它“大巧若拙”的語言風格。
二、“真誠不偽”的情感表達
在道家的思想中,“厚”體現著濃烈的返本歸源的哲學色彩。《老子》第三十八章: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所謂“厚”者,接近于道,要求大丈夫能夠立身樸實,返璞歸真,回到生命最原始的,有如赤子一般干凈純凈的狀態。反映在美學觀念上,則表現為對“真實”的提倡。
關于“真實”,莊子在《漁父》中有一段經典的論述。他認為,“真實”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能夠“真在內”而“神動于外”。這種“真”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客體的真實,另一種是主體的真實。所謂主體的真實,主要表現為個人生命狀態和精神感受的真實,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真情”。
《古詩十九首》在抒情上最大的藝術魅力恰恰就是其真誠不偽的情感表達,作者的一切情感抒發完全達到了“質真若渝”的理想境界,做到了“不自夸、不壓抑、不虛偽,盡情地袒露自己的生命。”
筆者認為,這種抒情的真實主要表現在兩點:
第一,主體抒情的強烈性。
如《今日良宴會》一首就代替所有不得志的士子發出了“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耱軻長苦辛”的呼喊,毫不掩飾自己對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渴望與追求。這種坦白,獲得了宴會上大多數人的認同與共鳴,因此才有“齊心同所愿,含義具未伸”一句。
又如《青青河畔草》一首,先用了一連串疊詞“盈盈”、“皎皎”、“娥娥”、“纖纖”,描述了一個艷妝的少婦的出場,然后又說她“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用難守的空床表現她對蕩子遠行不歸的思念之情。自古評價這首詩,有些人認為它“不免于野,不免于淫”,朱自清先生卻認為,由于主人公身份地位的限制,這句露骨的“空床難獨守”恰恰是這位蕩子婦內心情感最為真實的表達,說它失于淫野的,只是老學究的陳腐觀點罷了。
第二,抒情背景的真實性。
《古詩十九首》所選取的場景和故事背景,以及由場景觸發的抒情都是非常自然而且常見的。尤其語言的簡潔與形象,更將詩歌畫卷最大限度地還原于讀者眼前,使讀者更容易產生情感上的聯想。
例如《青青陵上柏》一首,開篇就發出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這樣悲涼的抒情感慨。這種感慨不是憑空冒出來的,是主人公在歷經了“青青陵上柏”和“磊磊澗中石”這兩種外物之后自然而然地發出來的。柏樹和水流都是和生命有關的意象。《論語·子罕》有一句話:“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一直以來,松柏都被當做是堅貞,高尚與頑強生命力的代表。因此古人有在死者的墳前栽種松柏的習慣,以此寄托讓死者“長眠不朽”的愿望。樹品甚至成了識別死者身份地位的一種標志。可見這種“陵上柏”,不僅是一種物象,還是一種與“生命”,與“死亡”有很深刻聯系的物象。再到后半句“磊磊澗中石”,《說文》:“澗,山夾水也。”指的就是山中的溪流。《論語·子罕》有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表示時間就像流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了,充滿著濃厚的時間意識與生命意識。換一個角度,以“石”為重點來看,“磊磊澗中石”,這些攢聚的石頭在溪流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接受著流水的沖刷,就好像生命中永不停歇的磨難與苦痛一樣。所以主人公在目睹開篇首句所描述的景象之后,很自然地生發出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的消極思想與厭世情緒。無論是松柏、流水,還是水中的石頭,都讓他聯想到了流逝的生命,不可避免的死亡,以及人生中正在經歷的低谷與磨難。
再往下:“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通過這一連串真實景象的描寫,主人公的真實心情也一點點在讀者面前剖露開來。起先說以斗酒為樂,駑馬為游戲。斗酒雖少(薄),但權且當作“厚”酒,駑馬雖劣,不也可以帶著我“游戲宛與洛”,遍看這一路風光嗎?這一句,乍看之下,倒頗有些道家的灑落了。但隨著接踵而來的真實景象,卻打破了主人公內心自我安慰般的灑脫假象,越來越流露中一股不平來。冠帶郁郁,衢巷縱橫,第宅眾多,宮闕壯偉,主人公嘴里說的是灑脫,眼里看到的卻盡是這滿目的繁華。可見他的灑脫,并不為真心。再加上洛中雖富貴,冠帶者只是自相求索往來,并不把他人放在眼下。貧賤與富貴之間有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在眼前的繁華勝景與自己貧困潦倒的強烈對比之下,一股隱隱的牢騷不平油然而生,加之又對自身處境有著明確而清晰的認識,貧窮與富貴的界限終究難以跨越,干脆產生了“極宴娛心意”,要及時行樂的想法,還反問自己“戚戚何所迫”?
詩歌情境與所要表達的情感之間聯系的非常真實自然,每一場景物的變化,都能加深一點作者情感的表達,讀者如管中窺豹,一點一點窺見主人公內心真實的不平之鳴。到最后,強烈的情感噴薄而出,顯得更為真實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