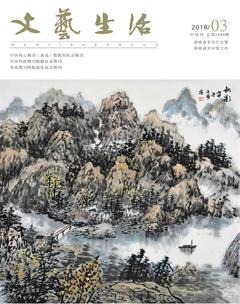淺析“場景”中的云南壯族民間舞蹈
石少奇
摘要:壯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作為中國民族瑰寶中最龐大的一支,其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歌舞文化無疑不使無數學者心馳神往。本文引入“場景”的概念,分析在不同場景中的壯族舞蹈發展狀態,并從身體視野解讀當今云南壯族民間舞蹈在時代背景下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場景;云南壯族民間舞;身體觀;傳承;發展
中圖分類號:J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08-0134-02
一、前言
壯族舞蹈為壯族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直接反映著壯族的社會生活,與其所生活的歷史、自然環境、民風民俗、宗教信仰以及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在這種人地關系的發展變革中,當然具備了地域性的基本特征。壯族舞蹈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又主要取決于這個民族的生存環境,地域所至的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居住環境、勞作方式、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性格取向以及觀念形態導致的客觀條件存在。使舞蹈形成了既有多個支系的風格特點又決定了舞蹈具備多樣性,獨特性、地域性的文化基本特征。
這種多風格特征的舞蹈形式,我們可以從不同“場景”的角度,去分析云南壯族民間舞蹈的形成因素。這里我們引入了樸永光教授對“場景”概念的詮釋。“場景”實由兩個概念復合而成,即“場”與“景”。“場”指空間,“景”意指場中的景象,實為場中的人所做事的情景。由此可見,“場景”是一定的人在一定的空間做著一定的事。
如果在“場景”上再添加一個時間概念,即一定的人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做著一定的事,即為歷史場景。如果在“場景”上再添加一個具體事的概念,如藝術創作,即藝術創作者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做著藝術創作的事,視為藝術創作的歷史場景。也就是說,實在的場景是由“人、事、時間、空間”等要素構成的具體展開的實景。
二、不同場景中的壯族民間舞
(一)場景與壯族祭祀舞蹈
文山州壯族舞蹈的起源都有一個共性,在其形成的初始,總是與宗教、巫舞密不可分。在壯族人民日常生活里,普遍存在“萬物有靈”的觀念意識。有自己的神靈崇拜對象和不同的宗教祭典儀式。每當發生自然災害或是村里老人病死,都認為是妖魔作怪,請來“魔公”和“師娘”驅鬼除魔。因為魔公、師娘是負責壯族社會宗教活動的頭目。認為魔公是神能與鬼對話。其實是負責念經文作道場,師娘是專管請鬼、送鬼、行巫術以治病消災。認為二者是人與鬼溝通的媒介。驅鬼除魔就必然舉行各種宗教祭祀活動。舉行宗教儀式時,他們總是頭戴面具,手持樹枝,身穿巫衣,以舞蹈和誦經來變現巫術的內容,手舞足蹈又念又跳。使無形之神成為可以被感知的有形之身。是神秘力量的人格化,用于祈求神靈保佑,除去病魔災害,逢兇化吉,人畜興旺,五谷豐登,以答謝神靈的恩賜。
壯族宗教祭祀舞蹈,多于驅鬼除妖,超度亡靈有密切關系,不論是人的生老病死,還是平日生活與勞作,都離不開祭祀舞蹈。這類舞蹈一般無固定時間,而是家中主事長者根據當事人的生辰八字和當地的人文氣候來選定日子、時間進行儀式。在儀式的途中跳這類舞蹈。領頭舞者主要是從事宗教的職業者,即民間稱之為“摩公”、“師娘”,其他則大多為當地村民。由于在儀式上渲染的是人、鬼、神三界的關系,因而整個場面的氣氛顯得凝重肅穆,再配上古樸的舞蹈動作,沉悶的鼓點節奏和摩公、師娘做道場時發出“哦,哦…”的念經聲,仿佛將觀眾也置身于鬼神交通的神秘場景中。壯族祭祀舞蹈涵蓋“跳銅鼓”、“龍阿耶”、“金錢棍”等多樣性功能的民族民間舞蹈。由于時代的發展進步,祭祀舞蹈的功能不斷淡化,其表現形式多用于娛樂、喜慶節日中,深受廣大群眾喜愛。
(二)場景與勞動舞蹈
舞蹈在人類社會中,與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在文山州少數民族民間舞里,大多都與勞動有著密切的聯系,其功能作用是人們用來傳授生產、生活知識的一種文明途徑,因為生產勞動舞蹈它不受年齡和地域環境的限制,人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地點則更加沒有限制,早期農民們在田間地頭勞動之余當做自娛的活動,而現在則多在廣場,文化館等場所表演。時間也沒有固定的日期,多在節日慶典時舉辦。
在取材方面和表現形式方面。始終保持著從勞動中來,到勞動中去的原始而又樸素的傳統傳承方式。勞動舞蹈也因此更加自然與自娛。
在壯族,其厚重的“稻作”文化就是勞作的真實寫照,在民間許多與勞動有關的舞蹈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文山州壯族勞動舞蹈有草人舞,盤子舞,春堂舞等,這些舞蹈都是在每年“開年節”或吉慶與豐收時節表演,這些舞蹈展現的或是耕田犁地、或是婦女穿針引線、或是舂稻谷的熱烈場面。壯族原本就是一個以勞動為生的勤勞民族,勞動賦予他們智慧,并從中積累了豐富的民間舞蹈文化。壯族兒女在獲得大量的生產資料信息后,創造了由生產勞動場景構成的文化總和。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壯族人民對勞動的贊美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應該說這正是壯族人民勞動舞蹈的全部內涵。
(三)場景與習俗舞蹈
習俗舞蹈展演儀式在延續社會傳統,整合族群心意狀態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而這些作用通常會借助藝術審美的手段來加以強化。因此,當習俗舞蹈隨族群延續而作為一種傳統固定下來以后,交融在儀式中的審美活動也因此獲得某種客觀存在的村落習俗意義,習俗舞蹈在村落傳統習俗展演儀式中完成習俗與審美的和諧同構。具有促進鄉民心靈意志的統一,整合族群公共意志的社會功能。從部落原始初民的生命過程儀式,到文明社會村落生活的日常與節日的狂歡,習俗舞蹈在神圣習俗與藝術審美的和諧同構中,實現了村落傳統的維護與發展。隨著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民間習俗的個人情感體驗逐漸弱化,藝術審美的比重日趨上升甚至出現置換。
文山壯族習俗舞蹈有扇子舞、棒棒燈等舞蹈形式。扇子舞至今兩百多年歷史,源于文山富寧縣的土戲。“扇子舞”既保持了土戲原有的輕盈、含蓄、內向的風格特征,又吸收了云南花燈扇子的一些形態特征。“棒棒燈”主要流傳于硯山縣的者臘,批灑,洋格和路德的腳澤龍壯族聚居村。每年正月初二至十六最為盛行,是一種集“牛頭舞”、“手巾舞”和說白對歌為一體的綜合性民間歌舞。習俗舞蹈,由于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壯族社會文化中具有一定地位。然而將生活習俗舞蹈從形式到內容加以分析,應該是宗教祭祀舞蹈的延伸,是宗教祭祀舞逐漸向娛樂、喜慶舞蹈發展的一種過渡形式,朝著娛人多娛神的方向發展。
三、壯族舞蹈的事
“民族舞蹈”是以民族為單元界分文化的概念,是舞蹈中具有民族屬性的舞蹈存在,或是民族屬性視角對舞蹈存在的確認。因此,圍繞著民族有三個核心概念,即“存在”、“確認”、“民族屬性”。在古代社會,民族舞蹈是由民族民間舞蹈和民族的宮廷舞蹈,或由民族的宗教性舞蹈和民族的世俗性舞蹈構成。而在當代社會,民族舞蹈由傳統形態、改編形態、創作形態構成。這些形態存在于“田野”、“廣場”、“教室”、“舞臺”等空間,并依照各自的語法在“傳承”、“被改編”、“被創作”以及“被研究”等。因此形成了民族舞蹈的不同場景以及場景中人的身份。
(一)“保護”
即做保護傳統舞蹈的事,其人既做保護的事,也做傳承的事。其“場”可籠統地稱為“文化空間”或“民俗空間”,進入這個場界的人既有參與展演的人,也有觀看民俗活動的人。目前保護文山壯族舞蹈的事主要由政府組織和民間自發組織兩種組織形式。在政府的主導下,壯族傳統民間舞得到了有效的保護,如“銅鼓舞”被列為國家級非遺項目,“紙馬舞”、“弄婭歪”、“棒棒燈”、“草人舞”、“男子手巾舞”被列入省級非遺項目。
除此之外,由政府舉辦的文山各地州縣文藝活動,也都有手巾舞、銅鼓舞、棒棒燈等壯族民間舞蹈參與的身影。主要團體有文山州民族歌舞團以及各縣級歌舞團,而近幾年來,各村委會的文藝隊伍越來越壯大,在各州縣舉辦的文藝晚會上大放異彩。
(二)“教育”
隨著政府對大中小學的的民間舞教育越來越重視,民間傳統舞蹈得到了很好的普及與發展。如云南藝術學院每年舉辦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活動,使學生們更近距離的學習到民間最淳樸、最傳統的民族舞蹈文化。舞蹈學院還積極組織學生到民間進行田野調查,與勞動人民同吃同處,更真切的體驗到民間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地域環境、民風民俗與民族心理。各地青年文化宮以比賽或慰問演出的形式,編創了很多優秀的少兒民族舞蹈,使學生們從小就對民族舞蹈有一個良好的認識。更有各縣鎮將壯族民間舞蹈融入進課間操,使學生們在鍛煉身體之余學習掌握本地的民族民間舞蹈。
(三)“創作”
壯族舞蹈的舞臺藝術作品創作,將傳統壯族舞素材作為表現的手段,使之為表現一定的內容服務,這也是中國語境中對舞臺舞蹈作品創作的理解。因此,在使用壯族舞素材時就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動作樣式,而是在原有樣式的基礎上再發展,使得動作語言更豐富,藝術性更強。而且以加工、美化的壯族舞動作為主要手段,塑造舞臺藝術形象,表現壯族民眾的思想感情,體現編導的審美思想。壯族舞蹈作品創作,有的是為專業團體表演所量身定做,也有的是為業余舞蹈愛好者表演所創,由于表演者的身份不同,舞蹈樣式也有一定的區別。同時,成人表演和少兒表演壯族民間舞蹈作品,也有一定的差異。
四、結語
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壯族兒女,在文山這片沃土上孕育出燦爛的壯族傳統文化。其民間舞更是風格多樣,功能性因場景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其中祭祀舞蹈、勞動舞蹈、民俗舞蹈隨時代發展被用于民俗活動、藝術表演、民族自娛等活動中。
當下,壯族民間舞依照不同場景的語境展開,由此形成了保護、傳承、發展的格局,也即當下中國壯族民間舞各種場景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