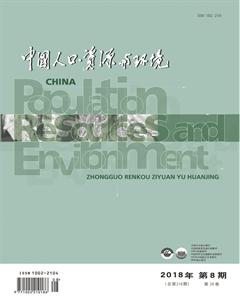西方環境風險感知:研究進路、細分論域與學術反思
2018-10-22 09:55:06王剛宋鍇業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8年8期
關鍵詞:影響因素
王剛 宋鍇業
摘要工業化與城市化背景下帶來的嚴重環境問題和潛在環境風險已成為當代社會的日常景象,這要求人們更加理性地面對環境風險。但由于公眾環境風險感知的差異,高環境風險感知引發的環境抗爭、政策失敗等過度風險反應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因此,整體性地描繪環境風險感知的研究全貌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它既是實現有效環境風險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會治理領域重要的現實課題。本文以西方環境風險感知經典研究的介紹為引,詳述了環境風險感知研究變遷的歷史后發現:西方環境風險感知研究體現了跨學科的特性,其對這一概念的認知和界定方式,呈現出從心理難題、文化結果到抗爭過程的視角變遷。進一步分析發現:①受專業背景的干預,不同學科研究者對環境風險感知概念的認知呈現出“寬泛”與“嚴格”的明顯分異;②環境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研究業已成為環境風險感知研究領域的核心議題。且產生出具有繼起關系的三種解釋:即“環境風險維度”“個體特征維度”“社會文化維度”;③已有環境風險感知研究的理論取向遵循著從“技術決定”向“社會建構”轉變以及從“事物邏輯”向“社群邏輯”更替兩條演變主線。其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需要反思:多學科的研究進路和概念認知缺乏有效的對話與融合;多維度的結構性影響因素尚未形成整體性分析機制;理論取向的演變未曾實現研究的融合。……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現代經濟信息(2016年19期)2016-10-20 18:46:44
現代經濟信息(2016年19期)2016-10-20 18:12:28
現代經濟信息(2016年19期)2016-10-20 16:20:30
中國科技博覽(2016年19期)2016-10-19 13:33:22
中國科技博覽(2016年18期)2016-10-19 10:49:54
中國科技博覽(2016年18期)2016-10-19 08:16:45
中國科技博覽(2016年18期)2016-10-19 06:39:44
中國市場(2016年36期)2016-10-19 03:54:01
中國市場(2016年35期)2016-10-19 02:30:10
商(2016年27期)2016-10-17 07: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