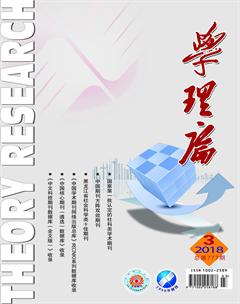毛澤東農民教育對軍隊基層政治教育的啟示
粟盛玉
摘 要:在以移動互聯網為特征的新時代環境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時應回到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中尋找破解思路:要運用科學的理論工具分析教育對象、要著力為官兵解決真實而關鍵的問題、要進入基層官兵的生活境域、要依托高效的新興滲透載體。
關鍵詞:毛澤東;農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3-0059-04
如何對農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問題。由于初創時期的人民軍隊主要由農民組成,所以農民教育問題不僅涉及中國革命的群眾根基,還關系人民軍隊的先進性,是軍隊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聲。在當前改革強軍的大背景下,時代呼喚基層思想政治教育拿出最扎實的效果。學習毛澤東關于農民教育的成功經驗,將對我們做好基層思想政治教育產生巨大的啟示意義。
一、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則
通過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與思考,毛澤東很早就清醒意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關鍵性作用,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已指出了對農民進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在此后長期的思索、實踐和反思中,毛澤東逐步把握住了對農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規律,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農民教育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教育實踐的基本原則。
(一)教育的起點:階級分析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認為,個人或階級在宏觀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決定了其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其他一切領域里的生存狀態與思維方式。農民作為一個階級,有該階級所獨有的立場與訴求。而農民內部又分化為不同階層,不同階層農民的政治態度、思想傾向也是不一樣的。只有堅持階級分析原則,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教育對象的階級特征與階層特性,才能在對農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做到有的放矢,對癥下藥。
毛澤東熟諳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早在192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中就科學地對中國農民階級進行了剖析,初步形成了符合客觀實際的農民階級圖譜。在1930年《興國調查》中,毛澤東通過調查,概括出土地革命前后各階級、各階層經濟地位的變化情況,進而推導出不同階層農民的基本態度和思想情況,為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了邏輯起點。
(二)教育的動力:利益維護原則
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論述思想與群眾的關系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毛澤東也深刻認識到,要使對農民的思想教育獲得感召力,就必須從農民的立場出發,滿足農民的實際利益訴求。于是,在之前階級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迅速鎖定了對中國農民來說最大的利益:占有農業生產中的核心生產資料——土地。他提出:“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2]沿著這一思路,他創造性地將對農民的政治教育和土地改革結合起來,成功激發起廣大農民空前高漲的革命熱情。
1933年,毛澤東對閩西上杭縣才溪鄉進行了實地調查。在《才溪鄉調查》中,他總結到:“這樣大數量的擴大紅軍,如果不從經濟上、生產上去徹底解決問題,是決然辦不到的。只有拿經濟上的動員配合著政治上的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熱潮。”[3]可以說,利益維護與教育動員的結合,為面向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最強大的動力。
(三)教育的方法:貼近生活原則
理論要想成為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就必須掌握群眾,必須進入群眾的生活。毛澤東歷來反對離開中國實際去照搬照抄理論,要求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通俗易懂,貼近生活。
毛澤東本人就是此原則的最好貫徹者。他有著深厚的哲學功底與古典文學素養,但對農民講課、做報告時卻從不掉書袋,語言通俗。但這卻是當時農民耳中活生生的語言,他們熟悉的、愿意傾聽的語言。1929年,毛澤東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教學十條原則:“啟發式(廢止注入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以姿勢助說話;后次復習前次的概念;要提綱;干部班要用討論式。”[4]正是這種放下架子、貼近生活、符合規律的教育方法,把我黨先進的立場、觀點一點點傳遞給了廣大農民。
(四)教育的形式:多重滲透原則
感受是一種比說教更強大的力量,尤其是針對當時還不習慣理論思考的農民。對農民的教育,毛澤東主張采取生動、直觀的形式,用農民喜聞樂見的文化載體,將黨的方針政策和革命理論一點點地滲透進農民的精神世界。他提出了很多具體的形式:“第一口頭講話,第二貼布告,第三寫標語,第四出傳單,第五演新劇,第六墻報上做文章,等等。”[4]秧歌、戲曲、合唱、標語、簡報、春聯、漫畫等各種教育形式迅速在農村推廣開來,像磁石一樣吸住了農民的眼睛、耳朵以及思想。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文學藝術要為革命服務、為群眾服務的方針。以此為標志,中國最廣大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與中國最先進知識分子的文學藝術創作之間,形成了一個牢固的接口。這一方針此后被長期貫徹下來。一大批飽含革命熱情、充滿藝術魅力又廣受農民喜愛的文藝作品噴涌而出,其中很多成了真正的經典,至今仍被我們傳唱。可以說,文藝是毛澤東為農民思想政治教育找到的一口極具滲透力的紅色染缸。
二、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與當前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點
站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軍隊政治工作面臨著新的情況、新的環境、新的要求。我們不禁要問:數十年前的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是否還具有繼續挖掘的價值?是否還適用于指導今天的基層思想政治教育?答案絕對是肯定的。因為從教育的性質、目的、對象、內容等多個方面考察,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與當前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都有著驚人的契合。
(一)講政治:均有鮮明的政治性
任何政黨都以掌握或參與國家政權為基本目標,都需要調用一套包含愿景與綱領的意識形態系統對自身的存在與行動進行合法性闡釋。對我黨而言,無論是對農民的教育還是對軍隊廣大官兵的教育,都具有明確的政治導向。
面對農民巨大的整體力量與相對落后的階級觀念這一矛盾,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5]如何把農民的力量導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是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要回答的重要命題。同樣,作為在社會主義國家機器中合法壟斷了暴力的軍隊,我軍必須是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必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護衛者。而面對著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擁有多元思想觀念的當代青年官兵,如何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獲得他們的真心認同,是當前基層政治教育關鍵而又艱巨的任務。
可以看到,毛澤東主張的農民教育與當代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極為鮮明的政治性。從教育目的上看,二者均力圖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最廣大范圍內得到理解、認可和擁護;從教育內容上看,二者均以意識形態的闡述與推廣——即我們所說的政治教育——為核心內容;從教育組織上看,二者均由黨的宣傳部門總體規劃,由黨的基層組織具體實施。正因為擁有這樣的共性,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的基本思路與做法非常值得當前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借鑒、學習。
(二)重實戰:均有突出的實踐性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我黨的指導思想從來不是抽象的理論推演,而是步步實事求是、時時解決問題的結果。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也不是漂浮在半空的設想,它扎根在最具體的現實情況中。
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后,大量知識分子涌入延安,掀起了一場興辦學校的熱潮。一些人試圖將農民教育也納入正規的學校教育中,大規模關閉分散、簡易的農民教育場所,將農民集中到少數幾個正規學校接受教育。結果這種形式既不便于農民的家庭生產,又增加了農民的經濟負擔。在教育內容上,他們照搬國民政府的課程內容,脫離農村實際,遠離農民生活,極大破壞了農民的學習熱情。毛澤東及時制止了這一脫離實際的行動,指出農民教育要立足當前的戰爭環境、立足農村的現有設施、立足農民的認知特點,把農民思想政治教育與敵后斗爭、勞動生產、日常生活結合起來。在他的指導下,各抗日根據地因地制宜的冬學、讀報識字組、夜校、民教館等得到了復興和推廣,使我黨在廣闊農村的思想陣地愈發穩固。
在當前強軍興軍的征程上,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強調一個“實”字,這與毛澤東農民教育的唯實理念高度一致。一是都瞄準實戰。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成形于殘酷的敵我武裝斗爭中,教育活動時時面臨著非常現實的軍事威脅,這使得教育的形式與內容都高度貼近實戰;在當前的人民軍隊,戰斗力標準已牢牢立起,廣大基層部隊也亟須一套能夠真正面向戰場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二是都立足實際。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里那種強烈的實事求是氣質,我們能在前例里切實感受到;今天的軍隊基層思想政治工作也面臨著具體而嚴峻的“實際”,一方面是更加開放的軍營環境、更加多元的社會價值、更加活躍的教育對象,另一方面是略顯僵化的教育模式和非專業的政治工作者隊伍,這需要我們有能力有智慧將當下的實際與未來的需求調和起來。三是都追求實效。無論是之前的農民教育還是當下的軍隊思想政治教育,都追求實際的教育效果,并要求這一效果能夠通過教育對象的行為表現出來,能夠在戰場上得到檢驗。
(三)接地氣:均有顯著的基層性
“群眾給歷史規定了它的‘任務和它的‘活動。”[1]只有掌握住處在最基層的廣大群眾,才可能汲取到推動歷史發展的最強大力量。群眾路線的成功,人民戰爭的偉大,都取決于它們遵循了這一唯物主義的歷史規律。而農民教育和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其要義都是要掌握群眾,掌握住大眾或軍隊中最根基的部分。可以說,二者都是對群眾、對蘊含于群眾中的磅礴物質力量的自覺追尋,是對群眾路線和人民戰爭思想更趨具體的落實。接地氣、重基層,也就成了二者必然的共有的特性。
從更加細節處審視,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與當前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層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都面向相對低層的對象。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國農民大多數是文盲,他們對于當時中國和世界的宏觀了解基本為零,同時具有明顯的階級局限性,如毛澤東所說:“中國農民群眾……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5]雖然當前軍隊基層士兵的文化層次、學歷水平一直在逐年提高,但相較于社會整體,參軍入伍依然還主要是低學歷青年的選擇。二是都教授比較基礎的內容。對農民教授的內容主要是掃盲,講解黨的土地、參軍優待、婦女解放政策,以訴苦大會為主要形式的革命對象教育等。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也主要是講政策、擺事實,從大框架上宣傳黨的創新理論,再加上一些情感層面的激勵和鼓動。二者都簡單明了,沒有復雜的歸納或演繹,也基本上不刻意追求深度。三是都廣泛使用非專業的教育實施者。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出發,毛澤東堅信人民群眾有能力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對農民的政治教育中他非常注重對農民教育骨干的培養與使用。農民教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場群眾性的自我教育活動。當前的軍隊政治工作情況也很類似,大多數一線教育者沒有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或政治工作學等任一方面的專業背景,都需要邊學邊做,邊做邊學。
三、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對做好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從改革開放至今,人民軍隊所面對的時代環境發生了極其劇烈的變動。全新的時代特征給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全新的挑戰。一是移動互聯網的挑戰。智能手機及以之為平臺的一整套消費、娛樂、社交網絡的高速發展,賦予移動終端極大的黏性。只要有機會,大部分基層官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拿手機。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不得不與為數眾多的微信公眾號、視頻、直播、網劇、手游、漫畫爭奪基層官兵的眼球和耳膜。二是多元價值觀的挑戰。當今中國社會不再處于一種由單一發聲渠道絕對掌控的局面。一批擁有龐大用戶群的網絡自媒體占據了輿論風口,一批擁有百萬粉絲的意見領袖主導著一個個社群。代表多種價值觀的聲音隨處可見。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所宣揚的主旋律價值觀,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無須解釋的天然權威,而是要承受多元觀念的沖撞與考驗。三是開放環境的挑戰。基層部隊的外部環境曾經是相對封閉的,外界的干擾和雜音很少,在這種封閉式環境中對官兵進行思想灌輸比較簡單。經過幾十年的對外開放,部隊所處的大環境已經高度開放,這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處在這種環境中的基層官兵大都視野開闊、思維活躍,對其再用老一套的灌輸式教育已經難有成效。四是脫離實戰的挑戰。戰爭年代,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到位、是否提高了部隊戰斗力,能馬上接受戰爭的檢驗與反饋。政治工作者能高頻地試錯與調整,并迅速找到最適應實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而長久脫離戰場,只能通過別國經驗、理論推演、演練演習進行判斷,終究與真實戰場存在差距,基層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有的放矢難度很大。戰爭年代,基層部隊優勝劣汰的壓力極大。而長久脫離實戰的部隊則不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其效果往往需要通過其他活動間接表達,很多時候做好做壞表面上看不出顯著差別。所以基層思想政治教育實施者很容易以應對上級檢查為導向,把主要精力放在確保官兵背記要點、補齊筆記等形式的完備上。
面對這些新的情況,我們可以試著回到原點,回到問題本身,回到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那里尋找破解的思路。
(一)要運用科學的理論工具分析教育對象
在毛澤東那里,分析農民是教育農民的起點。軍隊思想政治教育沿用了此方法,卻很少深挖這一做法的思想內核,未能將其充實發展以不斷適應新的問題。長期以來,分析教育對象在基層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理解中無非是通過談心掌握其自然情況,如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社會經歷、個人愛好等,以此表征教育對象可能的思想和行為傾向。這種分析模式能夠取得一定效果,但其訪談方式、信息結構、分析方法都缺乏科學的操作指導,高度依賴個人經驗和習慣,容易受刻板效應影響對官兵特點做出機械、片面的判斷。事實上,毛澤東對農民的調查與分析絕不是簡單的率性為之,而是具有使用科學方法的自覺。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毛澤東就研讀了大量西方前沿學術理論。如嚴復在1903年翻譯的《群學肄言》——即著名實證主義社會學家斯賓塞在1873年發表的《社會學研究》,毛澤東就曾仔細研讀并寫出體會[6]。毛澤東參照了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前沿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其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的實地調查都展現出極高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反觀當下,系統抽樣與調查的方法早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被廣泛使用,復雜性科學在20世紀80年代就被創立并迅速成為指導美軍建設的重要理論,依托大數據的社科分析方法也在全面興起。無論是在研究上還是在實踐上,我軍思想政治教育對這些理論工具都使用不多甚至聞所未聞,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亟須各級政治工作者、各方向的政工研究者,提高自身運用科學理論工具的意識與能力。
(二)要著力為官兵解決真實而關鍵的問題
毛澤東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通過為農民解決現實問題打開了進入廣大農民觀念世界的突破口,而他所抓住的問題——土地問題——又是最真實、最切中要害的問題。軍隊基層思想政治教育也應當結合當前實際,努力發現和解決官兵所面臨的真實的、關鍵的問題。一是解決真實的問題。這一要求看起來似乎多余,但我們做得并不好。一些基層政治工作者習慣想當然地以為自己了解基層官兵的需要,不作深入調查研究,憑直覺行事。例如有些單位以豐富官兵業余文化生活為目的,在節假日高密度地安排晚會表演活動、體育競技活動等,導致官兵感覺放假過節比正課還累。這看似在為官兵著想,其實解決的只是虛構的問題、不真實的問題。二是解決關鍵性問題。作為群體的教育對象不可能擁有絕對一致的利益訴求。在資源和精力都有限的情況下,有必要抓住主要矛盾,為官兵解決關鍵性問題,在可接受的成本內實現效益的最大化。不應讓精力過多被牽扯在不重要的,或者重要但當前不可解的問題上。其實毛澤東當時也面對著農民群體高度復雜的利益訴求,例如離婚問題。《尋烏調查》就記錄了一些根據地男性農民的怨言:“同志!你唔要來講了,再講埃村子里的女人會跑光了!”[7]但毛澤東正確地判斷出這不屬于關鍵性問題,會隨著土改的深入而自然解決。三是將解決問題與思想政治教育順暢對接。解決問題的目的,終究是要使教育對象在增強的獲得感中、在對基層黨組織的認可中,全面接受黨的理念、認同黨的主張。毛澤東就實現了解決問題與政治教育的順暢對接,把廣大農民的獲得感都最終引向了對“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發自肺腑的呼喊。所以軍隊基層政治工作者在解決好問題后,還要做好進一步的意義闡釋和價值引導。
(三)要進入基層官兵的生活境域
貼近生活是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的重要原則,但這不意味著只講日常瑣碎,不談革命理想。貼近生活的目的是要尋找到一個恰當的支點,撬開教育對象的認知體系,使教育內容進入其生活境域。境域(Horizont)是現象學的重要概念。胡塞爾將其描述為一種“特殊世界”,我們只有在其中才能以主題的方式生活,它是我們興趣的地平線[8]。簡言之,一個人的生活境域就是與他發生意義關聯的存在者的總和。一件事物只有進入官兵的生活境域,才能與他們發生相互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效,就必須進入官兵的生活境域。當前有的基層政治工作者習慣于照本宣科地傳達文件,這固然最大限度地確保了教育內容的權威性與準確性,也能使官兵接收到全部內容甚至背出要點,但往往無法使抽象的理論表述與基層官兵具體的生活構建起關聯。沒有進入官兵生活境域的理論,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堆抽象的教條,根本談不上領會、認同或踐行。
如何使政治教育進入基層官兵的生活境域呢?毛澤東為我們提供了兩方面的思路。一方面,要使教育內容與官兵建立連接。以標語為例,從現存的史料看,中央蘇區從未出現過類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的對我黨大政方針進行直接概括的標語,而大多是“打土豪,分田地”“勞動青年加入紅軍!”[9]這樣的與農民生活連接緊密、可以直接指導其行動的內容。與之相反,在當前一些部隊營區內,經常可以看到將宏觀論述直接拿來作標語的現象。有些論述是高度抽象的,若沒有進一步的闡釋,很難與官兵建立起連接,至少起不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要使教育內容直觀化,尤其是可視化。毛澤東對農民的教育生動直觀。在直接教育中使用訴苦大會、現身說法等富有畫面感的教育方法,在生活中廣泛運用秧歌、戲曲、標語、簡報、漫畫等直觀可視的表現方式。當前我軍官方發布的一些教育漫畫、動畫、微電影,畫風清新,語言生動,熱度持續走高,是朝此方向的一種有益嘗試。
(四)要依托高效的新興滲透載體
毛澤東農民教育運用了一系列高效的滲透載體,最典型的是戲劇。戲劇可以說是當時最有受眾吸引力的、滲透力最強的載體之一,對于那時的中國鄉村社會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如在贛南、閩西農村地區,演戲之風十分興盛,“古戲臺星羅棋布,遍及全區城鄉,以寧都為例最多時多達147座”[10]。我黨依托戲劇這一載體對農民進行教育,將先進的政治寓意和內涵嵌入傳統戲劇的唱段中,在廣大農民中取得了十分驚人的教育效果。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延安實地采訪后這樣寫道:“紅軍占領一個地方以后,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了基本的了解,廣泛地傳播了革命思想,爭取了人民的信任。”[11]
很遺憾,對于當今時代最高效的滲透載體,例如短視頻、網劇、手游、直播、社交媒體等,我們并沒有在軍隊政治工作中很好地運用,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一方面是由于我們缺乏認識,將短、平、快的現代傳媒所展示的內容視為庸俗文化,視為應該批判的對象,甚至用行政手段限制基層官兵與之接觸,要求他們只讀馬列原著和黨的理論。這種批判與揚棄的眼光值得肯定,但這種做法卻嚴重脫離實際。如果按照這種思路,毛澤東時代的農民教育豈不是該只組織農民研讀《共產黨宣言》、學習《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澤東不但沒有這么做,反而對當時質疑戲劇的同志嚴肅指出:“不能把人民喜聞樂見的土里土氣的東西斥之為低級趣味。”[12]另一方面,我們也缺乏使用新興滲透載體的能力。新媒體的運營、內容的制作與分發、粉絲的互動與管理,都有一套全新的模式,遵循著全新的規律。相較于商業新媒體,軍隊政治工作部門及政治工作人員對這些規律的把握還非常有限。總之,我們應當解放思想,提高能力,在基層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運用新興滲透載體的力量。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502,285.
[2][美]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斯諾文集:第1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208.
[3]毛澤東.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41-342.
[4]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4-105,271.
[5]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183.
[6]王樹山,王健夫.毛澤東書信賞析[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6-17.
[7]毛澤東.毛澤東中央革命根據地斗爭時期調查文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129.
[8][德]胡塞爾(E.Edmund Husserl).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M].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555.
[9]王建柱.見證中國革命歷史風云的“活化石”——記贛南中央蘇區標語和漫畫[J].文史春秋,2017(4).
[10]王永華.蘇區戲劇與中共意識形態教育的政治互動[J].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3).
[11][美]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M].董樂山,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110.
[12]張恒.毛澤東和戲曲[J].中國戲劇,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