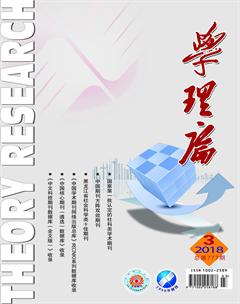“天人合一”及其思想價值略論
劉光偉
摘 要:“天人合一”思想漫長而復雜的演進過程也是中國古代主要學派在天人關系問題上交鋒與交融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天人合一”之“天”也被賦予了多重含義。“天人合一”思想對現代中國的國家政治、民族文化以及個體生命都影響至深。
關鍵詞:天人合一;發展歷程;天的含義;思想價值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3-0105-03
“天人合一”中的“人”一般是指人類或人類社會,而“天”則因時代不同、背景不同、流派不同而不斷被賦予不同的含義與色彩。這與西方哲學的“天”僅指“自然”(Nature)不盡相同。本文通過梳理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孕育、產生、發展和成熟等歷史進程,進而闡述了“天人合一”之“天”的多重含義,并探討了“天人合一”思想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長久而深遠的影響。
一、“天人合一”的演進歷程
(一)先秦時期的“天人合一”思想
胡適說:“我們可以把老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當作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1]26其實“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可追溯到這個時代。這個時代的子產曾發出疑問道:“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昭公十八年》)這顯然是在以人之道挑戰天之道,只不過略顯樸素和含蓄而已。
胡適說:“老子以前的天道觀念,都把天看作一個有意志、有知識、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1]41老子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道德經》第5章)的怒吼撕下了罩在“天”上的神秘面紗,打破了“天”的權威。同時老子提出了一個“道”的概念。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25章》),是老子把“天”的概念引向了“道”,引向了“自然”。應該說,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中,老子率先“打破了古代天人同類的謬說,立下了后來自然哲學的基礎”[1]42。從天命論到天道論,老子以“道”為最高哲學范疇的講法,把中國哲學引向了關于宇宙本原探索的新方向。
孔子很少談“天”,更不愿談“鬼”。當學生問及鬼神時,孔子反問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在天人關系問題上,孔子的觀點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然而孔子也曾說:“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史記·孔子世家》)又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顯然,孔子認為在人類之外是有一個講正義、重道德、有威嚴的神秘的“天”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李澤厚稱儒學為“一半是宗教,一半是哲學”[2]。孟子思想的核心是強調道德的先驗性,因此他提出了“四端”說和“性善”論。孟子將人性和道德與“天”相關聯。這種“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是一種“道德之天”,是一種“義理之天”。
李澤厚說:“《易》是由天而人,對外在世界即宇宙、歷史、生活作了多方面的論證。”[3]的確如此,《周易》之“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較早表述。而莊子之“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則是較早且更為明確地闡述了“天人合一”思想。胡適認為莊子的人生哲學可以用八個字概括,即“依乎天理,因其固然”[1]222。在天人關系上,莊子與老子一樣,更側重講“自然”之天,講人的精神追求,而遠離孔孟所言人倫道德之天。
胡適說荀子“獨創一種很激烈的學派”[1]248。這種“激烈”除了表現在荀子針對儒家先師“亞圣”孟子所倡之“性善論”而提出“性惡論”外,還表現在其對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批評上。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荀子認為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道,二者不必相干。這種“天人相分”的思想既有別于老莊又不同于孔孟,可謂是一種“別開生面”的“獨創”思想。所以張岱年說荀子是“中國哲學史上不講天人合一的思想家”[4]。
(二)漢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
到了漢代,“天人合一”思想已發展到較為成熟階段。漢代大儒董仲舒因提出“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而著稱。“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其對于“天人合一”的明確表述。對于天人關系,董仲舒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這是把“天人合一”思想向“天人相類”或“天人相通”方向進行了發展。
顯然,董仲舒“天人合一”之“天”對孔孟人倫道德之天的一脈相承和進一步發展。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于天”(《漢書·董仲舒傳》),天與人交相感應,“人事”善惡都將得到“天”的賞罰。
(三)宋明時期的“天人合一”思想
張載的“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張載集·正蒙》)是宋明時期關于“天人合一”最早的明確表述。張載以其“民胞物與”之說把儒家那種有等差之愛發展為一種“博愛”。在張載看來,這種“博愛”是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必要元素。朱熹依其“性即理”的主張提出了“天人一理”的思路。至于實現“天人合一”的路徑,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說,希望通過“格物致知”以達到“即物窮理”,從而實現“人”與“天”合一的理想狀態。王陽明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以“人”為主體的,是以人“心”之強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前提的。在王陽明看來實現這種“天人合一”唯有通過“知行合一”與“致良知”。王陽明這種強調道德良知的“萬物一體”思想,使得人與天地萬物之間達到一種融合無間的境地,從而“天人合一”思想發展到臻于完滿狀態。
二、“天人合一”之“天”的多重含義
(一)“天人合一”之“天”可以指“神意之天”
遠古先民對“天”的概念比較模糊,“天”“神”“上帝”對他們來說無甚分別,都至高無上,皆有神意可言。也就是說,這種神意之天是一種附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天”。此種“天”在《詩經》中較為常見。如: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詩經·小雅·天保》)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詩經·大雅·皇矣》)
這其中的“天”“上帝”都有著較為濃厚的神的意蘊。梁啟超認為古代的“天”“直接監督一切政治”[5]26。“天”的這種監督政治的特權,到了漢代被董仲舒發揮到了極致。董仲舒利用西漢人心中存有的“神意之天”觀念,巧妙地以神權統攝君權、父權、夫權,有機地融四者為一體,從而形成其完整、嚴密的帝制神學體系。毫無疑問,這套體系對中國人“神意之天”的觀念影響至深。
(二)“天人合一”之“天”可以指“自然之天”
遠古時期的先民對“天”的概念比較模糊,他們在產生“神意之天”的同時,“自然之天”的觀念也相伴而生。這種“自然之天”在《詩經》中也頻繁出現。如: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詩經·唐風·綢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經·小雅·北山》)
盡管這其中的“天”僅指“天空”,但已經初步表達出古人對于“自然之天”的認識。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的表述則是把“地”也納入了“自然之天”的范疇,體現了古人“自然之天”觀念的進一步發展。荀子承接老子,以唯物主義思想家的身姿大膽提出“天人相分”理論,進一步把“天”從“神”的層面剝離,指出“天”就是“自然”,并撰文《天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的主張。荀子指出,“天”即“自然”(Nature),不但沒有神意,而且是可以征服的。胡適對此非常贊賞,將其與西方的“戡天主義”(Conquestof Nature)相媲美。
(三)“天人合一”之“天”可以指“人文之天”
“人文”一詞最早見于《周易》。《周易》有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周公提出的“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等主張,明確將主流的“神意之天”融入道德、人文元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實際是開啟了中國哲學“人文之天”思想的先河。胡適說:“老子最大的功勞,在于走出天地萬物之外,別假設一個‘道字。”[1]42老子的這個“道”,性質上雖然無形、無聲,但卻無處不在,遠高于“自然之天”。這也為中國哲學之“天”向道德形上方向發展提供了又一種可能。孔孟在天人關系上則更側重強調“人”為,主張構建“仁德之天”“義理之天”,不斷賦“天”以人倫道德含義。朱熹和王陽明在“天人合一”問題上路徑上相反,一個主張“以天統人”,一個主張“以人統天”,但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于都主張以“氣理”和“良知”為載體將“天”道德化、人性化,賦“天”以“人文”色彩,從而實現“天人合一”。宋明理學和心學這種關于天人關系的形而上體系的建構,標志著儒學在形而上層面上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也使得中國哲學“人文之天”的觀念發展到了頂峰。
三、“天人合一”的思想價值
(一)“天人合一”是國家生態智慧的源頭
梁啟超認為,中國古代產生的對“天”、對“自然”的觀念是“后世一切政治思想之總根核”[5]27。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政府認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6]50。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這顯然是以“天人合一”思想為背景的當代中國國家生態文明觀和政治智慧。此外,中國政府還強調中國不僅要建設自己的生態文明,還要“為全球生態安全做出貢獻”[6]23。這種對全球生態安全的關注與奉獻,既體現了一個負責的大國在生態保護政策方面“兼濟天下”的政治情懷,也體現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普世價值。
(二)“天人合一”是民族文化生長的沃土
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來概括自己修《史記》的宗旨。史學家對天人關系的關注可見一斑。文學方面則更是如此。以詩歌為例,中國詩人總是喜歡寄情山水,他們筆下的山、水、田園等自然景物,往往易介入其主觀情感和人生體驗。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強調天人相通、人與自然和諧共融。這種特征自然也會被詩人以獨特的方式滲透于其具體詩作之中。如陶淵明詩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這里的“此中”即為陶潛始終心馳神往的大自然。只有回歸到大自然,詩人才覺得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他能找到生命“真意”的世界。也就是說,只有重歸這種“自然之天”,詩人的心靈才能得到慰藉,詩人的精神才能得以安頓。此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瑰寶的中醫、太極、建筑、音樂、國畫等無一不從“天人合一”思想中汲取精華,雖經數千年而不衰,并以勃勃生機展現于現代中國和世界。“天人合一”思想的普世價值決定了它不僅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蓬勃發展的沃土,也必將成為世界文化發展不可或缺的元素,從而為世界文化多樣性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三)“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精神情懷的家園
幾千年來“天人合一”思想始終在深層面的潛意識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一位中國人。中國人對“天人合一”的追求一方面表現在“人文之天”含義下,人在自我修養上的道德自省與自律;一方面表現在“神意之天”含義下,人對“天”的敬重與依賴。溝口雄三說:“中國的天的觀念,一直也沒有喪失它的影響。”[7]確實,中國人在極度悲痛時未嘗不呼天搶地,在欣喜若狂時未嘗不叩謝蒼天,在正義得到伸張時,未嘗不慨嘆老天有眼。人們這些在極端情感狀態下所生發的對“天”的呼喚與膜拜并非刻意而為,而是下意識之舉。在常態下,人們的生活中也不乏包含“神意之天”之語,如成語“天道酬勤”;熟語“人在做,天在看”;還有歌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這一切都說明,由來已久的對“天”的敬重和崇拜,使得世代中國人對“天”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情,賦天以多重含義,其一便是自覺不自覺地把“天”視為一種精神寄寓之所。但這種觀念不同于宗教,更不是迷信,而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天人合一”語境下的一種特有觀念。這種觀念是炎黃子孫從遠古至現代,以自己獨特的東方智慧尋求到的一個獨特的精神安頓之所。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人合一”思想無疑是中國人精神情懷的家園。
四、結語
“天人合一”思想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匯集了中國古代哲學主要學派的思想精華,并融入了政治、倫理、文學和藝術等諸多領域內容。“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強調“天”“地”“人”的共生共融,主張“人”通過提升內在的道德修養以達到超越的精神境界而與“天”心照神交。我們相信“天人合一”這一中華民族的原創智慧也必將為世界文明多樣性、為人類美好未來做出新的貢獻。
參考文獻: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2]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3]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4]張岱年.中國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1).
[5]梁啟超.梁啟超論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日]溝口雄三.中國的思想[M].趙士林,譯.北京:中國財富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