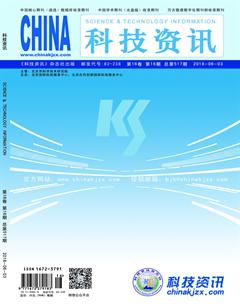隱喻的認知研究
王佳琪
摘 要:隱喻作為認知語言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和原型范疇理論、意象圖式等理論一起在認知語言學興起的三十多年內顛覆了人類的思維方式和對于客觀世界的看法。本文首先介紹認知語言學對隱喻的研究,隱喻的類型,通過大量的實例說明隱喻的復雜性、系統性和多層次性。進而考察漢語中的一些經典、常用的隱喻,以此揭示人類思維,主要是漢語語境下的人類思維模式。
關鍵詞:隱喻 萊考夫 認知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8)06(a)-0249-02
1 傳統的隱喻研究
西方自古有研究隱喻的傳統,分別是從修辭學、哲學和語言學這三個層面進行。
亞里士多德首先從修辭學的角度研究隱喻,他認為隱喻是根據一種類比和相似的原則,把一個事物的名稱轉用于另一個事物。后來和亞里士多德持同一觀點的學者豐富了對隱喻的看法,提出了所謂的“替換論”。他們都以相似為重點,認為隱喻是對詞語的修飾。比如老年之于生命,相當于黃昏之于白日,因此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替換,將黃昏稱為老年或將老年稱為黃昏。
柏拉圖從哲學的角度看待隱喻,和亞里士多德不同,他對隱喻持批判的態度。他認為哲學探討的是真理問題,而隱喻是花言巧語,與哲學大相徑庭。
最早由理查茲提出的“相互作用”是隱喻研究向語言學方向轉變的一個開端,提出話語成分在具體的陳述中互相激活和滲透,即“要旨”和“載體”互相影響對方,形成一種張力,繼而形成隱喻現象。“語言是不同領域的交匯點,不僅是認知的表現形式,而且也是它的組成部分。源于日常經驗的認知體系構成了語言運用的心理基礎[1]。”此后的本旺尼斯特、烏爾曼等人突破了傳統修辭學,把隱喻看成一種語義現象放到句子中,并且意識到了兩種概念之間的關聯存在于人的認知中。
2 隱喻的認知觀
隨著認知科學的發展,隱喻被以一種認知的方式重新研究。人們意識到,當人類從具體的概念中逐漸獲得抽象思維能力的時候,往往借助于表示具體事物的詞語表達抽象概念,這種抽象思維能力造就了人類的隱喻語言。其中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隱喻無處不在,它存在于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中,研究隱喻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人類思維的認知規律。
第一,隱喻是普遍存在的。傳統的隱喻觀忽略這一點正是因為隱喻已經深入到人類的認知里,人類對此習以為常,是無意識的日常語言的一部分。比如傳統隱喻的研究對象可能是“時間就是金錢”這樣的諺語,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時間—金錢的隱喻已經深入到我們的認知中。金錢是我們熟悉的,容易認知的,我們用它來概念化時間。
(1)你在浪費我的時間。(wasting)
(2)值得在那上面花時間嗎?(worth)
(3)我們的時間快用光了。(running out)
英語動詞更加一目了然,漢語和英語情況差不多。我們通過隱喻把時間概念化成和金錢一樣,是可以節省、可以浪費、可以花可以計劃的東西。
第二,隱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很多孤立的隱喻都能找到聯系,形成隱喻群。比如著名的“導管隱喻”,它指出言語交際就好像運送包裹,我們的觀念就是被送出去的物品,它被放在語句這個容器中,送到接受者那里,接受者再把物品從容器中取出,這樣的隱喻大量存在于我們的語言中。第一個隱喻,觀念是食物。比如“未加工的事實”,“難以消化的事實”,“貪婪地汲取知識”等。第二個隱喻,觀念是植物。比如“剛萌芽的想法”。第三個隱喻,觀念是資源,比如“揮霍我的信任”,“這種看法很普遍”等。這樣的關于“觀念”的隱喻有很多,他們并存并不矛盾,可以互相補充,形成一個關于觀念的隱喻群。
第三,隱喻不僅僅是語言問題,更是思維方式。思維過程本身就是隱喻性質的,如果仔細分析,我們一直以來的概念系統大多是以隱喻的方式構建的。這是隱喻最重要的特點。隱喻不僅根據具體事物的認知模式去構造其他事物的認識模式,而是整體性地將認知模式的內部結構關系轉移,是兩個范疇系統之間一致性的對比[2]。
也就是說,萊考夫等人的隱喻觀完全不同于傳統的隱喻觀,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不是修辭上說的比喻,不是“時間就是金錢”這樣的語言;而是一種認知現象,是大量無意識存在于語言中的,是“請不要浪費我的時間”類型的語言,本文討論的也是這樣的隱喻。
3 萊考夫:隱喻的三種類型
萊考夫總結了三種隱喻類型,分別為“結構隱喻、方位隱喻”和“本體隱喻”。
結構隱喻指的是通過一個概念來構建另一個概念,這兩個概念的認知域不同,但結構保持不變,存在著有規律的對應關系。萊考夫在結構隱喻中分析的最為細致的例子是“論爭”(argument)。它由四部分組成,分別是“論爭是旅行、論爭是戰爭、論爭是容器”和“論爭是建筑物”。這四部分分別說明論爭的不同特點,這四部分就是四個結構。近年來有語言學家歸納總結了一些人們常用的結構隱喻,比如死亡——離開,理解——看見,世界——舞臺,生氣——危險動物等。
方位隱喻不是用一個概念構造另一個,而是在同一概念系統內部,通過空間方位名詞組織起來的。人類對空間方位的感知能力是很容易獲得的,因此人類借助這個經驗去理解抽象的概念。最常見的隱喻是,上——高興、有意識、健康、好、多,下——難過、無意識、疾病、壞、少。比如:I am in high spirits/I am feeling down/wake up/he fell ill/turn the heat down等。我們人類睡覺時是躺著的,站立時是清醒的,悲傷壓抑時往往呈現低垂的姿勢,情感狀態飽滿時呈直立姿勢,而情緒高漲健康等對人類來說是好,反之是壞,由于上述這些因素,存在這樣的隱喻就不難理解了。人類對空間的理解非常充分,因此這類隱喻非常常見,而且大部分隱喻和相關概念聯系非常緊密,以至于難以拆開分析。
本體隱喻是指我們可以通過將一些抽象概念,如觀念感覺等視為有形的離散的實體,方便我們去把握和理解。比如:對考試的恐懼讓他不敢來上學/這世上有太多的仇恨/理解它要從兩方面入手,上述三個例子分別通過加指稱、量化、分層次三個辦法使抽象事物實體化[3]。本體隱喻中最重要的是容器隱喻,由于我們對容器的經驗太豐富了,因此這類隱喻非常普遍。只要我們能界定它們的時空邊界,它們都可以被隱喻為容器。比如視野、比賽、活動、狀態等。
(1)那艘船進入了我們的視野;(2)他退出了比賽;(3)我從勞動之中獲得了滿足;(4)她從昏迷中醒來。
我們發現這樣的隱喻已經和我們的日常語言緊密結合,難以看出這是隱喻了。這說明人類已經習慣于用具體的事物思考抽象的事物,隱喻成為我們認識世界和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即隱喻是由什么決定的?我們知道人類不可能無止境地創造新詞,遇到新事物時,我們選擇在熟悉事物基礎上,尋找新事物和原有事物的聯系,以此來認識新事物,因此產生了兩個認知域之間的投射。既然來源于兩個概念的相似,但一定不是只基于物理特征的相似,我們在感知事物時,是通過各種感官共同作用,而不僅僅是視覺。比如“山腳”這樣的語言不是我們討論的隱喻。筆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生理現象和物質經驗,人們在認知領域對兩個概念產生了相似的聯想。心理學家已經證明了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主客觀結合的產物,1975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語言學夏令營上,產生了四個舉世矚目的報告,其中之一就是Paul Key關于色彩詞的報告,它證明了人類認識和理解事物都需要人類認知系統的參與,或者說,人類自身構造了世界。人類的認知模式有創造性和共性,這也說明了很多隱喻在不同語言中的一致性。另外一個原因就要結合特定的社會文化經驗了。
4 漢語文化中的隱喻
事實上對隱喻在認知方面提出見解并不始于萊考夫,例如人類學家 Bebjamin Lee Whorf在1939年提出:“我們如果不通過與身體有關的隱喻就幾乎無法指稱哪怕是最簡單的非空間情景,我們的隱喻系統,利用空間經驗來命名非空間經驗……”語言學家Weinrich在1958年提出:“事實上,每一個詞都可能擁有隱喻意義,每一個事物都可以通過隱喻來表達[4]。”眾多對隱喻的看法互相交織,有助于人類更好的理解隱喻,我國自古以來也有其特殊文化背景下的隱喻。筆者從古詩詞和成語入手,總結了根植于我國文化內部的一些隱喻現象,我國自古以來就是通過空間和實體來認知抽象的事物。
第一,夢的隱喻。夢是容器,夢是非常典型的一個本體隱喻,它有明顯的時空邊界。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傍人不知夢中事,唯見玉釵時墜枕。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第二,關于智慧的隱喻。首先,智慧是金錢。足智多謀/學富五車/他是一個喜歡賣弄才華的人/恃才傲物/不要浪費你的才華。另外,智慧是水。才華橫溢/這幾句話滋潤了他的心。
第三,關于愛情的隱喻。愛情是自然景物。碧海青天/海誓山盟/落花流水/比起激情澎湃,我更喜歡細水長流。
第四,關于事業的隱喻。事業是植物。公司發展欣欣向榮/他的事業開始煥發蓬勃生機/碩果累累。
關于中國古代語言文化的隱喻,大多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入手,研究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母題。但文學隱喻也是隱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尤其需要對生活的感悟力和洞察力,需要注意的是,文學中的隱喻要和修辭學中的隱喻區分開。
對隱喻的研究還不是特別充分,但是人們認識到了隱喻的普遍存在和重要作用,它既然是一種思維方式,就可以廣泛地運用到其他領域,幫助人們認識新事物,命名新事物,因此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隱喻都正在占有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 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 張敏.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8.
[3] 高遠.李福印.喬治·萊考夫認知語言學十講[M].北京: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4] 石毓智.《女人,火,危險事物范疇揭示了思維的什么奧秘》評介[J].國外語言學,1995(2):97-98.
[5] 束定芳.試論現代隱喻學的研究目標、方法和任務[J].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996(2):9-16.
[6] 束定芳,湯本慶.隱喻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與研究課題[J].外語研究,200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