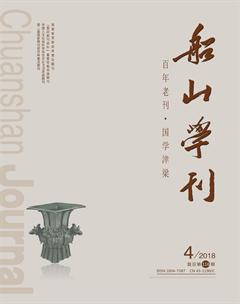論王先謙《駢文類纂》的刊刻傳播
莫道才 劉振乾
摘 要: 王先謙不僅是一位傳統的學者型官紳,而且是一位兼具湖湘情懷的出版人。《駢文類纂》是其編纂的一部集大成的駢文選本。書局和書院為其刊刻出版提供了傳播媒介和平臺。《駢文類纂》的刊刻傳播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通過刊刻渠道的時空轉移,助推湖湘出版業,提高湖湘駢文的傳播質量;通過古文選本的文體關聯,擴大駢體文的影響力,促進駢體與散體之間的均衡發展;通過選文存人及個性化布局,輻射整個清代駢文作家群體,推動清代駢文經典化。
關鍵詞: 王先謙;《駢文類纂》;刊刻;傳播
王先謙《駢文類纂》是清代晚期的一部集大成駢文選本,目前學術界對于《駢文類纂》的研究主要側重于選本體例、選文標準、駢文理論、駢散關系等方面。①縱觀王先謙仕途履歷以及王氏著述成果,其在刊刻出版方面的影響頗為深遠。王氏不僅是一位傳統的學者型官紳,而且是一位兼具湖湘情懷的出版人。
一、時空銜接:助推湖湘出版業
美國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指出:“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70年前的一段文字頗有說服力,他說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是一切心靈符號及其在空間上傳遞、在時間上保存的手段。”②國內學術界對于傳播定義多元,通行的如邵培仁《傳播學》認為“傳播是人類通過符號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發生相應變化的活動。”③駢文選本的傳播,其有效價值在于時空影響力。
王先謙于光緒二十七年刊刻《駢文類纂》,在刊刻《駢文類纂》之前,王氏歷任國史館協修、國史館纂修、實錄館協修、翰林院侍講、翰林院侍讀、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等職,曾主講思賢講舍、城南書院、岳麓書院。《清史稿·列傳·儒林三》(卷四百八十二)“王先謙傳”云:
先謙歷典云南、江西、浙江鄉試,搜羅人才,不遺馀力。既蒞江蘇,先奏設書局,仿阮元皇清經解例,刊刻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創於黃體芳,先謙廣籌經費,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誘掖獎勸,成就人材甚多。開缺還家,歷主思賢講舍,岳麓、城南兩書院,其培植人才,與前無異。……著有《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三家詩義集疏》二十八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鑒》三十卷,《虛受堂詩文集》三十六卷等。 [6]13304
《清史稿》對王先謙雖不無溢美之詞,但從史傳中也可以看出,王氏畢其一生的主要貢獻在于培養人才和整理文獻。刊刻出版成為王先謙傳播教育理念和學術思想的重要手段,書局和書院為王氏刊刻出版提供了傳播媒介和平臺。在刊刻《駢文類纂》之前,王先謙已先后完成《國朝試律詩鈔》(光緒六年)、《續古文辭類纂》(光緒八年)、《十家四六文鈔》(光緒十五年)、《六家詞鈔》(光緒十六年)、《律賦類纂》(光緒二十七年,與蘇輿合作)等文學選本的刊刻工作。《駢文類纂》的編選,既綜合了前人選本的刊刻經驗,同時也融入了王氏選本的刊刻特色。《駢文類纂》上起先秦,下迄晚清,構建了駢體文發生、發展、鼎盛、式微、復興的一個完整歷史時間譜系;對于清代駢體文的甄選,王氏亦去門戶之見,杜貴古賤今之通弊,且能兼顧空間平衡而不失區域本色。從傳播學視閾觀照,王先謙在《駢文類纂》編選刊刻的過程中就賦予選本以時空傳播潛能,從而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
王先謙刊刻活動以光緒十五年(1889)致仕開缺分前后兩個時期,前期重要的刊刻如《乾隆朝東華續錄》(光緒五年)、《皇清經解續編》(光緒十四年)。這兩部書都屬于續編性質,沿續前人編著軌范補充新內容。《皇清經解續編》是王先謙在江蘇學政任上的政績之舉,王先謙晚年對此頗為稱道。《王先謙自定年譜》云:
余奏刊經解后,到蘇州晤崧鎮青中丞駿,與商此事,慨然允蘇局助刊四百卷;仁和葉槐生主政維干,在上海主書院講,亦愿在滬助刊。余復設局長沙、江陰兩處,延親友分董其事。成書一千四百三十卷,廣丐同志,鳩集五萬余金,以二年余,獲成巨編。非友朋佽助之力,不克至此,誠后幸也。 [7]206
王先謙出版活動的區域以光緒十五年棄仕開缺分江浙和湖湘兩個中心。彈劾李蓮英、得罪西太后似乎是王先謙放棄仕途返回長沙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實際上其因果關系值得玩味,彈劾之事或乃王氏有意而為之,其真實目的正是為了退出仕途而轉型出版業。王先謙在刊刻工作中不僅找到著書立說的價值存在感,更重要的是通過《皇清經解續編》的續編建立起“延親友分董其事”的刊刻渠道。同時,王先謙在《皇清經解續編》的刊刻出版中看到湖湘地區與江浙一帶的文化差距,想通過熟悉的出版資源助推湖湘出版業,進而提升湖湘文化的傳播質量。《葉郋園事略》云:
長沙王葵園閣學一見盛稱之,言:吾在江蘇學政任內,成《全清經解續編》千余卷。感觸吾湘經學之陋,當編輯時,僅得船山諸書及魏默深之《書古微》、《詩古微》二種。猶未純粹,乃以曾文正公讀書日記,析其讀經筆記,雜湊一家。 [16]2207
這里表面上雖然是講湖湘經學的不足之處,實際上王先謙感嘆的是湖湘地區出版業的落后,很多學術著作因為沒有傳播條件而湮沒無聞,所以才對葉德輝這位志趣相投的合伙人“一見盛稱之”。因此,在開缺回長沙的當年五月,即輯刻《十家四六文鈔》,翌年又輯刻《六家詞鈔》,并有詩贈郭嵩燾,屢促其刊詩文集。當然,王先謙在長沙創設書局也得到了賦閑在湘的前輩郭嵩燾的鼎力支持。王先謙致繆荃孫的信札中亦云:“昨與郭筠仙(郭嵩燾)前輩創議開一小書局,每歲可刻千金書籍,既以表彰先哲,亦為敝省夙罕精善之本,有此一舉,庶士林得所嘉惠。” [11]31
《駢文類纂》的選輯刊刻正是在這種傳播經驗的積累以及日益成熟的出版條件下完成的,其目的就是要突破時空界限,達到“使異代之上,晤言若親;寰海而遙,光氣不隔”的傳播效果。從時間傳播來看,續纂一類的輯選工作已經初步完成,只有駢文還存在“題目太繁”“限斷未謹”的不足,尤其是李兆洛《駢體文鈔》對“所居之代,抑又闕如”,這既不利于總結駢文發展的普遍規律,也不利于駢文風氣的健康發展。從空間傳播來看,濃郁的鄉土情結讓王先謙把湖湘文脈的銜接工作作為自身的責任。此外。王先謙對湖湘駢文創作群體的推介也不遺余力。根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思賢書局1902年版的數據統計,《駢文類纂》中收入善化皮錫瑞存文99篇、長沙周壽昌存文14篇、湘潭王闿運存文10篇、平江蘇輿2篇、安化陶澍1篇、湘陰郭嵩燾1篇、善化孫鼎臣1篇、湘潭蔡枚功1篇。《駢文類纂》中清代駢文共存507篇,湖湘籍駢文家錄入129篇,占據了整個清代駢文的四分之一。從選文作者數及駢文篇目可以看出,王先謙對清代湖湘駢文是頗為推崇的,助推湖湘出版業對于傳播湖湘駢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文體關聯:擴大駢體影響力
《駢文通論》指出:“傳播學是隨著新聞事業日益發達而興起的一門科學,主要探討信息傳播的有關媒介、手段、時效、方式、效果等問題。在現代社會中,信息越來越成為一項重要的資源。它可以創造價值。而傳播卻不僅是新聞的事情。可以說,整個文化都與之有關。就現代社會來說,一種時裝款式的大流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傳播作用的結果,一種文風、詩風、畫風的影響力也離不開傳播的作用,甚至一個作家的知名度也離不開傳播的幫助。當然,一種文體的流播也是離不開傳播的作用的。” [3]46
王先謙在光緒八年編纂《續古文辭類纂》。《續古文辭類纂》是對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古文辭類纂》的賡續,但是,時人對《續古文辭類纂》褒貶不一。如王闿運謂:“《經解》縱未能抗行蕓臺,《類纂》差足以比肩惜抱。”譚獻批評:“閱《續類纂》畢,主張楚才,矜詡太甚。”尤其是光緒十五年黎庶昌編選了同名的《續古文辭類纂》,這對于王氏續本的傳播無疑是一種沖擊。
《駢文類纂》亦取式于姚鼐《古文辭類纂》。通過選本的方式來進行文體批評,起到駢散均衡的作用。駢體和散體都只是形式上的文體概念,實際上,《古文辭類纂》和《駢文類纂》在傳播途徑中產生的文體沖突主要是文類在駢散形式上的選擇矛盾,即論說、序跋、表奏、書啟、贈序、詔令、檄移、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哀吊、雜文、辭賦等十五類文體在駢文和散文兩大陣營中的歸屬問題。在實際操作當中,就是運用駢體還是運用散體來書寫和表達的問題。
姚鼐《古文辭類纂》的編纂已經從桐城派散文傳播上形成了一種先入為主的勢頭,造成散體在審美和應用領域對駢體的空間擠壓。王先謙在對姚氏選本的續纂過程中對部分文類以不續的方式提出批評,《續古文辭類纂》列略云:
辯論類元六十五,續四十一;序跋類元五十八,續一百四;奏議類元八十三,續無……書說類元八十五,續書六十四,說無;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詔令類元三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碑志類元一百,續八十;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類元六,續贊六,頌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哀祭類元三十八,續十七。 [13]276
《續古文辭類纂》中奏議、說、詔令、頌、辭賦類無后續,王先謙分別將其從散文挪移到駢文陣營當中,形成《駢文類纂》中的論說、表奏、詔令、贊頌、辭賦五類。此外,王氏還為駢文增加了移檄類。黎庶昌未能整體領會王氏的這種文本關聯,認為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存在個人偏好。
曩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纂《續古文辭類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甚異。王選只及方、劉以后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纂加約,本朝文才二百四十余首,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敘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嗜好之殊,蓋難強同。要之,于姚氏無異趨也,后之君子并覽觀焉。 [14]1
王先謙《駢文類纂》序目云:“見夫姚氏《古文類纂》兼收詞賦,梅氏《古文詞略》旁錄詩歌,以為用意則深,論法為舛。”王氏指出《古文辭類纂》在編纂體例上的謬誤,所以續纂沒有步武,黎庶昌覺得這只是個人嗜好上的差異,沒有從學術的角度進行嚴格區分。王氏嚴格的駢散界限觀念也只有在《駢文類纂》出版問世之后才清晰明了。實際上,王先謙在編纂《駢文類纂》的過程當中對此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其在給繆荃孫的信札中就多次提及。
謙近刻《日本源流考》、《駢文類纂》二書,《類纂》一用姬傳先生《古文辭》例,微有變通,采摭頗廣,本前八年所創稿,今更定卒成之。[11]33
此番《類纂》之輯,自屈、宋迄國朝,體制似較姚輯為宏闊。辭賦選入散文,本覺此中界畫未為允葉也。[11]34
從出版傳播的角度看,《古文辭類纂》《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實質上可以形成一個選本系列,三者互為關聯。《續古文辭類纂》處于中間的過渡環節,借助姚鼐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文壇地位,附驥尾而行千里。王先謙將傳播焦點轉移到《續古文辭類纂》之上,再經過嚴格的類別區分,從而水到渠成地推出《駢文類纂》。王先謙在給繆荃孫的信札中自言,《駢文類纂》八年前就有創稿,并且對后來的調整變通頗為得意,認為“體制似較姚輯為宏闊”。這里以論說類為例,重點分析《駢文類纂》對姚氏類纂的“微有變通”。
《駢文類纂》論說類是對《古文辭類纂》辯論類和書說類中說的整合,分文論、史論、雜論。從選文規模上看,《駢文類纂》要宏大得多,尤其是將劉勰《文心雕龍》五十篇全部錄入,劉知幾《史通》節選十六篇,頗有獨到之處;《古文辭類纂》自賈誼《過秦論》、司馬遷《太史公談論六家旨要》以下多選韓、柳、歐、蘇等唐宋八大家之文。從選文內容上來看,《駢文類纂》偏重文史,“論”的成分較多;《古文辭類纂》偏重諸子,“辯”的成分較多。這表明,王先謙默認“辯”為散體文之專屬。關于“說”,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不續,卻在《駢文類纂》中又與“論”并列,但真正以“說”命名的僅樂鈞《廣儉不至說》一篇;而《古文辭類纂》中的“說”實際上是指“游說體”,王先謙在這里轉換概念。
王先謙在“論說類”中的微有變通是將戰國縱橫家的論辯、游說之詞全部排除在駢體文外。當然,王氏這種文體關聯法是有風險的,一方面,《駢文類纂》確實達到了和姚鼐《古文辭類纂》以及王氏自選的《續古文辭類纂》參照對讀的效果;另一方面,四庫館臣在《〈四六法海〉提要》中云“秦漢以來,自李斯《諫逐客書》始點綴華詞,自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始疊陳故事,是駢體之漸萌也。”而《駢文類纂》割裂了駢體文與戰國縱橫家文之間的聯系,對李兆洛《駢體文鈔》所選的李斯之文一概不錄,把譚獻稱之為“是駢體初祖”①的《李斯上秦王書》排除在外,這或是王氏選本的瑕疵。
三、選文存人:揄揚清代駢文家
王先謙具有鮮明的駢文史學觀。由于清代駢文是作為其駢文史的一部分來進行建構的,因此他非常注重保存當代駢文作家及其作品。《駢文類纂》共收錄文章2122篇,其中清代存507篇,約占全書規模的24%。從入選作者規模來看,選本共選作者294人,其中清代65人,約占整體規模的22%。從王先謙所選清代駢文歸類來看,大體分布于雜文(135篇)、序跋(104篇)、書啟(52篇)、雜記(49篇)、碑志(39篇)、頌贊30篇、哀吊(21篇)、贈序(17篇)、辭賦(11篇)等九大類。在如此龐大的選文規模當中,忌平庸和忌繁瑣同樣是選本的亮點,王先謙在注重作品的經典化和推陳出新的同時,也適度傾注了時代群體的特殊情感。
雜文類主要是以洪亮吉(32首)、皮錫瑞(87首)為主的連珠。雜文類選文數量多有兩個原因:一是其篇幅小,所占版面少,易于掌控;二是連珠作為學習駢文的練筆,是重要的寫作素材,具有一定的市場需求。《駢文通論》指出:“‘連珠是作為習駢文者的練筆而用的,這從它以 ‘臣聞開頭的格式就可以看出,它是為寫奏疏之類文章而練習的。‘連珠只是一種泛義的微型駢體。”①皮錫瑞系晚清湘籍著名經學大師,王先謙對皮錫瑞廣為揄揚亦有感于湖湘經學之陋。《駢文類纂》選皮錫瑞駢文99篇,其中《演連珠四十九首》《左氏連珠三十八首》就占了87篇,充分表明王先謙對皮錫瑞駢文的重視。此外,《尚書大傳疏證自序》《史記引尚書考自序》系皮錫瑞經學著作自序,王先謙亦將其錄入選本,在傳播皮氏駢文的同時,亦為其經學著作廣而告之。
這種傳播案例在《駢文類纂》“序跋類”中比比皆是,最明顯的當屬郭嵩燾《十家四六文鈔序》。郭氏《十家四六文鈔序》是為王先謙刊刻出版的《十家四六文鈔》所作之序。《十家四六文鈔》是王先謙在刊刻《駢文類纂》之前編纂的另一部駢文選本,所選“十家”分指劉開、董基誠、董祐誠、方履篯、梅曾亮、傅桐、周壽昌、王闿運、趙銘、李慈銘,共選駢文139篇,這實際上就是十人駢文集之束集。在《駢文類纂》中,上述“十家”全部在選,合計篇目亦為139篇。可以看出,王先謙為了盡可能穩妥地保存清代駢文,不惜對自己過去的選本進行重復。當然,《駢文類纂》已經覆蓋了《十家四六文鈔》,起到后出轉精的效果,但這并不妨礙兩個選本同時傳播的功能,尤其是多個選本互相參證,更加有利于駢文作品的經典性重構。
在《駢文類纂》序目中,王先謙自云:“商量邃密,葉張之力為多。”葉、張分指葉德輝和張祖同,兩人均協助王先謙刊刻《駢文類纂》。實際上,近代藏書家繆荃孫對《駢文類纂》的刊刻亦有所幫助,這從王先謙寄給繆荃孫的信札可以看出。《藝風堂友朋書札》(王先謙·四十九):
謙近刻《日本源流考》、《駢文類纂》二書……吾弟(繆荃孫)駢文,務寄數篇或十數篇惠我,書成必速,切盼來函。又蓉生(朱一新)沒后,其遺著伊令弟苗生寄我,謙去秋擬鄉居,藏書全檢入箱,蓉生遺編他處難覓,亦乞選寄數篇。爽秋(袁昶)、竹筼(許景澄)之文,能否代致。又弟所知先輩朋儕中,但有佳文實在可傳者,并望費心鈔寄,中駟則置之。……惟駢文稿請先來,不可耽誤也。 [11]33
又《藝風堂友朋書札》(王先謙·五十):
承賜寄各稿領到,大著駢文敬登十一篇、朱蓉生二篇,柚岑一篇,此番《類纂》之輯……袁(昶)、許(景澄)二公遭此不幸,中心為慘怛者累日,亦各登一篇,聊盡后死之誼,其身后遺文諒有為之搜輯者,先謙存所及見而已。書約來春可成,再行寄上,元稿先繳察收。 [11]34
王氏前后兩份書札可以相互印證:繆荃孫在《駢文類纂》編纂中至少提供了朱一新、繆祐孫、袁昶、許景澄以及他自己的一些駢文稿件。這在《駢文類纂》中亦可以核實,繆荃孫(24篇)、朱一新(2篇)、繆祐孫(1篇)、袁昶(1篇)、許景澄(1篇)。這兩份書札還可以看出,王先謙深諳以選存篇、以篇存人的傳播價值。1900年7月,袁昶、許景澄因反對朝廷攻打外國使館而被以“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等罪名被殺,與之后被殺的立山、聯元等史稱“庚子五大臣”。《駢文類纂》保存袁昶《王母鮑太夫人誄》、許景澄《高夫人哀辭》,一方面寄托對死者的哀思,更重要的是以哀寫哀,倍增其哀。繆荃孫與王先謙之間達到了一種高度的選家默契,繆氏提供給王氏的朱一新《王母鮑太夫人誄》、繆祐孫《從嫂莊宜人誄》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鮑太夫人是王先謙的母親,莊宜人是繆荃孫的側室,這種特殊的關系使得選本具有睹文思人的特殊情感,而朱一新與繆祐孫的英年早逝又加重了這一層悲情色彩。
選本的個性化對于群體傳播也有一定的幫助,《駢文類纂》不僅打上了王氏風格的深刻烙印,同時也兼具了王氏交游圈的社會烙印,堪稱一個時代文人性格命運的留影集,這里以周壽昌和王闿運為例。《駢文類纂》選周壽昌駢文十四篇,王闿運駢文十篇。周壽昌是王先謙的恩師兼同鄉,王氏對于老師的文獻整理工作是傾盡全力的。光緒十四年,王先謙刻周壽昌詩、文、詞、日札十九卷,總為《思益堂集》;光緒十五年,輯刻《十家四六文鈔》,收周壽昌《恩益堂駢文》、王闿運《湘綺樓駢文》;光緒十六年,輯刻《六家詞鈔》,選輯周壽昌《思益堂詞鈔》二十七首,王闿運《湘綺樓詞鈔》十六首。王先謙在開缺致仕后勤于周壽昌遺著刊刻,一方面有感于人生仕途隱晦,未若做學問來得純粹;另一方面深感文運之厄,唯恐師道湮沒無聞。《思益堂集》序云:
余以嘆先生不早自知其無與于功名,不得壹意于學問之途以大昌其箸述為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強,爵位益高,當國家承平,既未必別有表見,而此十年心力,亦消磨于仕宦,不暇專致之學問。其孰為得失,識者宜有以辯之。……四十以前,積稿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卅余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既刊之十家四六中矣。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乎! [10]112
周壽昌的仕宦遭遇也是王先謙決心轉型出版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功名仕宦與著書立說之間做一權衡,發現立言比立功更加符合儒家士人的心性。相較于周壽昌,王闿運的仕途命運更加坎坷。王闿運胸懷帝王之學,早年依附于肅順,肅順倒臺之后游走于曾國藩門下,雖滿腹經世之學,卻一直懷才不遇。《駢文類纂》把王闿運辭賦《吊舊賦》《嘲哈密瓜賦》作為全書壓軸,很難說不是精心設計的。而且在清代駢文比較集中的序跋類、書啟類,王闿運的《秋醒詞序》《上張侍講啟》都分別作為同類中的壓軸之作。這樣的處理方式,在傳播過程中更加容易讓人留下深刻記憶,同時也把王闿運塑造成為清代駢文的一個終結者形象。
結語
《駢文類纂》刊刻于王先謙由功名仕途向著書立說轉型的思想成熟期,經過一系列刊刻傳播經驗的積累,對駢文的整理和總結工作具有集大成意義。從時空維度上看,王氏在助推湖湘出版業的同時,建構起一個完整的駢文框架體系,既延續了駢文發展的歷史脈絡,又兼顧地域空間的建構布局。從駢散文體歸類來看,王先謙通過各選本之間的關聯互動,既參照了前人文體分類的優秀成果,也表達了自己的文體歸類主張,使駢文和散文體式均衡健康發展。從選本的群體共性觀照,王氏身處于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歷史節點,在謀篇布局上不僅賦予選本以鮮明的時代和個性特征,也傾注了群體的特殊情感和閱歷,使其在傳播過程中能為人窺見一代人命運和風貌。
【 參 考 文 獻 】
[1] 〔美〕威爾伯·施拉姆.傳播學概論(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 邵培仁.傳播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莫道才.駢文通論(修訂本).濟南:齊魯書社,2015.
[4] 呂雙偉.清代駢文理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 孟偉.清人編選的文章選本與文學批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6]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7] 王云五,主編.清王葵園先生先謙自定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8] 李和山.王先謙學術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9] 李兆洛,選輯.駢體文鈔.上海:上海書店,1988.
[10]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五.北京:朝華出版社,2018.
[11]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 王先謙.駢文類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3] 姚鼐,纂.王先謙,續.正續古文辭類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4]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上海:上海世界書局,1936.
[15] 王維江,李騖哲,黃田,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王先謙 葉德輝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16] 汪兆鏞.碑傳集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編校:馬延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