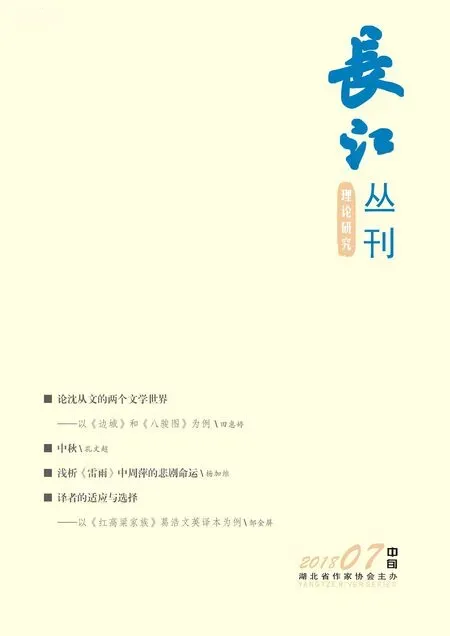做這個時代的“寄物居”
■/
《文藝報》總編室
王蕓的小說創作,秉持著現實主義的創作姿態,扎實而沉穩,同時在藝術上獨具匠心,非常靈動、圓潤、細膩。具體說,我認為她的小說創作有三個特點:
首先,王蕓的小說創作反復述說的一個主題,即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堅守。在王蕓的小說里可以看到,對于逝去的事物,對于回不去的故鄉,她常常充滿深深的惆悵和眷戀。比如小說《鑄劍》,表現出對即將失傳的古老鑄劍工藝的憂慮;《噓村古樹》寫但老漢對一棵古樹的守護;《龍頭龍尾》寫一個村子的人在春節時回歸老村,重新按照古老的習俗舞起“板凳龍”;《對花》更是體現了幾代戲曲人對于戲曲藝術的熱愛和堅守。在她的作品中充滿這樣傳統文化的內容和符號,比如戲曲藝術,比如古老的儺戲,比如鄉村的一些古老習俗:架花,板凳龍,跳和合,等等,這些符號成為她小說的一個重要意象,也成為她結構自己小說的起點和支點。這些符號是當下和歷史的一種連接,通過這些符號,王蕓試圖表達出一種頗為復雜的時代況味,呈現出新時代和舊時光之間的對抗,以及人們在這種新舊交替之間的情感上的惆悵和糾結。通過這些符號,王蕓表達出她對當下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思考。
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精神世界、倫理價值,都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王蕓的小說就恰恰聚焦在這種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和矛盾上。面對這些沖突,王蕓并不是簡單地給出答案,而是傳達出一種豐富復雜的情緒,這其中既有堅守和回望,也有傳承和發展。
小說《寄》里面的“寄物居”是一個很好的意象。所謂“寄物居”,就是人們把平時沒用但又舍不得扔掉的舊物寄存的一個地方。我們在生活中常有這樣的體驗,很多舊物已經用不上了,但又舍不得扔,因為它們寄存了我們的生命經歷,寄存了我們的感情。文學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寄物居”。王蕓的小說創作就起著“寄物居”的作用,把行將消失的傳統和情感,放在小說中寄存起來。
其次,王蕓的小說充滿對邊緣人,或者說對失意者、失敗者群體的觀照和關懷。她的很多小說里都有失敗者的形象,比如《控》表現了住在一棟樓里有不同故事的社會邊緣人;比如《羽毛》寫了一群受過生活重創的女人;《尋找馬耳他狗》寫一個初到城市的小保姆的辛酸;《寄》中的“寄物居”干脆就是專門收留那些流浪漢的。這些人應該是這個社會最邊緣、最失落、最失敗的一群人,王蕓都會以女性那種獨有的悲憫和體恤,去觀照他們的靈魂,將他們寫到自己的小說中來。這種關懷不是那種居高臨下的憐憫,而是一種理解和共情。從作品里能夠看出,作家深愛她筆下的每個人物,不論他們具有怎樣的身份、怎樣的故事,甚至像《與孔雀說話》中,對于一個出獄的貪官,王蕓同樣報以深沉的關懷的目光,這并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夠看到、做到并且在作品中呈現出來的。
所以,無論是回望的姿態,還是對失敗者的觀照,實際上體現的都是文學的悲憫精神和人文關懷,就是用文學的慢去對抗社會變化的快,用文學的人文關懷去對抗社會的叢林法則,在成功和失敗這樣的二元價值之外,重新開辟出一種價值維度,來收留和容納那些失敗的人。這也是王蕓的文學創作在當下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的意義。
第三個特點是王蕓對女性深入的描摹和書寫。這主要體現在《羽毛》和長篇小說《對花》上。
《羽毛》是一篇構思非常巧妙的小說,表現的是幾個女人的群像,她們都有不同的創傷,聚在一起彼此取暖。小說中寫到一個類似雜技的技藝,支點一邊是十幾根樹枝,另一邊是一根很輕的羽毛,維持平衡的就是這一根羽毛的重量,要想維持平衡,需要高超的平衡技藝。關一芹苦練這種技藝,只是為了讓有智障的兒子開心。對于其他人輕而易舉的事情,對關一芹這樣遭受生活挫折的人來說,羽毛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重量。宋羽是這群女人的組織者,支撐宋羽活下去的是他失蹤男朋友的消息,而她男朋友的身上也紋著一根羽毛。一根羽毛可以支撐人活下去,一根羽毛也足以把人壓垮。
羽毛是一個非常美的意象,實際上也是關于女性的一個意象,她們可以很輕,但她們同時又具有舉足輕重的重量,占據支點的一端,維持著一種平衡。這個意象充滿辯證的味道,寫出了生活的輕與重,也寫出了女性的輕與重。這個羽毛也可以解讀為,面對人生的遭際和變故,要尋求一種內心的平衡,它的難度不亞于這個羽毛的雜技,需要的是女性雖然細膩但卻堅韌的內心。
《對花》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長篇小說,時間跨度大,人物眾多,結構設置精巧,通過兩條人物線,表現了三代女性對戲曲藝術的堅守和傳承。這部小說的主題是表現戲曲藝術,但我覺得同時還有一個主題,就是女性,因為它呈現了一個女性的群體:蘇媛芬和她的女兒欒之鳳,陳小娣和她的女兒陳子湄,以及筱團長、楊菊花等等,這些女性具有多重身份,有母親和女兒,有戀人和妻子,有師徒和朋友,也有競爭對手,等等。通過這些女性,小說不止是寫單一維度的女性,而是把女性的不同側面詮釋得很充分。
《對花》在藝術上還有值得打磨的地方。相對于王蕓的中篇小說《大戲》,《對花》給人一種匆忙的感覺,它的敘事速度太快啦!這部小說20多萬字,但是內容容量卻很大,導致了小說的敘事速度非常快,而且越到后面越快。速度快的好處是可以快速地勾勒出時代的變遷和人物命運的浮沉,但是這種粗線條的快速的勾勒,所帶來的可能是人物面目的模糊,讓人覺得很多人物和場景沒有寫透,匆匆一筆帶過。
對于長篇小說來說,格局和容量可以很大,但還是要落實到具體而微的細節上,所以在確定了小說的主線之后,在選材上應該有所取舍,挑選一些典型性的片段和瞬間寫透了,歷史的厚重感自然就會出來,而并不需要像大事年表一樣事無巨細地都表達。要能快得起來,也要能慢得下來。既要能鋪陳開,又要懂得留白,而不是像撒胡椒面似的平均用力。
《對花》在主題的挖掘上還可以更加深入。不僅要寫出戲劇對于個人的外部命運的改變,同時也要寫出人面對戲曲藝術,所產生的人性深處的異化,這種異化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東西,都可以寫。
總之,王蕓是一個成熟的、有實力、有潛力的作家,期待看到她更優秀、更厚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