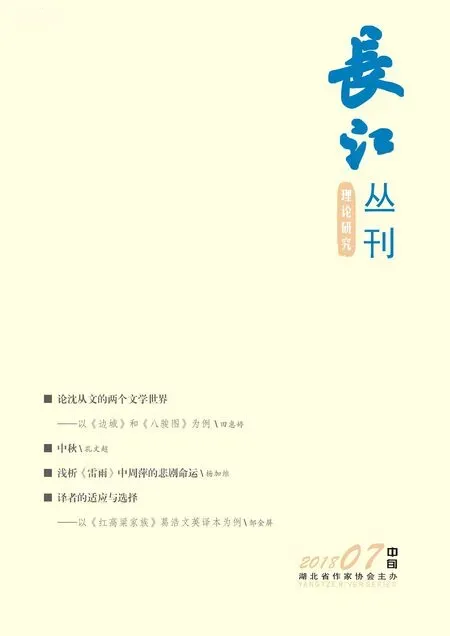鄉野的呼喊
——劍男詩歌淺議
■ /
湖北大學文學院
自《詩經》以來我國悠久的詩歌傳統中,專注于描寫人在大自然中的日常生活,如田園里的勞動場面,戀愛及求愛,亦或是宴會場景,將人類視為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和煦的氛圍。基于悠久的農業文明,我國古典詩歌傳統中,人與自然的關系親密和諧。崇尚自然,向往自然之美,表現田園情趣成為詩人的藝術追求。
這一文學傳統在五四新文學革命之時斷裂。中國社會的內憂外患、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強烈震撼,迫使風雨飄搖的中國開始全面審視和反省自己的現實處境。“苦難是中國詩歌革命的真正出發點” ,與此同時,詩歌也走出了文人吟弄風月的范疇,走向如何接近并改變現實的、底層的、個人之外的苦難社會的思考。
歷經百年中國終于擺脫了積弱和貧窮之后,人們猛然發現現代化進程的推動是以環境的破壞、資源的犧牲、文化的失落為代價的,人與自然的對峙更是導致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千瘡百孔。二十世紀末,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生態危機日益深化的語境中,掀起了一股生態寫作的浪潮。詩人紛紛思索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以己之筆寫下對生態破壞的反思,對人與自然和諧的憧憬。
湖北詩人劍男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詩歌寫作,以家鄉幕阜山為文學地域,對自然的書寫貫穿其創作始終。面對生態惡化的現實背景及工業文明對鄉土世界的沖擊,他的詩歌有著從鄉土詩向生態詩轉向的軌跡。
自然的還魅
在現代化進程中,鄉土世界屢屢遭受著工業文明的入侵,城市憑借其強勢姿態完成了對人類精神世界的謀殺及豐富感知能力的擠壓消解。現代文明造成了人類感知能力的破壞和精神生活的無處安頓。詩人劍男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并將寫作視點轉向人類的“內宇宙”,從感知生態的角度完成對鄉野的復魅。
“感覺生態文學”流派,是現代美國環境主義思潮中異常活躍的一個領域,這一西方話語目前在國內較少被提及。1987年,桑德斯曾在其隨筆《為自然說一句話》中指出“感覺生態”思維方式的重要性,“在我們生活中大多數時候,自然像被鑲上了窗框,就像錄像的屏幕、照片的白邊一樣是以鑲著邊框的狀態顯現的。另一方面,自然的有機的網眼已經深入到我們的內部,而我們卻幾乎感覺不到”。可以說,“感覺生態文學”是對當代文學生態寫作中輕視乃至忽視人類與自然之間感覺體驗的傾向的扭轉,它關注各種生命體之間的有機聯系,有著體驗性和情緒性的意味。讓讀者感受到“自然的有機的網眼已經深入到我們的內部”,喚醒人類的感知體驗,是感覺生態寫作的意義所在。
成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人劍男,其伴隨著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成長軌跡以及流轉于城市與鄉村的雙重身份,使他可以敏銳地感受到鄉野對人的感覺體驗的喚醒和都市對人類感知能力的破壞。這一鮮明的反差體驗成為他感知自然魅力的契機。
在其生命出生之地——幕阜山中,詩人的感知力被原初的自然所喚醒。他在《疼》一詩中寫道,“很多個春天過去了/但一到春天我的胸口就生疼/我希望我是喜歡春天的/像一粒種子迎接秘密的雨水/但我一見到風就想起凋零的花瓣/一憶起往事就想到到處沾惹的柳絮”。作者筆下,花開花謝調動著人類的情緒,人會因為凋落的花瓣而產生疼痛的感覺。大自然喚醒了人類身體的敏銳感知,在鄉野之中,人類會本能地將自我與動植物的生長、氣候的改變、季節的變遷聯系起來,并以它們為參照,關照自我的生命狀況。鄉野中和諧美好的生態世界及大自然的原始自由野性,是涵養人類審美感知體驗的沃土。
鄉野喚醒人類豐富的情感體驗,是劍男詩歌的重要特征。《遠行或者從頭開始》中呈現了母親和孩子勞動的場面,“到了秋天/收獲從內心的歡愉開始/母親在風中揮起了鐮刀/田埂上奔跑著挾著破舊識字課本的孩子/從一種遠行到另一種遠行/艱辛的勞動和盲目的奔跑要采擷生活中的甜蜜”;《春天的蜜蜂》里則刻畫了蜜蜂采花的畫面,“可能是第一次看見這么碩大的花朵/它們嗡嗡地叫/像找到心中隱秘的歡樂”。無論是人還是其他生命,勞動是生命體與自然最親密的接觸方式,其間獲取的是最直接的體驗和最本質的快樂。生命體通過勞動享受土地的贈與,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的是與自然血脈相連的感情體驗。
而在城市,人與自然的直接接觸體驗在現代化技術的入侵下遭受到了毀滅性打擊。收割機、刈草機等現代機械代替“鐮刀”,將人類從土地驅逐;游戲等各類間接性體驗的娛樂以及電視等置換現實世界的虛擬世界凌駕于真實的自然之上,切斷了人和自然的血脈相連。生活在城市中的現代人,其晝夜被電燈操縱、溫度被空調調控,以致人對自然的直接體驗被人為的虛假及舒適破壞。在城市中,人們的感覺被統一化、整齊化,來自自然和土地的真實感受被扼殺。現代意義的都市是一個特意制造非自然生活方式和環境的場所,科技和理性切斷了人與自然的直接聯系和體驗,完成了對大自然的徹底祛魅。
技術完成了人與自然的分離,城市的高樓大廈更是進一步將人和自然完全隔絕。“慵懶的城市里/人們開始喪失很多概念/森林、河流、大山/他反復詰問/什么是青磚綠瓦/什么是翱翔和嚎嗥……博物館太大/或者是太狹小/他在玻璃切割的陽光中反復踱步/消失得太快/這曾經是什么地方/他想/這可能是一座池塘/或者一片草地”(《在博物館》)。建筑的作用是隔離性的,人類的建筑,哪怕僅從一堵墻開始,就拉開了人與生態脫離的歷程,而城市規劃中形成的單調統一的建筑風格更是日益窒息著人類對自然豐富的感知體驗。
在城市,把空地鋪設成公路,森林改建成公園,河流圍上柵欄,這就意味著人類沒有機會接觸到原初的自然。不接觸造成了感知體驗的缺乏,接觸性和體驗性感覺的喪失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自然的多樣性從人類的視野中慢慢消失,始終處在單一性的景觀中,人就會陷入經驗滅絕之危險境遇。自然和人類的聯系不再密切,自然的變化于人類而言也不再重要。人對自然“集團性的無知就變成集團性的不關心” ,冷漠、自私、封閉、虛無等人性精神異化問題隨之而來。人的感受萎縮、雷同,生命感窄化,敏銳的情感體驗不復存在,城市變成人類失去人性和感知體驗、價值判斷的荒野。正如著名的生態倫理學家羅爾斯頓所言,“未來的史學家會發現,20世紀的一個奇特之處是人類知識廣博而價值判斷卻很狹隘,人類對于世界從來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知道得這么多而又評價得這么少,無怪乎我們會面臨一場生態危機” 。
人對自然的敏銳感知是形成深刻審美體驗的基礎,只有具備了這種感知能力,才能從停留在表面的對自然景觀的觀賞進入到從內在精神的層面與自然進行深度交融滲透的境界。劍男從感知體驗的角度對自然復魅,力圖掙脫以自然是否能為我所用、其形式是否愉悅了人類身心為標準來判斷自然價值的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將關注點放在自然的本身存在及人與自然的深層交互,達成一種“自然全美”的生態感知體驗,這使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特殊生命的治愈體驗
劍男非常關注某些特殊群體在鄉野中獲得的生命體驗,其詩歌中常常出現盲人、肢體殘缺者、正在經歷身體疼痛乃至承受精神痛楚的人物形象。當此類“有缺陷”的生命體放置于自然之中時,其身上存在的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諸多不和諧因素在鄉野的接納和包容中得到緩解。
《兩只鞋子》中寫道,“幾只鷺鷥練習單立/一個人正在湖中挖藕/鷺鷥的腿直而修長/挖藕的人雙腿埋在淤泥中/當他在淺淺的湖水中移動/我看見他用手從藕筐旁邊/摸出一只拐,像一個/熟練的水手駕駛一艘快要/擱淺的木船,輕輕一點/就把自己緩緩的送到前面的淤泥中”。通過單腿鷺鷥和缺了一條腿的挖藕男子兩個畫面的交替呈現、切換,在自然對人的無限包容中表現出殘缺之體在大自然中獲得的和諧感。
這種和諧感在《一把鐮刀》中體現為萬物對人的順應及人與物情感的滲透,“仍然被掛在墻上/仍然傾向一邊/仍然保留一個左撇子的手勢/從老屋向外望,是它曾經收割過的/如今長滿荒草的田野和河灘……一把鐮刀一定不會只是工具/一把鐮刀也會日久生情/你看它的主人,掛在墻的對面/他們的眼神似乎從沒有離開過彼此”。在作者筆下,一把鐮刀仿佛被賦予了生命,順應著人類的生活習性,并在長久的相處中兩者達成生命的交融。
劍男詩歌中不乏有感官缺陷的生命對自然之美的憧憬。“春天的下午這般迷人/一個憂郁的少女/在干涸的眼瞼盛下了清純的淚水/但一只夜鶯與她不同/它胸中埋著激情/它從一個枝椏到一片草地/它的跳躍暴露了少女的言辭/它運送時光到春天/一個充溢著血液的下午/風鈴和琴音處處的盲人學校/他們不看/但聽見”,亦或是“啞巴愛人世愛得多么苦……那么多嘰嘰喳喳的鳥兒/卻沒有一只喜鵲替他喊出心中的歡喜”。與感官缺陷相補償,這部分人的感知體驗極為敏銳,這恰好為其內在生命與自然的接通打開了通道。他們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看自然,而是靈與肉都深深地參與并嵌入到自然之中,與自然發生真實的生命交融。他們能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的生命,在其他的生命中感悟自己的生命,在與自然萬物深層的交互中滿懷對自然美的觸動、渴望。
自然具有一種無疆的美感,即便生命體看不見、道不出也不能阻止這種美感的傳達。殘缺的感官不僅無礙生命對美感的接收,反而更增添了其對自然之美向往的熱情。也只有寄身于大自然之中,才能使有缺陷的身體獲得和諧感。
相比身體的殘缺,更加困擾現代人的是靈魂的無處安放。精神苦難在劍男的詩歌中突出表現為“孤獨”,這是典型的現代都市病,也是其詩歌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無論是不悔之年“一個人的靈魂在風中疾馳”,而立之時獨自“乘明月醉臥他鄉”,還是在不惑的年紀里“敲遍一條長街,問張懷民的下落”。縱使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甚相同的內涵,但孤獨的情緒是劍男詩歌中不曾改變的主題。
“一個獨身女子穿過寂寞的街道,在一座/石雕旁吐出了隔夜的思想、食物和胃”,城市的孤獨者散發著消沉、腐朽和死亡氣息,給人一種無可救贖的窒息感。
將處所置換到鄉野,劍男在《夜宿大別山》中寫道,“一些事物在黑暗中沉睡過去/一些事物像我一樣在夜半醒著/人生所寄又能怎樣/千里大別山也不過有著人世一樣的孤獨”。自然使人豁達、通透,能讓人擁抱赤子之心、接觸到生命本質。在鄉野中人能與自然交融,更能在與自然的交融中明白孤獨是世間萬物的普遍屬性和本質特征,從而不再局限于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孤獨。“生命不過是寄居,秋色寄居枝頭/鳥雀寄居于浮云,人寄居于大地/萬物寄居于彼此/如風吹過風”,只有在與自然的對話中,人才能變得清醒而自知。這個時候,身體和精神的每一個感官、每一個毛孔都會打開,去敏銳地感知世界、體悟生命,與自然產生一種內在精神的契合。對于無處安放靈魂的生命主體,鄉野帶來的新鮮經驗,可以實現精神生活的短暫棲息和回歸,在人與土地內在生命的契合中完成對精神苦難的療救。
自然意象感知盛宴
劍男詩歌中的意象紛繁豐富,注重從視覺上建構美感,用大筆墨鋪陳的繪畫手法將眾多意象一一呈現,使之具有直覺感和可見性。例如,《共和國的菜園》中,“省略掉對泥土的吮吸和對陽光的搶奪/我喜歡這個小小的共和國,沒有/約束,也不需要節制和道德感/就像絲瓜藤昨夜還在和空心菜糾纏/早上又爬到墻頭和一群蜜蜂打情罵俏/藿香放肆地噴灑香水,番茄偷偷/在葉簇下珠胎暗結,我喜歡它們的/散漫、自由、該開花時開花,該/結果時結果,每一株都能活出自己的樣子”。劍男從日常生活中采擷意象,刻畫出一幅幅生態意象圖。加上一系列動詞的修飾,賦予意象以角色感和生命力,從而將單純的視覺感官引申到多感官的交融互通,形成立體的美感效果。
劍男對自然之真充滿執著,他諦聽自然的聲音,緊貼自然的生命節律,原汁原味地呈現自然的本真狀態,詩歌創作常常擯棄自然物被賦予的文化含義。例如《曇花的方式》一詩,“這生命中的練習曲/曇花要開放在時間的峰尖上/一現就暗合了一生的宿命/它緩慢的恢復是那樣的漫長/不能遏止/不能在春天中看到一人最后的歌唱/僅僅是一種方式/毀滅了自身的禮儀/死亡成就了一生不能寬恕的完美”。
由曇花開合到人的一生,劍男力圖通過對意象的去象征化來建構人與自然物的聯想關系,賦予意象以鮮活感。曇花是沉默著的生命體,人類之外的其他生命都是沉默無聲的,因此長久以來它們都被形形色色的語言和各種符號涂抹覆蓋,承受著文化對鮮活生命的視而不見。“人類走向文明的過程,就是自然逐漸喪失話語權利的過程”,而在這里,詩人洗滌去了歷史和文化長久以來賦予給“曇花”這一物象的種種象征旨意,撥開人類主觀意志對其作為鮮活生命體的遮蔽覆蓋,讓曇花回歸到生命本身,作為生命體為自己的命運發聲、訴說,從而實現生命的自我指認,重新綻放生命的質感和光澤。對生命祛蔽顯真,讓自然中的鮮活生命突破層層遮蓋,最終回到其生存現場和生命本身之后,形而下的實體自然物象才能因自身的生命律動與人類的心靈實現共通,未經干擾和踐踏的鄉野為實現這種異質同構的生命契合提供了可能。
將去象征的意象重新變為隱喻,是劍男給予自然物生命的又一種方式。蜜蜂與“單身漢”,丹頂鶴與“少女、繆斯”,鄉親們、溜冰的女孩和“一列列螞蟻”,“一朵跳動的火焰或一只蝴蝶”……動植物自然意象的擬人化和人的擬物化使劍男詩歌中的鄉野世界極富感知力和生命力。尤其是將植物意象形容詞化,如用“山茶的嬌羞”形容鄰村的少女,“楊花的輕佻和孟浪”形容妖嬈的女郎,更是讓其筆下的意象具有了或褒或貶的感情色彩。
句式的選擇使劍男對自然意象的書寫帶有鮮明的主觀化、情緒化特征。詩中頻頻發出“我藐視集體出現的東西/包括暴雨前歸巢的鳥/不夾帶一絲雜色的紫云英/成片的二月蘭,十里飄香的桃林/我藐視把春天集中在一處/把蘭草從山中挖出來/把映山紅移到路人可見的山坡”、“沒有必要動土……沒有必要焚燒荒草/沒有必要剪枝/沒有必要移栽幼苗”這樣的吶喊。可以看出,劍男將鄉野中的自然萬物視為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意象和鮮活的生命體,對它們的情感顯現出惺惺相惜的呵護和尊重。
伴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自然本來的樣子已不能再滿足人類的審美需要。審美消費主義下,自然是“等待被考察的面孔,而不是棲居的家園”。形式主義審美觀念的誘導下,人類忽視了自然擁有按照自身生態規律生存的權利,不顧自然的原始生命存在、不再認為自己是和自然聯系在一起的平等的生命體,而是根據自己的審美需求、價值需求隨意修剪和改造自然,使其服膺于人類的視覺暴政。劍男對此持堅定的拒絕和批判,他對原生態自然美和自然本真天性發出熱情的呼喚。大串排比句的使用將詩人內心的情緒烘托得淋漓盡致,讓其詩歌書寫言簡意賅、表義明確、表情用力。
詩人筆下的鄉野不再是現代化和工業文明沖擊下真實存在的鄉村,而是類似于古代山水田園詩派筆下的傳統意義上的、延續著和大地血脈之源的淳厚而質樸的鄉土世界。他對未經人為干涉的荒野之地、對鄉野中的自為生命體及原生態的自在生活姿態、甚至對鄉村封閉、貧窮卻又無拘的生活方式充滿了眷戀,帶著審美回望和推崇滿懷渴望地加以美化,使之成為被距離化、審美化、理想化的顯現出超越姿態和浪漫氣質的靈性世界。可以看出,詩人是把鄉野作為一種價值理想來建構的,旨在借助對鄉土世界的美化來表現對殘酷現實的精神逃亡、對可棲居的理想家園的追尋、對傳統文明價值回歸的懷想。這是他在傳統與現代、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鄉村與城市的文化沖突中做的價值選擇,更是詩人為在鄉村和城市的夾縫間生存的一代人尋求的精神出路。
劍男挖掘出自然對人類內心世界建構的積極意義,這也讓我們看到文學指導內心建設的可能性。封孝倫曾闡釋過自然美的力量,“如果說,人作為社會關系的一個扭結,在社會的網絡上被撕碎的話,那么在自然中他又重新被縫合了;如果說,人在社會階層的擠壓中被削平了的話,那么在自然中,他復又膨脹為一個四維立體的生命存在”。在與自然的擁抱中,人能收獲感官上的審美體驗,更能在對自然的沉思中回歸人與自然的本原性及和諧狀態。與自然的對話能促進個體意識的覺醒,使人擺脫心靈潰敗、生命感萎縮的生存現狀,感受到個體人格的獨立完整及個體生命的鮮活存在。劍男的生態詩歌證實了,越深入自然便越能看到大自然對于人類身心的建構和充盈具有無可比擬的力量。鄉野蘊藏了提供再教育的可能性,能夠喚醒人的感知力,將人與自然間被切斷的聯系再度銜接,從而提高人類與其生活處所之間的和諧感,激發人的生態保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