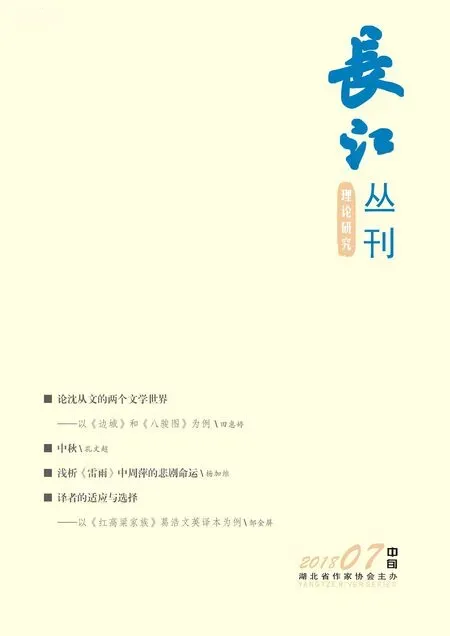實踐哲學視野中的經驗性與超驗性
■ /
山西大學商務學院思政部
一
馬克思是現代實踐哲學的創立者,實踐哲學與理論哲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實踐哲學的興趣在于人類活動本身,而理論哲學的興趣是對人類活動的現實進行理論抽象,認為這種理論的把握高于實踐本身。
實踐哲學的目的是為了對人類活動進行完整、全面的把握。本文認為,對人類活動的把握應從兩個不同的方面進行。首先是對人類活動的精神性與物質性關系的把握,這是人類活動的兩種基本的形態,實際上這二者的關系構成了哲學基本問題。其次,在價值指向的意義上,可以分為人類活動的經驗性與超驗性兩個方面,這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方面。
從哲學史上可以看出,哲學總是要超出經驗世界,試圖解決經驗世界之外的超驗領域的問題,盡管康德的批判哲學已經有力地證明了超驗對象是無法得到經驗的證明的,但直到現代西方哲學階段,很多流派特別是人本主義流派并沒有把目光收縮到單純的經驗世界之中,還是要努力地超出這個范圍,把握關于超驗性的問題。可見,經驗性與超驗性的關系,乃是哲學所無法擺脫的問題。實際上,二者的關系之所以得不到解決,并不是二者之間存在著無法溝通的隔閡,而是理論哲學對人類活動的抽象所致,人類活動的這兩個不肯分離的方面被理論哲學從思維之中分成了對立的兩極,并企圖從其中的某一個方面出發最終把哲學體系建立在一個確定的“阿基米德點”之上,這是一切理論哲學的共同特點,也是它們共同的失足之處。
本文認為,人類活動既是指向人的個體的,也是指向人類總體的,作為實踐活動主體的人,既是現實的個人,也是作為總體的人類,這兩種指向是不可分離的,人之所以以人的方式從事著實踐活動,就在于人類能夠形成延續不斷的歷史關聯,從而超出了動物界。
理解經驗性與超驗性的關系,需要從傳統西方哲學“有限”與“無限”的關系來進入,我們圍繞著黑格爾的看法來進行分析。黑格爾認為,人們之所以把有限和無限對立起來,關鍵在于對無限這個范疇缺乏正確的了解。通常人們所了解的無限性主要是指一種無窮的進展,比如在時空上的無限擴展,他認為這種擴展是單調無聊的,因為這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單調無窮的重演,他把這種無窮進展意義上的無限性稱為“惡無限”,在他看來,這種對無限的看法勢必造成把有限與無限的分裂,無限與有限分處兩邊,各自獨立。無限本是不受限制的,但這種與有限并列的無限是為有限所限制了的,不是真正的無限。他說:“像這樣的無限,只是一特殊之物,與有限并立,而且以有限為其限制或限度,并不是應有的無限,并不是真正的無限,而只是有限。”[1]黑格爾認為,有限和無限是“絕對理念”發展過程中的兩個既對立又同一的環節,真正的無限應當理解為有限和無限的對立統一,有限中包含無限,無限也包含了無限。他說:“有限性只是對自身的超越;所以有限性中也包含著無限性,包含著自身的他物。同樣,無限性也只是對有限性的超越;所以它本質上也包含它的他物。”并且,“并沒有一個無限物,原先是無限,爾后又必須變成有限,超越到有限性;它乃是本身既有限,又無限。”[2]這種無限,黑格爾稱之為“真無限”。最高的真無限,就是他所謂的“絕對精神”了。在黑格爾看來,由于“惡無限” 是對有限者的簡單否定,這并沒有真正否定了有限事物的有限性,而是重復發生的有限否定,這種無窮進展過程不論推到多遠,有限事物仍是有限的,它不能使有限事物脫離有限性而達到無限。“真無限”則不同,它在否定有限事物時,是把他物包含在事物自身之中的,因此事物過渡到他物并不是過渡到自身以外的東西,而是在他物中實現的事物自身,這樣,真無限沒有把無限推到有限者之外,而是在有限者之內的實現,是事物與他物、有限與無限的一個整體。黑格爾肯定了真無限而否定了惡無限。
然而,黑格爾對真無限的推崇是抽象、片面的,由于他否定了惡無限,造成了他必然會通過真無限來尋求某種絕對性和完滿性,這種最高的完滿性實際上否定了無限性,不能實現的完滿不是完滿的,而完滿一旦實現它又將是不完滿的。伽達默爾為惡無限作了辯護,認為無限就是沒有完結,不可窮盡,黑格爾所說的惡無限才是無限的真正本質之所在。
二
參照黑格爾的解釋,本文認為,從經驗性出發,達到經驗性的總和,這種無限并沒有超越經驗性,它仍是經驗性的,是“惡無限”,內含在經驗性之中超越了經驗性而指向人類活動總體的,就是超驗性,這種無限是“真無限”。
本文認為,經驗性的總和(黑格爾所言的惡無限)不能達到對人類活動總體的把握,不能超越到超驗性(黑格爾所言的真無限),試圖把經驗性的總和當成是超驗性,這是邏輯上的非法跳躍,因為這并沒有走出經驗性的范圍。事實上超驗性是包含在經驗性之中的,沒有不包含超驗性的經驗性,超驗性為經驗性提供了一個根底,是經驗性得以成立的基礎,但這個根底不具有絕對的完滿性,它是在無限經驗性鏈條之中的具體的確定性和完滿性,人類活動的完整性就是由經驗性與超驗性這兩個方面所構成,也即黑格爾所說的真無限與惡無限的統一。黑格爾否定了惡無限,導致了他對超驗性的把握只能是抽象的、虛幻的,換句話說,否定了惡無限將導致我們無法把握超驗性;而否定真無限,將無法把握經驗性,因為它必然是轉瞬即逝、無法規定的。超驗性為我們提供了把握經驗性的邏輯前提,這是人類實踐活動所內含的。哲學之所以要把握超驗性,不僅僅是出于哲學自身的需要,同時也為我們把握經驗性提供了依據。
和以往哲學之所以不能解決經驗性與超驗性的關系超驗性之所以成為難解之謎,僅僅是因為理論的抽象而遠離了其真實原型的緣故,我們找到了這種理論抽象的實踐原型之后,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批判對我們從人類活動出發來理解經驗性與超驗性的關系有著重要意義。針對黑格爾以絕對理念為基礎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學說,費爾巴哈指出:“思維與存在的統一,只有在將人理解為這個統一的基礎和主體的時候,才有意義,才是真理。”[3]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只是在思維自身之內實現了二者的統一,因此現實的客觀物質世界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彼岸的東西,就經驗與超驗領域的關系來說,絕對精神仍是與感性世界相分離的東西。費爾巴哈主張不是把絕對理念,而是把人作為思維與存在的同一的基礎和主體,他第一次把上帝、絕對理念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人,這是對西方哲學傳統的一次重要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從而完成了對宗教的批判”。[4]費爾巴哈把哲學的對象由超驗的實體轉變為自然的人,這是他的理論貢獻,不過,費爾巴哈對人的理解是撇開了人的一切社會關系、歷史聯系的,這只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是抽象的、孤立的個體,是一種受動的而非能動的存在,這種抽象依然不能真實地反映人的現實狀況。
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是現實的個人,這就為解決經驗性與超驗性的關系問題找到了可靠的基礎。我們認為,闡明人類活動的經驗性與超驗性這兩個方面,并不是一種理論預設,哲學史的發展從來沒有擺脫超驗性的問題,這恰恰證明超驗性與人的現實生活是無法分離的,它被看作是經驗世界之外的某種東西,只是因為當時的哲學還不具備把人類活動作為自己對象的諸方面條件,人類活動的超驗性就這樣被抽象為外在于人類活動經驗性的某種自在的實體或本質。馬克思所實現的哲學變革,為我們揭開超驗性領域的神秘面紗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工具,我們由此可以把那些排除在人的感性活動之外的超驗現象重新拉回到人類活動之中,剝離其被扭曲了的外殼,還其本來的面目。經驗性與超驗性都是人類活動的固有方面及屬性,我們也只有立足于人類活動,才能真正地實現對它們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