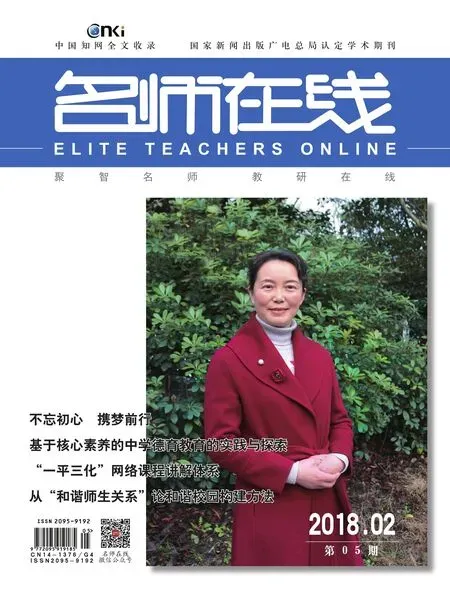文本引領(lǐng) 引向“真實”
張華秀
(福建省寧化縣第六中學,福建寧化 365400)
引 言
文本閱讀,已成為現(xiàn)代語文教學研究的主題,但文本閱讀到底引向何方,卻是千家之言,莫衷一是。文本的解讀是獨特的,也是多元的。但不管向哪個方向解讀,解讀到何種程度,都應遵循“真實”二字[1]。因而本人認為,文本引領(lǐng)重在一個“真”字。這個“真”字,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內(nèi)容。
一、把文本引向情感主題的真實可信
解讀文本切忌拔高思想。關(guān)于此點,本人可是有深刻教訓的。2000年9月,我完成了本科畢業(yè)論文,論文題目是《論竇娥冤中竇娥的悲劇美》。論文很長,近6000字,文中從四個角度論述了竇娥這一人物的悲劇美感。其中一個角度的論述是,竇娥這一人物之所以具有悲劇美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竇娥是一位有覺醒意識的女性代表,她強烈反抗封建禮教和封建家長制。我自認為這一點論述得很好,沒想到在論文答辯的時候,導師恰恰抓住了這一點,問道:你認為竇娥是覺醒女性的代表,請你再詳細闡述一下你的理由。我按文中的意思闡述,導師在一邊追問,直問到我啞口無言。之后我才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過度地拔高了竇娥的形象,使竇娥這一人物失去了真實感。仔細體會,竇娥雖然表現(xiàn)出強烈的反抗意思,但說她反封建禮教是沒有依據(jù)的,其實竇娥的某些行為不僅沒有反禮教,反而在維護禮教,就像祥林嫂一樣始終維護從一而終的女性操守。我想,這種過度拔高的解讀在教學中是常出現(xiàn)的,值得警惕。
二、把文本引向創(chuàng)作者的真實豐滿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情感態(tài)度和價值觀。我們在解讀文本時,不僅要還原作者的情感與態(tài)度,還應努力還原一個完整的、真實的作者形象[2]。我們在解讀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時,很多人在分析詩中的輕輕、悄悄那四行詩時,大多會講:他來了,來到這一所他喜愛的學校,他又走了,離開這一所他衷心喜愛的學校。不忍心驚擾這所學校的安寧,他甘愿一個人去承擔那愈來愈凝重的離愁,體現(xiàn)了作者對康橋和母校愛得深沉與灑脫。
三、把文本引向解讀者的真實體驗
在教學中,我們經(jīng)常有這種體驗,課堂上學生很難有自己的發(fā)現(xiàn),不然就是認識膚淺,解讀浮于表面;再不就是學生在課前大翻參考資料,然后搬上課堂,照本宣科。課堂看似熱熱鬧鬧,教師也可能感覺良好,實則學生一無所獲。這種課堂是失敗的。教師自己應有自己對文本的獨特理解,也應引領(lǐng)學生先拋開那些參考資料,結(jié)合自己的理解,對文本進行自我解讀,讀出自己的真實感受。在解讀過程中,只要學生的理解是合理的、有意義的,教師就應給予肯定和鼓勵。只有學生的自我發(fā)現(xiàn)才是最有價值的,也是最真實的。
《小狗包弟》中有一段環(huán)境描寫:“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里……滿園的創(chuàng)傷使我的心仿佛又給放在油鍋里熬煎。”我設(shè)置了這樣一個問題給學生討論:這里的環(huán)境有何特征和作用?學生有的說此段景物描寫表達了作者的傷感心情,有的說表達了作者對包弟和愛人的懷念之情。我引導道:“請同學進入作者的語言世界,認真分析作者的用詞用句的特征,為什么‘滿園的創(chuàng)傷使我的心仿佛又給放在油鍋里熬煎’?你們還能讀出什么?”學生繼續(xù)分析體會,一個學生說道:“這里最精彩的就這個‘又’字,說明我內(nèi)心的‘煎熬’是經(jīng)常的,接連不斷的,而作者一直住在這里只會觸景傷情,增添傷感。如果是我,我會搬離這里,離得越遠越好,而別人搬走了,作者卻未搬,這是不符合情感邏輯的,我想知道為什么。”我順勢問道:“同學們想想看究竟是為什么?”一位同學說:“因為這里留下了痛苦的回憶,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作者舍不得離開。”那位提問的同學說:“與其在這兒忍受煎熬,還不如離開,我覺得此處留給作者的是‘痛苦’多于快樂,作者應該搬走才對。”我又引導:“兩位同學都說得很有道理,可以讀出更深刻的內(nèi)涵嗎?”不一會兒,一個學生站起來說道:“我覺得作者之所以不搬離這個令他傷心的地方,與作者想要表達的主旨是相吻合的。本文抒發(fā)了作者對包弟的懺悔之情,之所以不離開這里,是因為作者要讓自己不忘自己的罪惡,用不斷煎熬的方式來懲罰自己,哪怕一次又一次地勾起內(nèi)心的傷疤,他也準備永遠承受。”聽到這些,我挺意外的,立刻表揚這位同學的獨到見解,并鼓勵同學在文本解讀中多挖掘自己獨到的東西。……之后我反思這堂課的收獲,覺得上得最有價值的就是此段,很多教師往往忽略了此段的分析,而我的學生恰恰在此段中讀出了教參上可能沒有的真實體驗。
結(jié) 語
綜上所述,我所說的“真實”并非排斥文學鑒賞的想象、夸張。我們知道,文學閱讀離開了想象,就會味同嚼蠟。我認為,不管讀者對作品做何種解讀,不能離開真實的生活基礎(chǔ),也就是生發(fā)想象的土壤是立足真實的。
[參考文獻]
[1] 史紅燕.語文課堂呼喚教學藝術(shù)——品讀《錢夢龍與導讀藝術(shù)》[J].初中生優(yōu)秀作文,2016,(2):254.
[2] 葉會彬.緊貼文字,注重方法——《名作細讀》細在何處之思考[J].考試周刊,2016,(6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