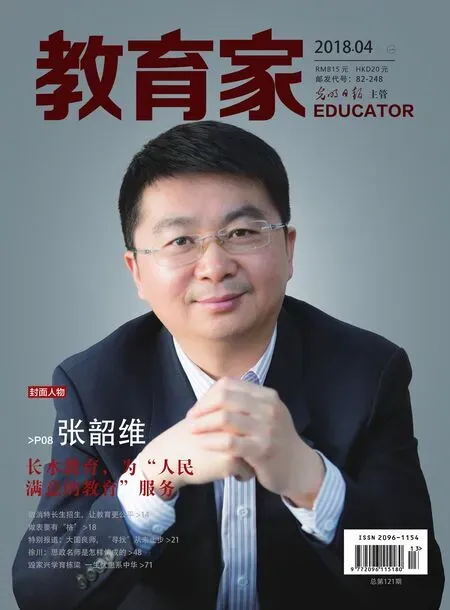“減少課堂教授”與“鼓勵多讀書”
文 | 周序
曾幾何時,老師在課堂上進行講授是一件天經地義、理所應當的事情,口若懸河、娓娓道來、侃侃而談等褒義詞匯也多被用于形容老師的課堂講授。但進入新世紀之后,講授法卻開始遭到批判,被認為會導致學生“被動靜聽”“盲目接受”,課堂教學當中應減少講授法的使用的聲音也不絕于耳。我在和一些教育學者談論講授法的時候,有人問我說:“你一定要用講授法來對學生進行‘填鴨’嗎?”可見即便是專門研究教育學的專家學者,也將講授法等同于“灌輸”“填鴨”等不良的教學形式。問題在于,課堂講授什么時候成了“照本宣科”的同義詞?如不做一番辨析,這種混淆可能還將長期持續下去。
同樣原理,不同命運
什么是講授法?通常的理解是“教師通過口頭語言,向學生傳遞教師已經掌握的知識結論。”由于知識結論是“教師的”或者說是“教科書里給定的”,因此學生只能“被動”地接受,而無法主動地“建構”。由于擁有話語權的是教師,因此學生只能“靜聽”,自己的觀點、看法沒有機會表達。按照這個邏輯來分析,講授法的確顯得保守、落后,“減少課堂講授”的觀點也就顯得頗為理直氣壯。
但即便是對講授法批判得最嚴厲的專家學者,也認為讀書是個好東西,也紛紛鼓勵大中小學生都應多讀書,提高閱讀面。什么是讀書?讀書其實就是“作者通過書面語言,向讀者傳遞作者已經掌握的知識結論。”和講授法相比,我們發現,這兩件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背后的原理其實是一樣的。唯一的不同在于講授法用的是口頭語言,而讀書面對的是書面語言。雖然語言形式不同,但本質卻一樣,都是將語言作為知識傳遞的工具。
于是問題就產生了:為什么我們在激烈批判講授法的時候,也異口同聲地鼓勵多讀書?對本質相同的兩件事采取完全相反的態度,難道不自相矛盾嗎?
說講授法與讀書原理相同,可能會有人有疑問。比如有人會說,讀書可以是“自主閱讀”,而講授法則讓學生“被動聆聽”,二者自然不一樣。因此對講授法和讀書之間的可比性,還應做更加細致的比較。
除了方式相同(通過口頭或書面語言傳遞知識)和內容相似(傳遞教師已知或作者已知的知識)之外,更關鍵的地方在于學生(讀者)的學習狀態(閱讀狀態)上。有人認為講授法導致學生“靜聽”,無法表達自己的觀點,因而是落后的;但讀書何嘗不是讀者在“默讀”?教師在課堂當中偶爾還會向學生提問,甚至組織學生思考和討論,因此學生多少還擁有一些話語權;而在讀書的時候才是完全的、徹底的靜默,想和作者交流探討根本不可能。如果講授法因為讓學生“靜聽”就顯得保守,就需要減少其使用,那么讀書就應該因為讓讀者“默讀”而更顯落后,更不值得提倡了。反過來,如果我們對“默讀”顯得無比寬容,又何以對“講授法”如此耿耿于懷?
有人說,因為讀書可以是學生從自己的興趣、愛好出發進行的“自主閱讀”,因而更有“正能量”。加上了“自主”兩個字,性質就不一樣了。而講授法則不管學生的興趣愛好如何,只要是國家規定的課程,都必須講,學生聽起來自然乏味。這一辯解看似成立但實則無理。有“自主閱讀”,那難道就沒有“自主聽講”?當年于丹、易中天等人在百家講壇開講國學的時候,圈粉無數,難道這些粉絲們都是“被迫”“被強制”著去聽的?
另一方面,如果說國家課程無法選擇,有沒有興趣都得聽講,因而是“被動”的,那么國家課程所配套的那些課外讀物、推薦書目,難道就都符合學生的興趣,一下子就都讓學生“自主”了?一個對歷史毫無興趣,無心聽講的學生,我們也很難指望他在面對《史記》《漢書》《萬歷十五年》乃至一些通俗歷史讀物的時候變得興致盎然。為什么我們總是對“聽講”中的“被動”明察秋毫,而對讀書過程中“被老師要求讀”“被家長逼著讀”等現象視而不見呢?
其實無論是聽講也好,讀書也罷,都有自主的時候,也都有被迫的時候。老師講得有趣,書寫得好,那么學生的興趣、積極性便會被調動起來,這個時候自然就“自主”了;反之,如果老師講得不好聽,或者是書寫得干癟枯燥,那么即便是學生原本感興趣的領域,也會聽(讀)得索然無味。可見,“自主”不是讀書值得鼓勵的理由,“被動”也不該是批判講授的依據。講授法和讀書在方式、內容以及學生的狀態上都毫無二致,批到一個,另一個自然也就無法成立了。一邊批判講授法,一邊又鼓勵學生多讀書,這可以說是目前中國教育當中的一個奇特的矛盾現象。
如何“講授”才是關鍵
誠然,目前大中小學課堂當中都存在著滿堂灌輸、照本宣科、填鴨教學等不良的,甚至是有害的講授,但“這樣的講授”值得批判,并不意味著整個講授法都應該予以抨擊。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教師在課堂上要不要講授,而在于應該如何講授。好的講授不會妨礙學生的自主,反而會讓學生愿意聽、想聽;也不會讓學生全程“靜聽”,而是穿插著精心設計的思考、討論和表達機會;甚至還可以讓學生對原本不感興趣的領域變得有興趣,對原本不喜歡的科目變得喜歡。這樣的講授,沒有批判、抨擊,甚至“減少講授時間”的必要。
好的講授也不一定要求講全、講透、講徹底。好書是啟發人思考的,好的講授也同樣會給學生留出思考的空間。教師可以在合適的地方“賣關子”“留懸念”,讓學生去思考,去體會,自己得出結論。因此,講授法并不是“滿堂灌輸”“一講到底”的同義詞,它并不排斥學生的“生成”和“建構”,可以將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自主性有效地結合在一起。中小學課堂中之所以“滿堂灌輸”盛行,是因為“應試”的需求壓制了教學的需求,這是一種被“異化”的講授而非講授本身。即便代之以探究法、討論法,在片面“應試”的壓力下,也往往轉變為形式上的探究和討論。而大學教師之所以偏愛“一講到底”,大約是因為“重科研輕教學”的大環境,讓他們無暇也無心關注怎樣講才能講得恰到好處。
拋開這些干擾教學的因素不談,即使是在一個理想的教育環境中,要講好也并不容易。好的課堂講授,需要老師們在語言表達、環節設計、流程安排、意外處理、總結提升等各個方面有頗高造詣,還需要大量的經驗積累,以及課前的精心思考和設計。不過在這些方面進行修煉與提高,原本就是老師的責任和義務。這就和讀書一樣。好書令人愛不釋手,是因為作者語言功底深厚、觀點深刻、見解獨到,還在寫作時做到了精心構思、字斟句酌、深入淺出。當然,這也是一個優秀的作者應該做的。如果作者在寫書時懶于構思、敷衍成篇,那必然沒有幾個人愿意讀他的書;而如果有老師因為不善言辭而不得不長期采用探究法、討論法授課,我想我們也很難說這個老師“理念進步”“方法先進”,而是會斥責他“不思進取”“原地踏步”。因此,與其糾纏于“要不要講授”,不如集中精力去思考“如何才能講得更好”。
總而言之,我們對講授法的理解還存在著偏見,往往是將講授法中被異化、被局限的講授當作講授法本身的固有弱點來進行批判。但如果我們將講授法與讀書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二者原理相同。如果我們相信讀書使人進步,需要繼續提倡,那就應該意識到講授法也不是一件壞事,因而不宜武斷地要求“減少講授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