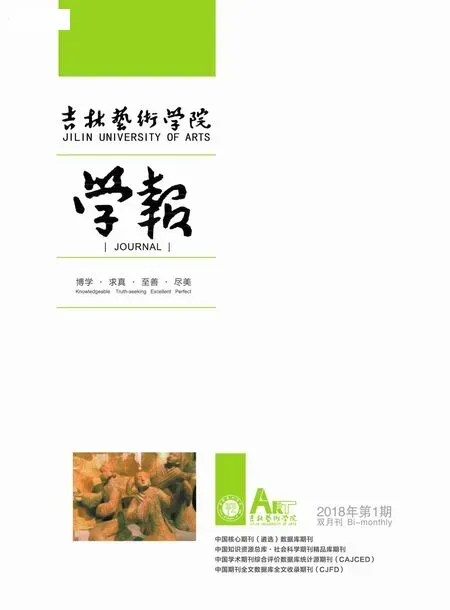歌劇《圖蘭朵》與《紅幫裁縫》中的江浙民歌主題比較研究
張雪鋒 魏 揚 陳梅明
(1.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510006;2.上海師范大學,上海,200234)
東西方文化交流從古絲綢之路到馬可·波羅(Marco Polo)來華、鄭和下西洋到旅行家希特納(Mr.Hittner)來華以及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國門,一條條商路和歷史事件無不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縮影。而在音樂文化領域,歌劇就是受其浸染和洗禮的代表性體裁之一。文中以吉亞卡摩·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歌劇《圖蘭朵》和金湘歌劇《紅幫裁縫》為分析對象,它們無論從題材內容,還是音樂素材和技法的運用上,都體現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顯著特點。圍繞江浙民歌這一素材,對兩部歌劇的民歌運用思維和手法進行分析與比較,主要從音樂素材、歌劇結構及技法進行探討,探討江蘇民歌《茉莉花》在歌劇《圖蘭朵》中的應用,浙江民歌《馬燈調》和《十月飄》在歌劇《紅幫裁縫》中的應用及三首民歌中的音程向位關系;探索民歌素材對兩部歌劇情節、歌劇結構的牽引與串聯以及對作曲技法的“同化”。
一、 江浙民歌素材在兩部歌劇中的應用
1. 江蘇民歌《茉莉花》在歌劇《圖蘭朵》中的應用
歌劇《圖蘭朵》采用五聲調式和地道的中國江蘇民歌《茉莉花》為主要線索,貫穿全劇的每一幕中。《茉莉花》別名為《鮮花調》,據音樂學家錢仁康著文說:“其曲譜早在1804年就出現在倫敦出版的地理學家約翰·巴羅(John Barrow)的著作《中國游記》中。書中說《茉莉花》曲譜是希特納記錄的,約翰·巴羅擔任過英國駐華大使秘書,他曾提示:這首歌曲當時在中國‘似乎是最流行的歌曲’。”[1]
《茉莉花》主題在歌劇中共出現了9次,在這9次變奏中,有長的、短的、甚至一句的。像一句的只用了獨奏加和弦來展現,這樣突顯了幽深靜遠;有的則是用管弦樂隊大合奏加大合唱,來凸顯氣勢磅礴的宏大場面。
譜例1為原民歌《茉莉花》旋律。歌劇中《茉莉花》主題第1次出現在第一幕中(pp45-47),且是完整使用的(這是全劇唯一一次完整使用),由童聲合唱《在東方山頂上有仙鶴在歌唱》。這里的結構為多句式單一部曲式,共有8句,調性在bE宮調式上(與原民歌調性一致),節拍為2/4拍,伴奏零星點綴,童聲伴隨著劇情中人們的嘈雜與吵鬧聲,顯得如此稚嫩與美妙,烘托著圖蘭朵那高貴而純潔的美。
譜例1 民歌《茉莉花》片段

譜例2 民歌《繡花繃》

譜例3 民歌《十月飄》片段

2. 浙江民歌《馬燈調》和《十月飄》在歌劇《紅幫裁縫》中的應用
歌劇《紅幫裁縫》是2013年作曲家金湘受中央歌劇院委約,根據“紅幫裁縫”歷史史實改編創作的,由胡紹祥、俞峰、王曉菁聯合創編的一部原創歌劇。金湘在該劇中運用了兩首浙江民歌,一首是浙江建德縣民歌《十月飄》,曲調分別放在曲首序奏、第四幕曲三、曲六、尾聲曲一、曲四中;一首是浙江奉化民歌《繡花繃》,放在第二幕第三首中。
譜例2為民歌《繡花繃》,它在整體上與常見的結構不一樣,其為五句式的結構。前奏4小節為大小鑼演奏,給定節奏和速度,然后連續唱四句,唱完第四句后再敲大小鑼,然后接著唱“哎格侖登唷”的和聲句,并結束在第五句,調性為bB宮D角調式,節拍為2/4拍。在這短短的五句中,已經有了前奏、主題段、間奏過門、補充結束句,形成了相當成熟的單一部音樂結構,節奏鮮明而輕快,頗具有浙江奉化當地音樂文化特色。
譜例3為民歌《十月飄》主題,旋律簡單易唱,調性為C調,2/4拍。該民歌主題在全劇共出現5次,皆為不完整民歌主題形式。歌詞按十個月分為十段,從不同的月份時節講述人們的生活情境。
3. 三首民歌中的“音程向位”關系
兩位作曲家對江浙地區的民歌運用如此之鐘情,顯然江浙民歌在風格與旋法甚至情感處理上有一定的共性和聯系。本文運用“音程向位”分析法將這三首民歌進行比較分析。“音程向位”(Interval direction and size)是美國音樂理論家肯特·威廉姆斯在其著作《二十世紀音樂的理論與分析》中提出的概念:“旨在分析音樂作品時對音樂前景中旋律音程的方向(Interval direction)進行定向分析、旋律音程與和聲音程的尺寸(Interval size)進行定位描述。他規定:旋律音程上行為正向、用符號‘+’表示;下行為負向、用符號‘—’表示;音程的距離則用半音數表示。”[2]音程向的基本形態包括橫向、斜向和折向,其中橫向表示為“→”、“→→”、“→→→”等,斜向又包括上行與下行,分別以“+”、“++”、“+++”或“—”、“——”、“— —”等表示;折向包括下折向進行和上折向進行,分別以“+—”和“—+”表示,音程位用半音數表示。筆者先分析民歌《茉莉花》中的旋律音程向位,分別用希臘字母“α、β、γ、δ、”(見譜例1)四種基本樂匯標記(不包括衍生樂匯)。倘若以《茉莉花》中的四種樂匯為參照,再分析《馬燈調》和《十月飄》的旋律音程向位,便會發現《馬燈調》和《十月飄》中的旋律音程向位幾乎都是建立在《茉莉花》中“α、β、γ、δ”四種向位母體樂匯上進行發展的(除個別如“ε、θ”外),或者說這些旋法之間都是相互交替變換、衍生發展的(共六種),順逆皆可。為了直觀明確,作者將這六種按順序進行分類編號,詳見表1:

表1 三首民歌中的六種基本“音程向位”特征
表1中共有六種基本音程向位樂匯“α、β、γ、δ、ε、θ”,共有二十八種形式,其余二十二種變體均為“α、β、γ、δ、θ”這五種變形、衍生而來。
“α”為兩個音的橫向和上行斜向進行,稱為橫折型音程向位,起端為g1音,柔和地微微上行三度波動,停于b1音,樂匯在第二句重復一次,形成典型的平穩、優柔旋律動機,奠定江南風格的旋法結構特征。它在三首民歌中有四種變體,共出現四次。
“β”為兩個音上斜向、橫向、下斜向進行,稱為等邊型音程向位,可帶音程位“0”或不帶,具有層次性和回旋性,衍生變化形態最為多樣,旋法頗具吟唱質感,它在三首民歌中有十四種變體,共出現十七次。
“γ”為同音反復橫向進行,為單獨音程位“0”,旋法重復具有鞏固的作用。它在三首民歌中有兩種變體,共出現四次。
“δ”為三個音的連續下斜向進行,稱為單邊型音程向位(上、下行皆可),旋法具有傾泄性和落差感。它在三首民歌中有一種變體,僅出現一次。
“ε”為兩個音上斜向大跳后下斜向進行,旋法具有張力和韌性,有脈沖與暗示旋法走向之意,因此這類的旋法很少出現在抒情的江南民歌中,它在三首民歌中無變體。
“θ”為四個音下斜向和連續反向進行,旋法具有連貫性和間歇性,停頓性傾向較強,比較少出現在流動性強的樂曲中,往往傾向結束。它在三首民歌中有一種變體,出現一次。
從上表發現,除了民歌《繡花繃》中有極少數四、五度跳進外,幾乎所有的旋法發展、衍生結構都是以二、三度進行的(四、五度跳進是歌曲情緒的需要)。這三首民歌素雅而嫻情、柔和而細膩,沒有過多的附庸結構。在二十八種音程向位樂匯中,有二十二種變體形式均由“α、β、γ、δ、θ”這幾種基本音程向位樂匯經過順行、逆行、倒影、逆行倒影衍生變化而來,母體相同的變體之間亦可相互派生和展衍。而在音程位和音程向上呈現出極大的共同點:如都圍繞音程位“2”“3”發展,音程向節律規整、有傾向性,“β”類音程向位成為三首民歌的核心旋法樂匯,“α”“β”和“γ”類的變體都可包含音程位“0”,“β”類和“θ”類的變體多起伏性和流動性,適當增強了旋律的質感和句法的可塑性。整體旋法以二、三度進行為主,輔以重復音結構,旋法邏輯方向鮮明、規律,多次鞏固并發展句法結構力,是典型的江南民歌旋法特征。
二、民歌素材對兩部歌劇情節結構和技法之影響
《圖蘭朵》和《紅幫裁縫》是兩部不同題材、情節、結構、技法的歌劇,但江浙民歌素材卻在風格、旋法、結構上有著很多相似性。
1. 民歌素材對兩部歌劇情節結構的牽引與串聯
歌劇《圖蘭朵》于20世紀20年代創作,處于晚年的普契尼在創作手法、藝術追求、審美觀念等方面都已趨于成熟。圖蘭朵的形象以征婚的方式,把愛情看成是逗趣、報復、開心的一種娛樂,以冷酷、殘忍,甚至變態的方式來任意剝奪他人生命的情節展示給觀眾,是完全憑借其獨特想象和夸張設計的。在Ying-Wei Tiffany Sung的論文中闡述到:“探索圖蘭朵的混合,東方式的范圍加西洋式的修改,她也打破了西方和東方富有想象力的障礙,真實性不再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3]作者認為有兩點原因:一是劇本戲劇性的需要,當時西方正盛行真實主義,不僅是作曲家自己喜愛這種形式,更是作為一個流派與正統歌劇相抗衡、滿足大眾需求的直接體現。二是由于中國長期的閉關鎖國使得西方人對中國情況一知半解,僅憑道聽途說與他們自己的想象編織出這樣一套離奇和懸乎的故事情節。結構上分為三幕五場,體現著聯綴結構形式,在每一幕的構架上均不相同。第一幕中作曲家并沒有以直線的方式來進行鋪陳劇情和結構,而是以其個人獨特的多層次架構來寫作的,《茉莉花》主題合理安排在三個不同的合唱小場景里。第二幕以兩個場景的形式呈現,而《茉莉花》主題則分三次置后在第二場。第三幕的《茉莉花》主題三次都出現在第一場中,這里放棄了第一幕那樣多層次的架構,而是以緊湊的方式來陳述,且《茉莉花》主題最后一次由童聲演唱的形式與第一次的完整主題遙相呼應。劇中《茉莉花》主題運用不同的結構、旋法、調性、和聲、演奏演唱方式,以每一幕3次變形發展來烘托戲劇情節和效果。因此,東方民歌就成為作曲家可依賴的捷徑和最佳素材,成為整部歌劇的核心紐帶。
歌劇《紅幫裁縫》創作于當今,不需要受制于像民族運動或流派這樣的因素牽制。它為四幕加一個附屬尾聲,情節圍繞幫會選舉和男女主角的愛情為線索,每一幕分明而清晰,沒有出現聯綴結構,歷史性脈絡和敘事性情節統轄全劇。第一幕第一場以熱鬧的序奏引出選舉合唱,而民歌《十月飄》主題正是序奏之精華所在。這首民歌暗示了一年四季時節更替與輪回,正好契合幫會選舉更替這一主題。第二幕是男女主角私奔逃上了一艘貨船離開家鄉,在第三曲中巧妙地引用寧波民歌《繡花繃》,與后曲的天色大變、海上出現了海盜上船搶劫這一戲劇性、矛盾性情節形成落差與對比。第三幕講述男主角天意被革命黨人陳發所救,陳發帶著孫中山親手設計的“中山裝”圖樣請天意制作,天意在陳發的西服上發現只有阿繡會鎖的獨特針法,由此斷定阿繡還活著。第四幕主要是講述兩人的重逢,其中兩次展現《十月飄》主題。尾聲是對男女主角的婚姻祝福,以兩次大合唱的形式呼應民歌主題《十月飄》。兩首民歌雖不能決定整部歌劇的結構,但它們的展現和出現的位置卻是作曲家精細設計的結果。民歌《繡花繃》起聯結功能,《十月飄》為主體,并設計成首尾迂回呼應。兩部歌劇戲劇情節相異,但兩位作曲家以江浙民歌為素材依托,民歌主題對兩部歌劇結構之串聯作用顯著,對歌劇的推廣和普及有著重要的牽引意義。
譜例4 三位滿洲官唱段節選片斷

譜例5 歌劇中“起承轉合”句法片段

譜例6 和聲片斷1

譜例7 和聲片斷2

譜例8《紅幫裁縫》中序奏縮譜片斷

2. 民歌素材對兩部歌劇技法的“同化”
普契尼在繼承傳統作曲手法的同時,也積極地拓展和運用了“真實主義”的創作營養,學習并借鑒了法國派的戲劇手法、馬斯卡尼的多愁善感和印象派豐富的和聲色調。“根據英國評論家Andrew Clements所述,作曲家德彪西和斯特拉文斯基也影響了普契尼的晚期風格。”[4]
(1)兩部歌劇旋法思維五聲化
歌劇《圖蘭朵》對民族調式的運用,遠不止停留在民歌上。“他虛構出一些帶有中國特色的旋律,整部歌劇從頭至尾幾乎都浸染在中國旋律的五聲性色彩中,并在很多地方使用了be小調(這是因為鋼琴上的be小調所有的黑鍵恰好表現五聲音階并易于演奏),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特有的一件古老的民族樂器——古箏。”[5]如三位滿洲官的唱段(見譜例4),可以發現A、B、E、#C四音組結構,這個四音組其實在暗示著中國五聲調式中典型的宮、商、徵、角四音特征;而在伴奏音樂織體上,也出現了明顯的持續音A音和頻繁的模進與重復發展,這可認為是西方音樂的典型做法。普契尼根據自己對中國的理解與想象,對中國元素的音樂從節奏、和聲以及音色把控等方面花了大量的手筆來渲染。在整個唱段中,作曲家巧妙地將中西方旋法元素相結合,以西為體、以中為用,既有傳統的西方思維方式,又有五聲性的縹緲想象,體現出普契尼高超而前衛的技法思維。
金湘在《紅幫裁縫》中主要運用民族調式融合泛調性和現代無調性手法來創作,大方向上與《圖蘭朵》大相徑庭。作曲家將民族化的音調泛調性化、復雜化,使得旋律充滿層次性和搖曳感,既凸顯民族調式的風味,又不失韻律感和現代性;同時運用中國傳統的“起承轉合”句法結構,展現歌唱活性與戲劇性旋律相結合的思維。如譜例5把原民歌五句式結構改寫成四句式“起承轉合”結構,不僅壓縮了旋律,統籌了節拍,而且將節奏密化、調性轉化、裝飾化,體現著“以中為體、以西為用”的核心創作思想,也加強了旋律的流動性和連貫性,賦予民歌旋律新的活力和感染力。
(2)兩部歌劇和聲語言民族化
普契尼依舊是以自己的樸素風格為主體,但打破了常規和聲學中的禁忌,頻繁地運用平行四度、五度關系,還經常使用長時值的持續音、高疊和弦、增四、增五度等和聲,使得協和與不協和混合、交織。
如譜例6的和聲不僅包含平行四、五度,而且還有很不協和的三全音bD-G、bEA與C-#G增五度,它們與基礎性三和弦相結合,表現出一種個性而獨特的和聲色彩。從另一個角度亦可看出五聲性縱合和聲的潛質,將二、三、四、五度音程與三全音音程及增五度進行縱合,形成復雜而豐富的和聲塊。
如譜例7上方和聲為增三和弦(C-E-#G)加增小七二和弦(bA-bB-D-#F),下方和聲為A-bE與F-C的五度縱合,這里的復合性和聲效果更強,既體現出德彪西式的五聲性幻想、朦朧特色,又顯示出西方高疊和弦、不協和和弦的套合,上下聲部和聲色彩既對立又彼此融合,兼具西方傳統和聲效果與民族五聲性效果,顯現出豐富多彩的音響余韻。
歌劇《紅幫裁縫》以純五度復合和聲為主要和聲技法。在魏揚先生的文章《金湘創作中的“純五度復合和聲體系”探究》[6]和《正五聲純五度復合和聲的和弦體系》[7]中詳述了純五度復合和聲的緣起、應用與發展,并將其歸為三類:五聲性、七聲性、現代性的純五度復合和聲。將其和弦分類、編號:即用“大寫字母J(金氏)開頭進行編號,后面跟著兩個數字:第一個表示有幾個純五度進行復合,第二個表示該和弦在此類和弦中的排序。”[8]
序奏是用泛調性寫作的。第1小節開始以D宮調式開頭,第4小節即到bE宮,第5小節回到D宮。接著是一系列的離調,從C大七和弦到G大七和弦,到bA大七和弦再到A大七和弦,后返回到D宮屬大十一和弦,最后轉至G徵和弦,并短暫停在G徵調式上,為合唱部分C宮主調出現作屬準備。從例10中可發現B-#F與G-B(J2-4)、B-#F與#F-G(J2-1)(第8小節),G-C與bA-C(J2-4)、#G-#C與A-#C(J2-4)(第9、10小節),并且8-10小節低聲部以B-F、C-G、#C-G、D-#G增四度級進復合(J2-6),11小節D-A與E-A(J2-5)及12小節D-A與C-D(J2-2)的復合。這一系列的復合和聲手法為選舉的爭執與戲劇性沖突作了鋪墊,也展現了選舉前夕的熱鬧場面,充分體現了民歌旋律樂隊化、交響化的力量和氣勢。
三、結語
歌劇《圖蘭朵》與《紅幫裁縫》都將中國江浙民歌作為主要素材,大膽而高超的東方調式運用與浪漫派的手法相揉合、穿插,使音樂線索與戲劇發展線索緊密結合、水乳交融。首先,兩部歌劇都有表現主義的風格,它多體現在人性的扭曲與冷酷、奇異的幻景場面,常見對唱、合唱中;同時也存在浪漫派的風格,表現了人性的復蘇與轉變、愛情的力量、幸福和平的憧憬與向往,多集中體現在詠嘆調上。其次,兩部歌劇在宏觀音樂結構與戲劇結構上的把握也很獨到,作曲家在創作中巧妙地將江浙民歌用于人聲與管弦樂隊交融以立體化、復合化,將劇中人物、沖突、內心描寫、事件與樂曲高潮統攝于心,使得歌劇的戲劇性結構與嚴密的音樂結構思維相統一、交織。按照金湘的話說:“到了具體的音樂之中,也并不是截然的對立、分割,而是有意識地相互交織,我將其稱為‘風格復調’。”[9]再者,兩部歌劇都屬于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民歌《茉莉花》在歌劇《圖蘭朵》中就是愛情的象征,卡拉夫不僅是為追求愛情而來,他還猶如救世主一般,以西方人的超級優越感和自信力來對圖蘭朵公主進行人性上的救贖和愛的感化,使其放棄復仇心理,誠服于西方文明之下。歌劇《紅幫裁縫》以民歌《十月飄》為序奏,引出兩個幫會選舉之爭,勾勒出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線索,以此來交代中國西裝史和服裝產業的文化背景。第二幕中《繡花繃》主題以兩人的愛情主題為轉折點來串聯劇情,在第三幕中襯托出西方文化對整個服裝產業崛起的影響,并在第四幕及尾聲以《十月飄》主題進行情感深化,對紅幫精神大力弘揚。兩部歌劇以江浙民歌為切入口,展現了兩位作曲家的智慧與創造、相似的美學觀念及對民歌情節的熱衷,對人性真、善、美進行了傳頌與追求。
民歌作為一種人類文明的載體,飽含著勞動人民的生活情趣與真情愜意,深刻地體現著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歷史。在某些方面,金湘甚至在繼承與沿襲普契尼的路線,繼續向前探索和發展,因此也被譽為“東方的普契尼”。巧妙運用傳統民歌無疑是歌劇創作的重要元素和兼具雋秀思想的一大法寶,不僅從素材、技法和質地上豐富了歌劇的音樂感染力和戲劇感召力,還將鮮活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融合在戲劇情節中,并將其推向世界的舞臺。這兩部歌劇以典范之身印刻著民歌的魅力,既對中國民族音樂的繼承和傳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也為歌劇創作找尋了蘊含旺盛生命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