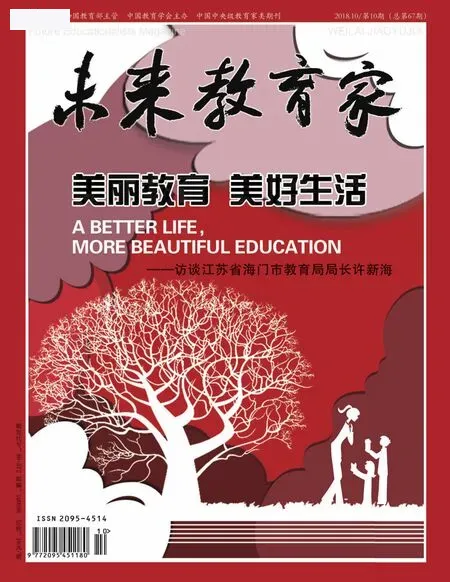“未來教育家”之路
文東茅/北京大學教授
在母校湖南師范大學八十周年華誕之際,與所有校友一樣,我最想表達的就是感謝和祝福:感謝母校的教導,祝福母校越辦越好。話短情長,母校到底給了我們怎樣的諄諄教誨?怎樣才算不辜負母校的教導?母校怎樣的發展才算是“越辦越好”?這是我常常思考的問題。我最近的答案是:作為師范大學,母校一貫教導我們要為人師表,獻身教育,努力成為教育家!只有在校友中涌現出越來越多的教育名家、大家,母校才算是“越辦越好”。
湖南師大,從1988年設立至今,一直有一個崇高的獎項:“未來教育家獎”。這可能就代表著母校的辦學理念和期盼。但何為“教育家”?如何才能成為“教育家”?可能不同人的理解有差異懸殊,我本人就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認識過程。
我1986年中師畢業被保送到湖南師大的,在1989年獲得第二屆“未來教育家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未來教育家”幾個字都給了我非常大的激勵,我曾暗下決心:終其一生實現一個目標,去掉“未來”二字,成為教育家。
1990年大學畢業后,我幸運地留校任教,此后讀碩士、博士,一直是在教育學專業,博士畢業后在大學工作,也一直從事教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從最初接觸教育學至今已經35年,在此期間,教過不少學生,寫過不少論文,做過北大教育學院的院長,參加過不少國家重大政策研究,甚至專門做過“教育家成長”的課題。按說,我本該在教育學方面有了相當的造詣和成就,本該離“教育家”越來越近。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覺得“教育家”幾個字離自己越來越遠。
為什么呢?因為在教育界有個共識——教育家要具備幾個條件:要有獨到而且系統的教育思想,同時要有長期的卓有成效的教育實踐。獨到的、系統的教育思想,長期的、卓有成效的教育實踐,這幾個條件,我幾乎無一具備。另一個原因是:我們這些教育學的學者,長期以來都習慣于“批判性思維”,對任何一位教育家都會帶著批判的眼光,“一分為二”地看待,最終,沒有一位教育家是自己發自內心尊崇并愿意效仿的。一想到即使成為教育家也終究逃不過被人批判的命運,“教育家”幾個字對自己的吸引力也就越來越小了。

古人言:“四十而不惑”,我在四十歲時恰恰是最困惑的時候。由于覺得自己人生該實現的很多目標好像都已經實現了,也就缺少了新的奮斗目標,還自我麻痹地認為是“知足常樂”“超越功名”,由此而導致自己經常處于迷茫、懈怠的狀態。我當時抱有這樣一種認識:人生就像一條拋物線,分上半場、下半場,上半場要努力拼搏,看誰走得快、走得高;下半場,就要看誰走得慢,看誰能夠在最高點上待的時間長。我想自己大概已經到了那個最高點,我的下半場,就只能是努力延緩那不可逆轉的下滑、衰老而已。所以,我執意辭去所有的行政工作,準備安心做一個普通教授,以平平淡淡度過自己的余生。這種狀況讓我想到了諸葛亮《戒子書》中的話:“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這樣的人生不禁讓人內心產生巨大的失望和不安。
是古圣先賢的經典和傳統文化讓我的生命再次燃燒起希望和夢想。我以前也學過一些孔孟的教育思想,但大多只停留在文字上,并沒有把他們與自己的生命建立聯系。從2016年3月開始,我帶著人生的困惑和“及門弟子”的崇敬之心開始每天學習《傳習錄》,進而反復學習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道德經》等經典。通過學習,我才切實體會到中華民族先賢的偉大智慧,感受到能以圣賢為師的無比幸運。文以載道,大道至簡,很多人生道理在這些經典中早已闡明,一旦明白了這些道理,我們的人生就豁然開朗、充滿了光明。
首先,關于人生。《大學》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斷修煉、提升自己的思想、品德、胸懷、境界,使自己變得更純潔、更高尚,成為一個“心懷萬物一體之仁”的“大人”。這樣的“大人”最重要的品質是“大德”,而非“財”“才”“功”“名”,“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厚德才能載物。德的提升需要貫穿終身,也完全可以持續終身,因為“至善”是永無止境的。如此看來,人生并不是一條由所擁有的知識、能力、體力、職位等有形物質構成的拋物線,而可以是一條精神境界向上無限攀升的軌跡。“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用所學的知識、能力,尤其是美德去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鑄就永遠積極、陽光、向上的人生軌跡,這樣的人生多么有價值、多么有希望!
第二,關于教育。《中庸》開篇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謂教”,《大學》也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教育的根本任務在于“修道”或“修身”“修德”,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認識,使人生的選擇和軌跡符合“為而不爭、利而不害”的“天道”“正道”,其基本途徑是落實在事事、處處、時時以至于終身的“修”。陽明先生進一步明確指出:心是身之主宰,修身之要在修心,修心就是修道,就是致良知。修心就是要在起心動念處用良知覺察是非善惡,進而不斷為善去惡。由此看來,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修養身心、立德樹人,這也是國家教育政策一再強調的,關鍵在于教師、學生、家長要真正篤信、落實。
第三,關于教師。韓愈有句名言:“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的根本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都是輔助和補充,否則就是主次顛倒、本末倒置。欲傳正道就必須先修道、悟道、明道,而其前提就是要“信道”,相信圣賢的經典中蘊含著人間大道和至高智慧,相信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追隨圣賢而不斷提升自己的道行。為此,教師首先要有堅定的文化自信,堅定地相信古圣先賢的偉大智慧及其教導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同時要身體力行,做學習傳統文化、修心修道的表率,因為“傳道”不僅在于“言傳”,更在于“身教”。通過傳統文化涵養師風師德,通過傳道授業解惑,幫助學生修道、悟道、明道,走向人生大道,這就是教師生命的意義。
這樣的教師并沒有自己“獨特而且系統的教育思想”,他們豈不永遠不可能成為“教育家”?按照通常的標準,他們確實不可能“獨樹一派”,成名成家。但在我看來,他們放棄的是自己有限的小智慧,獲得的是古圣先賢的大智慧、大學問。“心同則道同,道同則學同”,若能與古圣先賢同心同德,篤信并踐行圣賢教育思想,這些教師也就擁有了經過歷史檢驗、足以令自己自信的教育學說,這樣的教師才更有可能成為真正化育人心的教育家。
如此看來,我此前幾乎是虛度和浪費了三十余年的時光。如今,我已經年過半百,還有機會成為“教育家”嗎?每次想到這個問題,我的導師張楚廷先生就會給我無窮的信心和力量。先生開始教育學的研究時應該已近五十,還肩負著湖南師大校長這樣繁重的行政工作;1993年我成為他在教育學領域指導的第一個研究生,當時他已經56歲。先生從來沒有覺得起步太晚,工作太忙,而是幾十年如一日,勤學不輟、筆耕不輟,如今已經寫出了上百部著作、上千篇論文,成為了當今中國公認的著名教育家。先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樣,即使從現在開始,我也完全可以再奮斗三十年、四十年。我深知自己并沒有先生的智慧,但我可以直接學習先生的智慧乃至更偉大的圣賢的智慧;我或許沒有機會去創辦一所自己的學校,但如今我已經創辦了一所與眾不同的“學校”——“致良知涌泉學苑”,這個2017年初才創辦的網上公益性傳統文化學習組織,如今已經吸引了上萬名教師、學生和家長,在這里,我完全有可能開展“長期的、卓有成效的教育實踐”。看來,成為教育家,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肯不肯”的問題,我需要的是堅定的決心和堅持的毅力。
好在我還沒有放棄,“未來教育家”,我還在路上。希望再過二十年,母校百年華誕之際,我仍然在堅持的路上,也希望在這條大路上,有越來越多的校友一路同行。我相信,這才是母校最美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