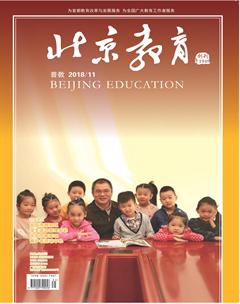教育國際化:用本土課程培養能參與國際競爭的人
王紅
近年來,談到基礎教育的國際化,各種各樣的“國際班”“國際課程”自然是少不了的“主角”。國際班通過開設各種引進的國際課程源源不斷地把中國學子送出國深造,這成為宣傳基礎教育國際化成效的證據。《2015中國教育發展報告》稱,全國約有三百多所中小學校開設了國際班。不僅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爭先“上馬”國際班,南京、鄭州等二三線城市也不甘落后,就連中西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也紛紛有模有樣地辦起來。一時間,基礎教育國際化似乎沿著這條道路走向“燦爛”。
但我心里總覺得不是滋味,直到有一天,一位來自美國、在中國2所知名中學國際部任過校長的“老外”說了一段話,讓我更加覺得,中國基礎教育的國際化實在是應該反思。他說:“中國學校的國際化,不是中國人的勝利,而是我們‘老外的勝利,因為你們不是用自己的課程把中國的學生送出國參與國際競爭,而是用我們‘老外的課程把中國的學生送出國參與國際競爭。”此話乍聽感覺非常刺耳,然而仔細想來何嘗不是事實!細數諸多國際班的“看家本領”,有幾個不是靠著IB課程、雅思課程、AP課程等舶來的“洋課程”把中國的少年學子們送出國的呢?
本來,這樣的局面在市場開放多元的格局下似乎也無可厚非,國際課程的締造者們通過國際班這樣的“代理”,把課程輸入中國的學校,中國的學生和家長購買這些國際課程就像商人購買任何一種進口商品一樣,商人賺得的是外匯,而我們的孩子獲得的是出國留學的機會,公平交易,正大光明。當然,當下對于是否在國內開設國際班、是開在校內還是校外等問題還存在爭議。問題的關鍵是這些國際班用什么樣的課程來支撐其國際化的內涵。如何開設國際班甚至國際化學校只是一個國際化的路徑和技術問題,而用什么樣的課程來達成國際化的成效則是國際化的本質內涵問題。
那么,國際化的本質內涵究竟是什么?“你可以不出國,但不可以沒有國際視野”,我的這句話曾被一些中小學校長引用作為“國際化”的注解。然而,“國際視野”也好,“國際理解”也好,這些都還僅僅是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它們所代表的僅僅是一種認知和態度,只是國際化的條件因素,并不是國際化的內核。國際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種策略選擇,它有內、外兩個指向。對外,指的是“全球化事務的參與”,就教育的國際化而言,則是有效地為全面參與全球化事務培養人才。對內,指的是本系統與外系統的兼容性,即是否憑借系統內的核心資源培養出與全球化環境兼容的競爭力,就教育而言,即是否能夠憑借本教育系統的核心資源培養出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人。教育系統的核心資源毫無疑問是課程,因此,教育的國際化也即能否憑借本土的課程培養出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人。
用本土的課程培養出參與國際競爭的人是否具有可能性?這表面看起來是一個課程標準問題,但核心卻是對國際人才核心競爭力的把握以及對本土課程核心價值的專業建構問題。IB課程也好,雅思或AP課程也好,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通行,并不在于它們掌握了國際通行課程標準的發言權,而在于它們的課程設計從內容到形式都與國際人才核心競爭力所要求的核心要素相匹配并且采取了適當的實施路徑。從這一點說,只要中國本土課程按照國際人才核心競爭力的能力目標倒推,優化課程價值追求,恰當設計課程內容、課程實施路徑,完全有可能做到用本土課程培養參與國際競爭的人。
因此,教育國際化的著力點絕對不應該放在引進什么樣的國際課程上,而應該放在如何優化本土課程,讓本土課程與國際人才標準相銜接,用本土課程培養人才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上。
所謂優化本土課程有兩種路徑,一是挖掘中國本土課程中具有較少文化壁壘且與國際人才能力素養相匹配的內容,按照國際人才能力素養進行課程價值和內容、形式的建構,如在人文素養類課程方面,中國陰陽五行的東方傳統哲學與圣經中的西方傳統哲學有很多相同之處,完全可以用中國的課程來培養學生適應國際競爭的哲學思維。二是把中國的課程元素融入國際課程進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以本土課程為內核的國際融合課程。張之洞先生提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任何一種國際課程,如果沒有經過與本土課程的融合,最多只是舶來品,并不能為中國課程的國際化帶來價值。課程的融合需要尋找契合點,如在創設STEAM課程時,可以將最具中國特色的中醫藥文化以及中醫藥萃取等元素融入課程,建構中國版本的STEAM(C-STEAM)課程。
不僅如此,當我們用本土化的課程培養出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人時,我們的課程就具有了通行國際市場的價值,那時,我們的國際化就不只是停留在“進口課程”階段了,而是步入“出口課程”的時代了。彼時,我們才能在國際競爭的舞臺上表現出我們教育系統的專業自信,而唯有建立在教育專業自信基礎上的國際化才是真正的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