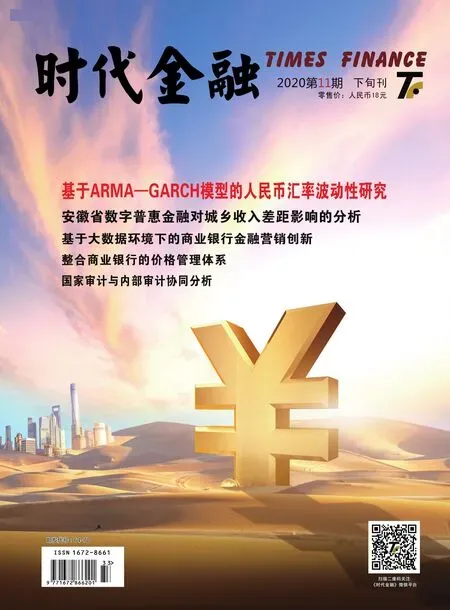人工智能等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
——基于三次產業的實證分析
王志凱
(天津工業大學經濟學院,天津 300387)
一、引言
近年來,人工智能這一概念逐漸在社會中流行開來,且發展勢頭迅猛。聯想集團首席技術官芮勇說:“這次的人工智能所引領的智能化,其實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的一個標志,就像第一次是蒸汽機,第二次是電力,第三次是數字化一樣”。大數據、機器人、無人駕駛這些新興技術逐漸融入人們生活中,使人們的生活更加便利,也引發了“機器替代人”的恐慌。技術進步會使經濟增長,經濟的增長會使就業增長,但是技術進步如何影響就業卻一直是個問題。本文采用1990-2016年的相關產業數據建立自回歸模型,探討技術進步對不同產業就業以及總就業的影響,以期在人工智能興起之時,為今后產業政策的制定以及經濟發展方式和就業方面的調整提供新的啟發。
二、相關文獻綜述
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是一個古老命題。古典經濟學家們(以李嘉圖為代表)普遍認為,技術進步就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它一方面會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另一方面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現如今,爭論焦點主要在對就業的綜合影響上:一派認為技術進步直接破壞就業(FabienPostel-vinay[1],2002);另一方面,人們相信技術進步通過各種渠道間接促進就業增長,從而帶來就業增長(Pianta和Vivarelli[2],2001)。
首先,先看破壞效應。工業化初期,其主要特征是采用機器生產而不是人力,導致對工人的需求下降,會對就業產生破壞效應。姚戰琪和夏杰長[3]研究結果表明,技術進步對中國整體就業增長有負面影響。劉書祥、曾國彪[4]二人研究表明:當前技術效率改善對就業沒有顯著影響,滯后期技術效率的提高對就業增長有負面影響。國外的研究表明,技術進步可以對就業產生創造性的影響,被稱為技術進步的間接就業補償效應。國內學者丁仁船[5]通過計量研究指出,技術進步對中國的就業具有正面影響。
國外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從長遠來看,技術進步不會對失業產生影響,在短期內,有可能增加摩擦性失業水平。劉春燕[6](2010)認為技術進步短期中抑制就業,在長期可以促進就業的增長。冉茂盛、鄒亞麗[7]指出短時間內(1-3年)技術進步對就業有顯著負效應,但從長期看(4-8年),它能促進就業率的提高。
綜合以上幾種觀點,技術進步到底是破壞就業還是促進就業跟時間跨度可能有關系。當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逐漸興起時,它對于不同產業在不同時期的就業影響是不同的。基于此,本文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運用脈沖響應函數(IRF)考察1990-2016年技術進步對三次產業就業的短期和長期效應,并考察技術進步對總體就業的短、長期效應,以期在人工智能興起之時,為減少其對就業沖擊提供幾點建議。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
首先計算三次產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由于我國三次產業相關統計數據年限較短,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建立At=A0ezt的動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其中,Yt-產值,At-時變的效率參數,它是不歸于資本和勞動的技術水平,Kt-投入資本,Lt-投入勞動,α和β分別為資本彈性和勞動彈性,等式兩邊取對數:

該對數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OLS)估算,在估算出和后,便可算出TFP,即“索洛余值”。然后對其求全微分可得:

采用產出增長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長率后的余值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在希克斯中性技術和規模收益不變假設下,ΔTFP等于技術進步率:

算出ΔTFP后,運用相關數據進行向量自回歸。
(二)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Yt:總產值(億元),選用的是我國1990-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并按照1990年不變價格平減。
Kt:資本要素投入,選用的是我國1990-201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作為資本投入指標,同時以固定資產價格指數進行平減調整。(1990-1994年和1999-2000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額通過加權算得)。
Lt:勞動要素投入,選用的是1990-2016年我國總就業人數以及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
以上指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按國家統計局三次產業分類法,將2003-2016年從國家統計局中獲得的按行業分類固定資產投資數據整合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數據。1990-2002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部分直接取自于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部分根據其中的數據經簡單計算獲得。
(三)實證分析
建立了兩變量的VAR模型后,便可測算技術進步的影響,按AIC信息量最小準則選擇模型滯后階數,按2選擇模型擬合優度最高的。相關的脈沖響應圖如下:

圖1 技術進步對第一產業就業影響
一開始,技術進步會對第一產業的就業帶來一個負的沖擊效應,但之后該效應逐漸變小,隨后趨于消失。據此,技術進步會對第一產業帶來短暫失業,但不會帶來長久的失業。第一產業的主要生產要素——土地有限,先進技術的進入將產生明顯的勞動力替代。技術水平進一步提高后,將產生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將逐步轉移。

圖2 技術進步對第二產業就業影響
起初,技術進步會極大促進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帶來一個正向沖擊,隨后逐漸消失。由此可知,技術進步會帶來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的暫時性增加,但這一增加并不是長久的。在第二產業,首先,技術水平的提高帶來了許多新行業,包括生物醫藥、新材料等,其為了擴大規模,會雇傭更多工人。但隨著第二產業資本深化特征明顯,會產生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使得傳統工業部門吸收勞動力就業的能力下降,并且工資水平的上升帶來的用工成本提高使得就業下降,導致正向沖擊消失。

圖3 技術進步對第三產業就業影響
技術進步對第三產業就業的影響波動幅度很大,這與第三產業的產業性質有很大關系。第三產業多為新興服務業,新的技術進步必然會對其就業人數產生負沖擊,但當這一新技術運用后,便又會吸納更多的勞動力。上圖中線的走向比較吻合現實情況。
第三產業技術進步主要在信息技術服務、金融、等一些現代服務業,對高級專業人才的需求是其他行業無法滿足的。然而,傳統服務業如批發、零售業等進入門檻較低,吸納就業能力強。隨著技術的普及,專業人才也逐漸增多,現代服務業就業率增加,因此波動幅度較大。

圖4 技術進步對總就業影響
總體來說,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呈現負效應。但這一負效應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四、結論及建議
本文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測算了技術進步對三次產業就業及總就業的影響。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對第一產業就業初期有短暫負效應,中長期趨于平穩,對第二產業就業初期有短暫正效應,中長期該正效應逐漸消失,對第三產業就業的影響波動幅度很大,總體上技術進步對總就業產生了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有減弱的趨勢。
經上述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技術進步對于不同產業在不同時期的就業影響是不同的,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進步加速推進的背景下,要區分不同產業不同時期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制定相應措施,減少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沖擊。
(一)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擴大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對就業的影響
從長遠來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帶來的新興產業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要加強人工智能、機器人制造等新興產業的培育,強化就業服務,促進就業創造效應的形成和釋放,實現新興產業發展和就業增長的雙贏。
(二)更加注重高端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提高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產業的就業能力
機器人等技術快速應用使人才與產業轉型升級的矛盾進一步凸現,滿足新技術人才需求不足和低端勞動力過剩問題并存,需要深化教育改革,促進人才結構調整,支持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及相關產業發展,增強就業吸納能力。
(三)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能目前主要是替代低技能簡單勞動力和具有一定經驗的熟練工人,未來很可能會從事高技能和知識密集型的工作。完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加強內部力量,增強對技術變革的適應能力,是技術進步給就業市場帶來沖擊的應對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