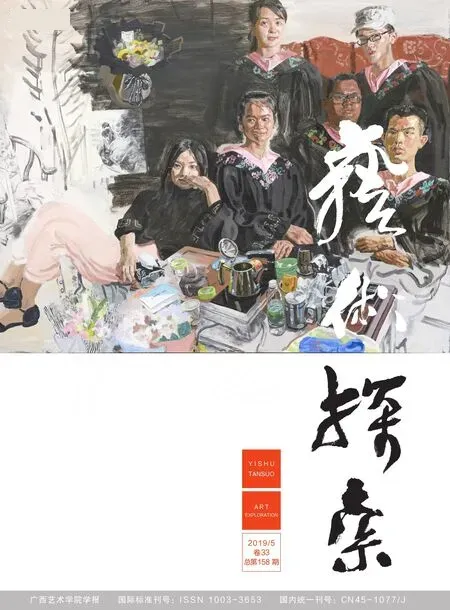中國當代女性電影的人格塑形與敘事策略
——以《嘉年華》《找到你》《寶貝兒》為例
袁道武
(上海大學 上海電影學院,上海 200072)
有關中國女性作為一個現代性性別群體的議題,可以溯源至五四運動時期。彼時的“婦女解放”是在具有現代性的民主革命與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展開的,而女性題材電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但嚴格來說,女性電影真正在中國誕生恐怕是新時期以后,作品有《沙鷗》《青春祭》等,尤其以《人·鬼·情》(1987年)為宗。這部“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迄今為止中國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電影’”[1]127-128,將中國電影中的女性意識猛然催醒。新世紀以降,女性電影開始多少帶有某種聲討男權的火藥味,以李玉的“女性三部曲”(《今年夏天》《紅顏》《蘋果》)為例,《今年夏天》首次以女同性戀作為故事主角,突出女同性戀群體的性別困惑和對男權的鞭撻,《紅顏》《蘋果》探討的重心雖然開始轉向女性的生存,但也頗有“為女討男檄”的意味。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到阜陽六百里》《萬箭穿心》為代表的女性電影敘事則立足于女性所面對的殘酷而真實的社會處境,重點突出女性的生存之難。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以《嘉年華》《找到你》《寶貝兒》為代表的對女性主義進行新的探索的影片,它們呈現出與之前不同的探索策略和文化景觀。《嘉年華》通過冷峻的語言與敘事,圍繞一起性侵案件展開對于不同年齡段的女性困境的反思;《找到你》則將視角對準事業與家庭兩難的職場女性,探討女性弱勢地位的根源與自解的可能;《寶貝兒》通過“棄嬰女拯救女棄嬰”這一帶有原型意味的母題表述女性的生命價值。簡言之,此時期的女性電影開始逐漸轉向理性探討男女兩性文化結構的議題,嘗試將鏡頭聚焦于兩性不平等的根源。這些作品盡管仍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將男性作為假想敵的傾向,但從表述策略上摒棄了獨舐傷口的凄苦與憤懣,開始以立足于社會現實土壤之上的姿態面對一個“大他者”娓娓講述,中國當代電影的女性主義探索得以以一種新的方式推進。
一、《嘉年華》:結構與意象中的景觀
《嘉年華》導演文晏在人物設置上選擇了七位女主人公,亦即“七位夢露”①“七位夢露”的提法來自《探討性侵女童的<嘉年華>:文晏與她的“七位夢露”》,新浪網,http://ent.sina.com.cn/m/ c/2017-11-24/doc-ifypathz 5553518. shtml。:小文、新新、小米、莉莉、小文母親、律師郝潔以及代表著女性意象的夢露雕像。故事圍繞一起未成年少女性侵案展開,以多線程敘事推進,這七位“夢露”對應著一個女人不同年齡的生命階段,喻指女人一生都可能處于被戕害的境地。除了隱去過去經歷的女律師,這幾位女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在她們所經歷的男性世界中受到創傷,或與男性爆發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男性的憤怒與失望同在。小文和新新遭受商會會長的性侵,資本的力量讓相關人等沉默與妥協;小米為家庭所不容選擇離家出走,是女性對家庭失望后的轉身離去;莉莉在懷上混混健哥的孩子后被拋棄,是女性面對男性抽身而去的憤怒與無力……女性人物設置基于一種性別上二元結構的立場,是該片戲劇張力的來源。
意象是本片最重要的一種創作語言,夢露雕像、金色發套、游樂場、高速公路……《嘉年華》通過大量意象的羅列,“從龐雜的現實中提煉出了它的邏輯,以感性意象搭建起了理性的敘事框架”[2]85,以客觀的意象來代替主觀的意圖表達,是一種“在一剎那間表現出來的理性和感情的集合體……意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只是一個思想,它是一團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能使情緒找到它的‘對等物’”[3]251。在《嘉年華》中,如果說游樂場、海灘、高速公路等是具有居伊·德波“景觀社會”色彩的“社會景觀”,承載著女性困境的敘事功能,那么其中的金色發套則代表著女性的成熟與性的萌發。金色發套第一次出現在鏡頭中是小文和新新爭奪金發套合影,因為戴上它拍照會“更好看”,隨之而來的是兩位女童被劉會長侵犯。隨后金發套流轉至小米手中,她饒有興趣地打量著發套,她喜愛這種女性的裝飾品。應該說小米的價值觀里原先并沒有正義與邪惡之分,直到金色發套落到健哥手中,它像《舊約》中具有拜物教色彩的“金羊毛”一樣,使小米走上迷途。
“(景觀)不是影像的聚集,而是以影像為中介的人們的社會關系”[4]3,也就是說,承載意象表達的物象,具備了景觀社會中“風景”的傳播屬性,它們首先作為物理的自然的風景,接著成為文化意義的指涉,最后凝練成一種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所指,背后反映的是社會中的一種權力關系。作為女性被窺伺和被把玩表征物的夢露雕像,承擔著作品寓意表達的重要功能。頗為諷刺的是,導演在一場映后對談中指出,其創作靈感直接來源于兩起關于巨型夢露雕像展出隨后被拆除的公共藝術事件(美國芝加哥和中國廣西貴港)②2011年7月,美國芝加哥密歇根大街上樹立起高達7.9米的夢露雕像面向公眾展覽,后被斥責為“世界上最糟糕的公共藝術作品”,不到300天即被拆除。無獨有偶,2013年12月,中國廣西貴港市也樹立起一座更高的夢露像,后同樣被拆除,有關部門給出的理由是“有傷風化”。,現實事件和文本寓意的表達形成了互文。反觀影片可以發現,從開場小米舉起手機拍攝“夢露”到結尾一群男性工人粗魯地拆卸塑像,夢露雕像在電影中每一次出現都裹挾著女性被窺伺與被把玩的意味,成為和劇中人物在情緒上共振的一個外化表達。戲里戲外,“夢露”是一種社會景觀,“她”因裙下“風景”而被觀賞,承載著男性的窺視欲望,但又承受著來自世俗的苛責,這一悖論如同埃舍爾畫作中的矛盾空間一樣,問題并不出在人們看到的世界,而是人們看待世界的“眼睛”。
二、《找到你》:新語境中女性所面臨的二律背反難題
《嘉年華》在女性話語的表述上明顯有二元論的色彩,這樣的處理方法雖然獲得了較強的沖突和張力,但卻很有可能將性別困境的紓解引向一個性別對立的局面。《找到你》在這方面就顯得較為克制,它并不注重將故事的矛盾構建在性別對立與戕害上,而是將爭取女性的主體性地位作為探討的議題。如果說《嘉年華》是從歷時性上以不同年齡縱深來選擇女性角色的話,《找到你》則是從共時性上選擇同一社會橫截面的不同階層的女性,以此來展現不同女性的困境。表面上看,李捷、孫芳、朱敏在原生家庭、教育背景和職場經歷方面差異明顯,但用片中李捷的話來說,她們其實是“處在不同的境遇,活在各自的難題中”。這個難題指向的都是新的社會語境下,女性在日趨復雜、多元、嚴苛的生存環境中如何體認自身,以及她們所面對的家庭、事業的兩難選擇。對此,波伏娃強調生育是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提出女性的“三步策略”,其中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工作。另一位女性主義學者弗里丹雖然否定女性在事業和婚姻上不可兩全的觀點,但她緊接著指出,當女性走出家庭進入職場,“雖然社會地位提高了,但是她們又面臨新的問題——在選擇是否要孩子時,在追求事業的成功時,她們感覺到沖突、恐懼和無奈,以及與此有關的具體問題”[5]2,這正是《找到你》中的女性所面臨的一個二律背反式的難題。
應該說《找到你》具備一種不同于以往《杜拉拉升職記》為代表的“有職場沒女性”的女性電影表達面向,它更加緊貼社會現實語境,并且嘗試探討女性面臨的困境與造成這種困境的根源,它所呈現的這種二律背反式難題,也讓觀眾具有一種痛感和無力感。此前的女性電影中并不是沒有這樣的探索,但《找到你》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敏銳地捕捉到現代女性在壓力陡增的職場中所面臨的困境,而這種困境偏偏是一種無奈又無處言說的悖論:一個女人究竟應該在事業和家庭中如何取舍?女性是否天然應該承擔起養育后代的責任?她是否能輕松地說出我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母親?正如影片結尾李捷所言:“如果你選擇成為一個職場女性,會有人說你不顧家庭,是個糟糕的媽媽;如果你成為一個全職媽媽,又有人會覺得生兒育女是女人應盡的本分,不算一個職業。”對此,有學者認為,“走出困境不僅意味著女性擺脫階層、地位、職業的掣肘,也意味著男性要革新觀念,參與和分擔后代的撫育,更意味著保護母職的法律體制建設和整體社會氛圍的營造,真正為女性參與社會工作、獲得平等發展提供條件和可能性”[6],即女性所面臨的這種困難的解決,需要的是兩性共同的參與,本質上指向的是建立在性別平等基礎上的一種互知互助。但是這又帶出另一個問題:面對這樣的女性難題,男性會普遍地自我體認并參與進來嗎?
三、《寶貝兒》:女性命運與身體的永續輪回
《寶貝兒》以“棄嬰”為敘事原型,講述了“棄嬰女拯救女棄嬰”的故事。同樣是被遺棄的女嬰,在長大成人后面對著同樣因為先天身體缺陷而遭遺棄的女嬰,仿佛二十年前的自己。在這一敘事原型的觸發下,引出了一個女性電影中的帶有永續輪回色彩的“被遺棄的女性”形象。從《嘉年華》中的小米,到《找到你》中那個被生父放棄治療的女嬰珠珠,再到《寶貝兒》中的江萌和無肛癥女嬰,女性的悲凄命運往往肇始于一個被遺棄的行為,而這個行為的發出者都是她們的生父。對此,她們的生母表現出悲痛并采取拯救的行動,甚至犧牲自己的身體。而當她們的母親缺席時,必然出現一位同樣是女性的拯救者,她可能是一位干練的女律師,可能是貧苦但善良的老嫗,甚至是成人的棄嬰女,但不可能是男性。《寶貝兒》中的女性形象與前兩部作品在本質上一致,作為女性,她們的宿命是遭到遺棄或者遭遇創傷,隨后成長為另一個女性的拯救者,而男人與這一過程無關。
相對于《嘉年華》圍繞未成年女性,《找到你》聚焦于現代職場女性,《寶貝兒》將鏡頭對準了生活在底層的和殘疾的女性群體,邊緣色彩更加突出,這是這部影片在女性形象上的另一種呈現。從更廣闊的視閾看,如果說前兩部作品是在探討女性在性別權力文化結構中如何體認自身的困境,如何從困境中突圍的話,那么《寶貝兒》則展示了女性在這困境中的一種先驗論式的形象。相比前兩部作品,它在女性形象構建和文化表達上更加沉重,具有一種宿命論的色彩。要注意的是,女性主義敘事一個常見的修辭術是性,而性直接指向女性的身體。性與政治、文化層面表達的親緣關系,常常使得身體書寫成為性的表征,也常常將女性敘事的表征引向對政治的指認。
四、近年中國女性電影的敘事策略
短短一年內,這三部女性題材電影的集中呈現,充滿著某種潛在的呼應社會話語流變的意味,可以說迅速變化的兩性社會語境使得創作者們早已摒棄女性主義電影中“紅顏薄命”和顧影自憐的嗟嘆老調。通過梳理近年出現的這三部女性電影可以發現,它們在女性主義表達上存在一些共同的敘事策略。
(一)女性身體的殘缺與商品化
按照巴特勒的性別操演①“性別操演理論”又被譯為“性別表演理論”,本文以所引用文獻的譯法為準。理論,“它具有意圖同時也是操演性質的,而操演意味著戲劇化地、因應歷史情境的改變所做的意義建構”[7]182,比之波伏娃的“身體是一種情境(Situation)”說,這個觀點帶有更濃重的建構論色彩,實際上我們也很難去描繪一個沒有被文化意義鐫刻的女性身體。在這個電影序列中,女性的身體變成了一種等待賦予意義的媒介,“身體不是一個準備就緒的表面,等著被賦予意義,而是一組個人以及社會的邊界,它們被政治性地賦予意義并受到維系”[7]182,而這形式就是殘缺和商品化。在《寶貝兒》中的江萌甫一出生便因為身體的缺陷而遭到遺棄,為了治病她在手術中被摘除了子宮,她身體的殘缺指向的是一個女人失去成為母親的可能性。而當這些女性在面對無路可走的境地時,都別無選擇一般出售她們最后的資本——身體,以換取生存的可能。小米為了湊齊辦假身份證的錢出賣自己的貞操,孫芳為了湊齊給女兒治病的錢選擇成為一位陪酒女郎。當女性面對她們無力改變的困境時,創作者們的選擇都是女性將自己的身體商品化。正如凱瑟琳·麥金農那句為人們所廣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性主義中的地位就像勞動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8]225這到底是女性自我的物化還是來自男權的壓迫,在影片呈現時非常容易走進女性的“自我設障”中。這一點在《嘉年華》中也十分明顯,小文和新新被性侵,伴隨著處女膜破裂引發的醫學檢查,在主觀視角固定機位的鏡頭中,女性的下體被迫重復接受著他者的觀看。莉莉對于女性的美有著本能的追求,在選擇便宜的私人診所進行人流手術后,她以酒精麻醉自己被刮胎盤的身體,恨恨地拋出一句“下輩子再也不當女人”的哭訴,鏡頭隨即跟著小米的視角掃向莉莉的臀部,鐫刻女性身體的刺青卓然入目。
(二)先驗的假想敵:孱弱的、缺席的男性
無論是《嘉年華》《找到你》還是《寶貝兒》,男性角色在影片中都被放置在后景的位置,他們成為反派或配角,成為女性登臺言說和控訴的背景板或假想敵。《嘉年華》中的劉會長作為一個以權勢壓迫女性的施暴者,他的面孔始終被導演隱匿在鏡頭中,而助紂為虐的警察、旅店老板、婦檢醫生,或是《找到你》中那個“媽寶男”的丈夫,以及在妻子孕期婚內出軌的王總……他們的形象要么猥瑣可憎,要么卑微懦弱,無法為女性困境的解決提供實質性幫助。在《嘉年華》中,負氣離家出走的小文找到離婚的父親——一個經濟身份上的弱者,為她提供一頓早餐后便將她打發回家。面對著自己讀小學的女兒被性侵,小文的父親在資本和權力編織的網絡面前一籌莫展。平日里愛吹噓的健哥聲稱可以為小米辦理身份證,卻在小米將錢給他時閃爍其詞,這是一個壞都沒壞出狠勁的男性角色。《找到你》中,孫芳的男友張博傾其所有卻不能解決女友的困境;《寶貝兒》中對江萌情有獨鐘的是一位跛腳的啞巴……他們并不是施害者,但卻無法成為困境中的女性的救助者,且他們本身也孱弱地生存著。很多女性電影的敘事策略似乎總是將男性放置在戲劇矛盾的對立面,撇開戲劇沖突和張力的需要,這樣的安排是否有刻意尋找靶心之嫌,造成女性困境的敵人是否僅僅是一名男性,這一點目前的女性電影也沒有進行探討。
(三)再次出走的“娜拉”們
將視線稍微往前推移即可發現,《紅顏》《蘋果》《到阜陽六百里》《萬箭穿心》的最后,處于困境中無法自解的女性,最后的選擇都是出走。小云、劉蘋果、謝琴、李寶莉,無一例外地在最后選擇遠離那個曾讓她們有所期許但最終無望的男性的世界。女性的這一宿命同樣出現在《嘉年華》和《找到你》中。在最終選擇拒絕出賣自己的身體后,小米躲開男性皮條客,砸碎鎖住她電動車的鐵鏈,在這一充滿著隱喻反抗男權話語的動作后,她騎車絕塵而去,前途未卜。孫芳帶著李捷的女兒,同樣準備離開,目的地是她心心念念的大海那邊的島——一個令人充滿遐想和向往的具有烏托邦色彩的彼岸世界。頗具意味的是,近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娜拉”們面對自身解放這個議題同時也是困境時,還是選擇出走。在這些女性電影中,困境的解決似乎都是被懸置的,抑或說女性擺脫困境依靠的既不是她們自己,又不是片中孱弱的男性角色。女性困境的問題最終被擱置,成為“懸案”,如果它需要得到解決,那么功能性的男性角色將會適時地出現,一如古典戲劇中最終降臨解決矛盾的神——男性的主導權力使女性得到最后的解救。當騎著電動車行駛在高速公路時,小米的一襲白衣很容易讓人想到身處男權叢林中的“夢露”形象,她和卡車上那被拆的夢露雕像形成了鏡中的互視,但導演并沒有告訴我們小米將去何方。在那個新的環境中,她是否還會重新面對之前所經歷的難題?劉會長、健哥、酒店經理式的男人們會不會再次出現并施加相似的暴力?女性電影對這些問題始終沒有給出答案。當然也并不是說,女性最后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像《今年夏天》的君君一樣,拿起武器向代表權力話語的男性執法者們開戰,但如果創作者回避女性應該怎么面對性別困境這個問題,而選擇呈現她們轉身離去的背影,那么中國當代電影的女性主義探索并沒有取得實質上的進步。
結語
在新的社會性別語境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了顯著提高,都市女性白領群體迅速成長,這一改變必將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痕跡。迅速變化的兩性社會語境使得曾經的女性電影中那種以復調形式呈現的自我嗟嘆不見蹤影。面對著女性生存現狀和女性主義崛起的現實,中國當代女性電影的探索必將繼續深入。然而,如果那些力圖為女性發聲的電影最終指向的都是一個個被凝視的“夢露”,一個個出走的“娜拉”,而伴隨影片呈現的是一個又一個面目可憎的男性形象,那這種女性電影本質上仍然沒有脫離現有的表述框架。比較典型的是,《找到你》中李捷認為“一個女孩的生活不應該被愛情和婚姻左右”,則有將女性的困境歸咎于男性并將男性作為靶心的傾向,這種女性主義話語其實并沒有真正地體認新的女性主義理論和新的現實社會圖景。
同時,面對著世界范圍內女性主義思潮不斷深化的現實語境,女性電影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在創作表達的方向上是共融地改寫文化權力的結構,還是在將意識形態的“洗澡水”潑出去的同時,把“沐浴的嬰兒”也一起潑出去?當然,我們應該承認,為了避免某種在話語上陷入模糊的相對主義趨向,女性題材電影的創作確實需要遵循壓迫和解放的一般理論,尤其是在今天的語境下,“你不可能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后現代主義者”[9]57。但如果說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的女性主義是所謂的“男權制的新的文化資本”[8]126的話,那我們必須要問:到底什么樣的女性主義才是正義的?抑或它終究是一個無解的悖論?不把男性當作假想敵,而是致力于承認女性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風貌是一種可貴的原初形式,和男性一樣,她們的優缺點都是無法抹去和遮蔽的珍貴品質,能否把其視作與男性品質一樣,是有差異無優劣的存在,這恐怕才是中國當代女性主義電影創作值得思考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