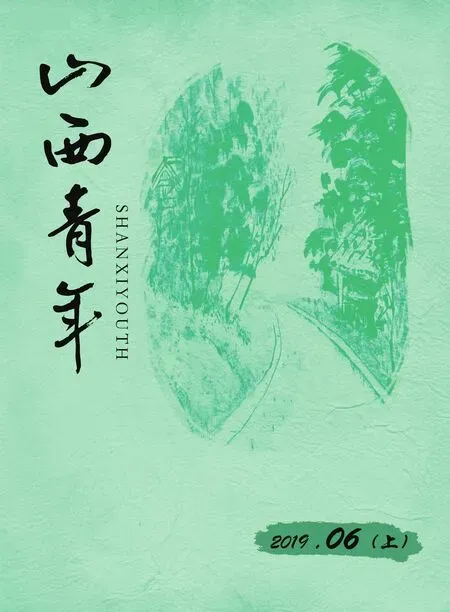當代中國大學生領導力的探究
孟祥韻
(中山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一、建構領導力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2015年國務院出臺《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指出“遵循教育規律,創造性地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堅持用價值觀引領知識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1]《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著力提高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和善于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2]對于領導力的探索和培養,國內外高校、社會群體都摸索出各種方法,凝練出不少的理論,尋找各個領域領導力的最佳路徑和最優建構,但領導力的概念和發展依然充滿著模糊化、不確定性。
二、高校領導力的現狀
(一)領導力理論的發展狀況
最早提出領導力理論是英國的文學家Carlyle提出的區別于常人的特質領導力,[3]這是一種對偉人們的一種描述性語言的創造性表達。最初對英雄偉人事跡和行為的描述逐步發展為各個領域領導者的行為理論建構和延伸,類似綿延的理論,試圖從研究領導者的行為、風格等各類素質和特質提取出可復制、可借鑒、可持續發展的領導力理論體系,進而塑造更多的“領導者”。這類理論典型特征便是在“綿延”中試圖尋找永恒的真理。類似帕格森的“純粹綿延”理論。起源是關于領導力理論的眾說紛紜,逐步發展為各個行業領導力,各個領域領導力,領導風格(或主或仆,或二者的結合體)、模型建構如勝任力冰山模型、洋蔥模型等素質模型.[4]
西方國家如美國高校領導力教育突出公民教育的引領地位,采取社會變革模型[5]國內高校的做法有成立專門教育機構。[6]國內有學者認為高校基層黨組織是大學生領導力教育的一個路徑。[7]國內關于領導力的理論分析從各個視角分析,例如5M視角下的領導力理論,[8]以職業發展為導向的大學生領導力開發與培養,[9]以全體成員在多元層面的元分析理論視角研究多元領導力[10]等高校對于領導力的分析和理論研究多層次、多角度不斷拓展和豐富領導力的理論和實踐。
(二)大學生領導力的主體
關于大學生領導力的培養模式雖然眾多,一般較為偏重學生干部的領導力培養。一般來說,大學生社團組織的架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部門為責任主體開展和落實各類學生活動,依靠各類組織開展培訓活動,與國外的學生事務中心功能基本一致。此外,學生自發組織群體,學生自媒體平臺,各類興趣小組。所以大學生領導力的主體為學生群體,需要指明的是專業教師在大學生領導力培養的頂層設計的參與率較低甚至處于邊緣地帶。
(三)大學生領導力發展現狀
1.技能型領導力培養
國內有一些研究者認為大學領導力依托或長或短的培訓,通過學生社團、公益組織等各類平臺開展系列活動和集中培訓。一方面從施與者方面覆蓋面較小,另一方面從受眾者即學生群體根據興趣、意愿來選擇活動、選擇平臺、選擇受訓技能,業余技能、生活技能等較為普遍和實用。
2.實踐型領導力培養
誠然,實踐出真知。有些高校將大學生領導力的培養重心放在實踐行動上,激勵和引導學生走向社會,走向公益,走向基層社區、村莊,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例如服務當地中小學教育的支教活動,定期關愛老人的敬老院公益活動,運用專業知識進行鄉村改造的社會服務活動活動等等社會實踐。這類領導力的培養雖然增強了學生的社會性、提升對社會的認知和自身的社會性感性認知和理性經驗。
3.創新型領導力培養
秉著激發學生創新性的能力,高校設置一些橫向和縱向的創新型項目,成員之間共享領導力,利用專業特長、個人特長、校內外社會資源圍繞一個共同目標,成員可以是虛擬團隊和面對面團隊,無論是新技術運用還是溝通的方式較傳統的模式都有較大的改變,即從過程到結果的進程中體現創新。
4.領袖型領導力
學生干部多以領袖型領導力的培養方向進行。學生的自我意愿較強,自信心較足、好勝欲望較強等表現張力較強,同時自我管理能力較好,內驅力較足,所以無論專業還是學生活動、社會實踐等方面稍加引導,提供平臺均能嶄露頭角。以上多以“領”和“導”而形成的合力,學生自我領導力固然有但不占主體性地位。尤其是領袖型領導力的誤區較為普遍,在于學生入校后對于領導力的認知并未有系統的理論培養體系導引,更普遍的原因關于技能、學術能力等方面學生群體及社會群體并不認為他們屬于領導力的范疇。
三、大學生領導力缺失的原因
(一)概念意識誤區
關于自由主義的認知如同對于領導力的認知一樣,一般均從字面上去理解。我們對于自由的認知程度之低等同于領導力的認知程度。領導力培養可塑性較強,它融入人的知識、本性與身心,擁有它則改變人的“內包裝”和“外包裝”,塑造了人的社會性,猶如萬能鑰匙總能打開各種各樣的“門”。因此,領導力的智慧不等于精湛的學術、技能等專攻的“術業”,領導力是一種融合劑,不僅是自身更是他人或團體的融合劑。
(二)大學生群體偏見
利己主義的傾向較為普遍,比如剛進入大學階段,大學生群體一個較為明顯的表現是積極參加社團、競選班干部,大二階段這種積極的心態和行為依然較為明顯和突出,這類激情為青年人的特征;大三則進入了分水嶺,學生自身前途及生涯發展成為最首要的關注點,將班級事務、社團工作等職責降至次要和非必要地位。活動開展的導向性同步會有變化,但學生參與公共活動,承擔公共事務的激情明顯下降。
(三)小眾意識
盧梭曾區分過“眾意”和“公意”,誤區在于人多或呼聲高的“眾意”就是正確的,少數甚至極少的“公意”就是錯誤的。對于公和私的態度,例如對于遠大的理想和近在咫尺的利益,多數人擇其后者,對于眼前的利益和不遠將來的目標更為用心和在意。凡是基于人類理想事業的長遠目標而成就的偉人都載入史冊,對比那些只顧及私人利益、小團體利益甚至不惜損害他人利益的人不在少數,思想意識無法放開、無法突破自我的界限,正確的價值觀對于他們是外在的擺設,內心獨崇的自我才是至高,這類價值觀有較強的感染性和誘惑力,人往往在做抉擇的時候受眾多外界因素的影響,理性的觀念的向心力往往敗給離心力的自我意識。
(四)理論課程的普及程度不高,覆蓋率較低
高校中學科分類的細致化和學生的專業化等現狀,與領導力相關的學科普及程度較低,例如心理學、社會學、統計、公共管理、政治哲學等目前尚局限于本專業內學生。近年來隨著通識教育的興起,大學生對于公選、輔修以及必修課程的重視程度明顯有差別。領導力相關的學科教育尚未獲得較為明顯的成效。
四、大學生領導力的培養路徑
(一)樹立價值觀
價值觀一般以是否順應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為標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培養大學生領導力的第一要務,這個標準是檢驗當前大學生價值觀正確與否的試金石。引導學生形成穩定的價值觀,在職業生涯規劃中和人生的抉擇中始終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校園活動不局限于自身專業,引導學生從“小我”走向“大我”。
(二)領導力學科知識系統化
首先,隨著互聯網興起,學生的學業依然是以自身專業為主,輔修專業為輔,接收知識更加零碎化、片面化,“淺嘗輒止”的閱讀模式在互聯網的強大漩渦中不起漣漪。第二,網絡的海量信息及誘惑性挑戰了新時期大學生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能力,同時挑戰了三尺講臺的權威性。學校層面對于領導力知識的系統培養尚未形成門類和考核的標準。第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學習和全面掌握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大學生群體的理解和接收知識的能力較之其他群體有更明顯的優勢,學生群體一般認為黨員有必要有責任深入學習和掌握,非黨員的學習意識有待加強。學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維能力尚處于建構階段,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的運用和實踐處于摸索階段,迷茫和懵懂,例如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解尚停留在字面。理性的觀念是在知識的積累中不斷堅固和完善的,擁有領導力可以用理性的觀念指導實踐。因此,應對領導力學科知識進行系統化、整體性配置和展開。
(三)拓展領導力的參與者、設計者
教授傳遞的不僅是專業的科學知識,也有學科與人生的道德規范,嚴謹的學術氛圍無形中塑造學生的學風、班風、校風。領導力能夠發力和有力需要全面的視角,全員的參與,對學生的教育培養和塑造,教師團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學生受教育的影響因子不僅來自活動,更來自講臺和課堂。所以應當拓展領導力的參與者和設計者,豐富領導力培養的方法。
五、小結
領導力的培養不是為了成就“領袖”而是激發學生形成積極的人生觀、價值觀,社會化成熟、價值觀穩定、綜合素質強,進而認識世界、服務社會、奉獻自己,推動某一領域的學科發展、社會進步的參與者和實施者。如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論,大多數人的智力理論是不完備的,從某個特定的角度解釋智力,每個大學生的領導力是參差不齊的。培養領導力不僅需要了解他們的內心境界和個性特征,人類社會的發展積淀下來的智慧和經驗如何灌輸到他們的頭腦中,落實在他們的行動中,在領導力的培養中需要把握二者的關系,同時多變的社會環境、高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全球化的發展模式、政治、經濟等外部因素的諸多不確定性,這些社會因素是領導力的應對的外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