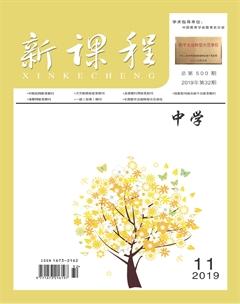平行空間也要相交重合
向深晴
平行空間的理論是由現代量子力學的發展而提出的,在物理學中的專業術語為平行宇宙,它是指從原宇宙分離出來,與原宇宙平行存在,既相似又不同的其他宇宙。科學家原本認為,平行空間是完全平行的,既不相交也不重合。但隨著近些年的研究發現,這一看法并不完善。講到這,可能以為我在科普宇宙知識,然則我卻是要講一個類似平行空間的故事。
去年7月,驕陽似火、夏日炎炎。我和準高三的孩子們正在做最后沖刺,高考備戰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學校突如其來的一個通知讓我手足無措。高三課程不變,兼任初一班主任、數學老師。我頓時又蒙又傻,內心一陣混亂。高三和初一,這可不僅是教學的跨度,更是學生年齡層的跨度,還是我個人對于教學方式理解的跨度。在我的工作規劃里,只不過才總結出一些對高中授課和育人的個人理解,還沒有完全去實踐運用,突然又讓我重新開始另一項工作,這就好像我在拼命死勁地爬歌樂山,躊躇滿志地想沖向山頂,但是快到半山腰了,告訴我前方封路了,請沿著橫向的小路去繞道。這簡直是給我出了一道壓軸的世紀大難題。
但是,大詩人也說過“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我內心艱難,熬過了暑假。開學后,整個事態的發展并沒有被我內心的那種抗拒所驅使。我每天的工作被安排得特別緊湊,而整個節奏也是出奇快,實在是沒有時間再去思前想后。
涌泉樓、操場、通慧樓之間來回不停地穿梭。上一節課還在探討高三年級函數問題,而下一節課就轉換到給孩子講正數、負數的概念問題;一小時前還在以亦師亦友的姿態和十七八歲的孩子暢聊人生,一小時后就在十一二歲的孩子面前表現“教不嚴,師之惰”的態度。每天都在各種人設之間變換,在各種矛盾沖突之間游走。高三與初一的教學,大孩子與小孩子的管理,不同年齡層家長的應對,還有那一段樓與樓的距離。兩個跨度就好像兩個平行空間,看似毫無聯系,實則慢慢擦出了火花。
一段時間,我正在苦惱怎樣糾正幾個聰明的初一孩子學習習慣問題。數學需要嚴密的邏輯過程。但是初一孩子剛剛洗去小學時的浮躁,心智不穩。在解題時,孩子們總是情愿想破腦袋,也不愿意落實到筆頭上。我擔心長此以往,孩子們便會粗枝大葉,形不成嚴謹的學習態度。我嘗試了很多方法,意圖改變,但收效甚微。我知道我必須轉變思路,另辟蹊徑了。不曾想,高三的孩子解決了我的難題。一次班會課,我邀請了大孩子和小孩子作分享交流。小孩子們很興奮,聚精會神、目不轉睛,甚至還做起了筆記。大孩子不經意間將我擔心的問題拿出來討論,并且還將自己厚厚的錯題集展示給小孩子看。那一刻,我知道我不用再糾結了。快要踏進大學的學長學姐尚且還需注意習慣,更何況這些小毛頭呢?
高考一輪復習階段,有的高三孩子總在計算過程中出錯,導致失分太多。從前,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大都讓孩子自己處理,自我總結。想想,高三的孩子如果在計算問題上還頻頻出錯,那豈不是白走一遭了。幸好,在初一,我正肩負著培養學生的數學計算能力的重任。每一個細節的教學,每一個能力的提升都是高中教學不曾給予的。我可以很輕松地找到大孩子們計算方式上的弊端,從而給予他們正確的提點,并適當做一定訓練。從此,大孩子的計算錯誤寥寥無幾,計算方式越來越優化,計算能力日漸提高。
初一班上有個小孩子,家庭情況特殊。小孩子小學時,還能照顧于左右。上初中后,父母為了生計,到外地做小本生意,孩子的爺爺輩也不在了。沒有成年人照顧孩子,家長迫于無奈,只得在校外給小孩子租賃房子,讓其單獨在外學習生活。我不禁想到我高三的一個大孩子,他和小孩子有相同的經歷。初中時期,父母長期不在身邊,沒有了家長的約束,缺少了父母的關心,他從名列前茅變成了班級學困生,甚至多次違反校紀校規,直至被勸退。大孩子的父母這才悔不當初,重新開始,孩子才得以脫胎換骨,重歸正道。起初,我多次勸告小孩子的父母,但不盡如人意,直到小孩子長期遲到,成績有所下降。我立即將大孩子的父母邀請到學校與小孩子父母交流,至此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小孩子的父母重新找尋了生計,回到孩子身邊。
數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平行線永不相交。之前,接到這項任務時,我百感交集。認為這兩種跨度就猶如兩條平行線,看不到交點,找不到相互之間的交集,它們只能存在于平行空間中。但是,我卻忽略了,數學中還有一個概念,即是在向量的世界,我們不在乎起點,平行向量就是共線的向量,平行就是共線,它原本就擁有無數個交點,相互之間有無數的交集。就像這看似跨度巨大的兩個教學任務,原本以為根本沒有共同點,只會是兩個難度不同的問題。沒曾想,它們卻摩擦出了幸福的火花,照亮了不同空間的孩子。正所謂“單絲不成線,孤木不成林”。單獨的一條絲并不能成為有用的一條線,去承受重物。再挺拔的一棵樹也不能成為浩瀚的林海,去潤養大地。平行的空間也要相交重合,才能開啟多元的世界。
平行空間的碰撞,開啟多元的教育。這是一種新嘗試,也是一種新方式!
編輯 高 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