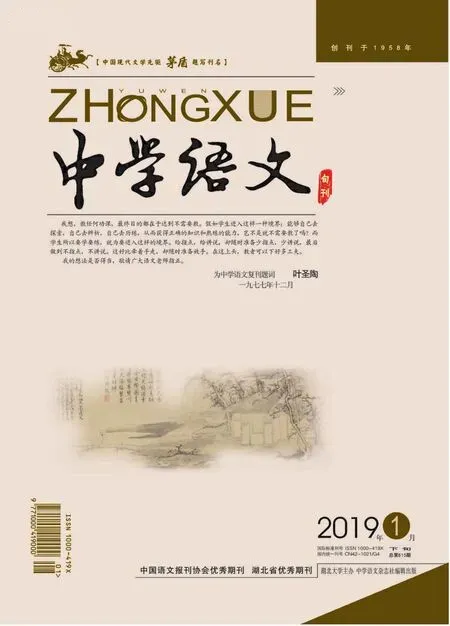人教版必修1第一單元教學札記
黃 蓉
提到煉字,人們總是想起杜甫的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總是想起盧延讓的“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提到煉字的經典,不外乎“僧敲月下門”中的“敲”,“紅杏枝頭春意鬧”中的“鬧”,“云破月來花弄影”中的“弄”……煉字似乎和詩有很大的關系,而且常常是古典詩。那么現代詩是否也講究煉字?如何讓學生品味其中的妙處?下面我想以人教版必修1第一單元為例,談點粗淺的看法和做法。
人教版必修1第一單元是學習現代新詩,《沁園春·長沙》是新舊詩的銜接點。“沁園春”是詞牌名,《沁園春·長沙》的作者和內容都是現代的,其他3首詩都是各具特色的白話詩。在教學中,我發現不管哪種形式,講究煉字是其共同點,我們可以采用比較教學讓學生更好地品味賞析。
以《沁園春·長沙》為例,詞人在描繪絢麗多姿、生機盎然的湘江秋景圖時,視角由遠而近、由高而低,有兩句學生都認為寫得精彩,即“鷹擊長空”“魚翔淺底”,都認為有兩字用得妙,即“擊”“翔”,但問及為什么時就卡殼了。但老師說換一種說法或換一個詞試試,氣氛又活躍了。 經過“擊”與“飛”、“翔”與“游”的比較揣摩,學生不難體味“擊”的力度和矯健,“翔”的自在和輕快,且與整首詞的激昂格調是一致的。
再如《雨巷》,詩人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結著愁怨的姑娘”,這姑娘“撐著油紙傘”彷徨在寂寥的“雨巷”。其中“丁香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意象,分析了李商隱等詩人寫的3首有關丁香的詩后,學生不難體味丁香代表的是高潔,是花中的愁品。但我覺得詩歌中的另一個道具“油紙傘”也不能忽略。我們可以讓學生將油紙傘與其他傘抑或是斗笠進行比較,緊扣意象的內涵,不難得出:戴斗笠的男性大多是隱者或俠客或漁夫;而戴斗笠的女性大多為漁家姑娘;其他的傘要么花哨要么洋氣;而只有油紙傘既古典又知性,加上蒙蒙的雨,更顯神秘。與“丁香”的色調一致,給詩歌的主旨也賦予了神秘的色彩。
再如《再別康橋》,如何讓學生體味徐志摩對康橋的那種揮之不去的淡淡的憂愁又深深的眷戀,通過對一系列意象的賞析,是可以初步達到效果的。但如果對融入了詩人情感的意象進行比較賞析,那效果又非同一般。如第二節中的“金柳”換成“楊柳”“綠柳”如何,“艷影”換成“倒影”如何,“柔波”換成“水波”如何,一比較一揣摩,“金柳”不僅僅映襯了夕陽更煥發了“新娘”的嫵媚,“艷影”和“柔波”都滿含著詩人對康橋的深深眷戀。
再如《大堰河——我的保姆》,詩中歌頌的是一位勤勞、善良、樂觀、質樸的勞動婦女,質樸的敘述固然感人,但有一處感人的細節,我覺得不容忽視:“……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里,撫摸我”。一般情況下,學生抓住“把我抱在懷里,撫摸我”,也能感受到大堰河對“我”的溫馨的母愛。但如果我們將“厚大的手掌”中的“厚大”換成“纖細”如何,細細比較,學生不難發現,這“厚大的手掌”是勤勞的勞動者的手掌,不僅符合大堰河的身份,又能在表現其母愛的同時,表現出她的辛勞、她的賢惠。這與詩歌前面的敘述相吻合,正是有前面一系列的勞作,手掌才變得厚大,因為在“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里,撫摸我”之前,還曾補好了兒子們被荊棘扯破了的衣服,包好了小兒被柴刀砍傷了的手,掐死了夫兒們襯衣上的虱子;也正因為大堰河是這樣一位心地善良、勤勞賢惠的持家人,所以也就有了“她死時”“平時打罵她的丈夫也為她流淚,”“五個兒子,個個哭得很悲,”“你的乳兒是在獄里,寫著一首呈給你的贊美詩”。
這樣看來,詩人講究煉字,大多從情感、意境、主旨出發,為的是更生動傳神地刻畫人物、表情達意。通過對人教版必修1第一單元的教學,我覺得比較賞析可以讓學生更好地體味詩中的情感,這也許就是所謂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的效果。不過這個“嚇”指的是引起讀者的心靈顫動,從而達到共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