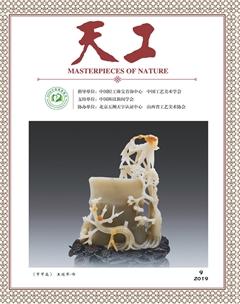中國早期佛雕藝術的審美演變

[摘要]佛教并不是我國的本土教派,其產生于印度,因此我國早期佛雕藝術受到印度佛雕藝術的影響較大。通過對印度佛雕藝術民族性的改造,使其逐漸演變為帶有中國特色的佛雕藝術。雖然中國早期佛雕藝術發展充滿了曲折性,但是其為后來佛雕藝術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早期;佛雕藝術;審美演變
佛雕藝術東漢時以小型佛雕的樣式傳入我國,由于其模型較小,并不足以被大眾文化認可和接受,直到北涼時期產生了洞窟佛雕藝術,此時其才真正作為一門新興的藝術形式出現在大眾視野內。
北涼的佛雕藝術幾乎完全模仿了印度風格,但是其在我國佛雕藝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標志著我國佛雕藝術的正式產生。由于完全繼承了印度佛雕風格,北涼佛雕展現出了宗教藝術本身的神佛性。此外,其作為外來的文化形式與我國固有審美產生了巨大的碰撞,其所具有的民族特性也被認作是一種神性。
因此,我國的審美文化對印度佛雕藝術改造也會從這兩方面進行,首先是去除掉來自外來民族文化的陌生性,讓其回歸民族,產生民族審美文化內涵。其次便是去除印度佛雕藝術所具有濃厚的宗教藝術性,使其往生活靠攏。這兩方面是逐漸表現出來的,在佛雕藝術傳入初期,去除其具有的外來民族特性,展現出自身民族內涵是最為迫切的,世俗性內驅力發揮出了主要作用,而藝術性內驅力則發揮其輔助作用,完成佛雕藝術本土化改造。
北涼佛雕藝術興起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歷史原因,其二是地理文化因素。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到東漢末年由于連年戰亂,所構建的儒家倫理體系已然崩壞。戰爭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是儒家學說并不能解釋戰爭帶來的生命茫然感,而佛教的傳入正好契合了人們的思想,讓人們可以在連年的戰亂中產生新的精神依托。佛雕藝術作為佛教思想的先導,以具象的表現形式引導人們產生抽象的信念,從而讓佛教思想便于傳播。佛雕藝術從西域而來,其想進入中原地區就必須沿著絲綢之路先通過西域,因此佛雕藝術文化在北涼地區興盛。
北魏佛雕藝術的發展依然憑世俗性內趨力量推動,但是較北涼更為深入。而藝術性內驅力則發生了轉換,其由形式因素轉變為內容因素。這也十分符合古人對于外來文化的改造習慣,先從形式因素開始,將次要因素與民族審美文化內涵相融合,再延伸至主要部分。
世俗性內驅力主要通過統治者干預體現,這—進程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滅佛與敬佛的轉換,其次是法門主動向權力的靠攏。佛教講究萬事皆空,舍棄紅塵,世俗所有事物都在拋棄之列,權利自然包括在其中。并且佛教勢力日趨長大必然使統治者產生戒備心理,此實為滅佛之因。佛教作為外來文化,當傳入另一地域時,其必然想保持最原始的狀態,這就會與本地文化產生沖突。傳入我國的多為大乘佛教,就是因為其較為靈活,可以與我國文化融合,并且其尊重世俗權力,此便為敬佛之由。
北魏佛雕藝術的變動充分體現了民族藝術性內趨力和祖先崇拜儀軌的內在作用。印度佛雕藝術具有濃重的西域風格,而其傳入中國后,與中國傳統的羽人飛仙結合,從身體短壯、姿態笨拙轉變為體態輕盈、身浮云氣的形象,這種形象淡化了其所具有的神性。此時,佛教傳^中國已有了一定的時間,但是其與本土文化還尚未融洽,但是中國文化已經表現出了對其認可的態度。盡管在內容因素方面還存在著沖突但是形式因素已經進行了審美文化內涵的改造。佛雕藝術向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演變邁出了第一步。
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東晉佛雕藝術極為繁榮。雖然保存下來的佛雕較少,但是其形式多樣,有著多種創新風格。東晉佛像雕塑石窟形制較小,盛行小型佛雕,且多以單尊造型為主。由于受到西域及北方藝術風格的影響,并且又在其中融入了自身的風格,從而形成了繁榮局面。單尊的佛雕對于經濟實力的要求大大降低,此時土族也有了建造的能力,權力中心對于佛雕藝術的影響力便受到了削弱,士族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佛雕藝術可以被更廣泛的建造。
東晉時代審美趨向于張揚,因此佛雕藝術也就沿著張揚藝術性趨向發展,而此時形式因素與內容因素幾乎占據了相同的位置,藝術的內趨力與世俗的內趨力都發揮了文化改造的作用,佛雕藝術世俗性的發展同時也使其藝術性更強。當以世俗的標準來理解佛的神性時,其便成了一種觀念物,有效地去除了神性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取而代之的是親切感。世俗性內趨力對神性的反動,使其藝術性的發展更進一步。
北魏分裂后,北方又陷入了連年戰火的狀況。而南方朝代同樣更迭頻繁,經濟政治動蕩不安。雖然此時的君王多崇信佛教,但是政治形式動蕩、經濟局面的衰退導致佛教藝術也同樣衰落。
到了東魏時期,佛教思想有了極大的發展,此時佛教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更符合本土文化。所以在佛雕藝術衰退之際,佛教思想卻廣為傳播。雖然佛教思想的繁盛與佛雕藝術衰落相背離,但是思想的繁榮必然會促進其方便法門的發展,也就表示佛雕意識只是暫時進入了冷卻期,佛教思想的興盛必然會使得佛雕藝術再一次繁榮。
佛教思想的不斷傳入使得其打破了士族壟斷的狀況,逐漸走入大眾視野,被廣大群眾所接受,佛學玄學化已成為歷史。而佛教的大眾化使得佛像體裁和造像形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普通大眾開始了小規模的造像活動,并且由于連年戰亂導致的經濟衰退,大型佛雕造像逐漸減少。佛雕藝術的規模發展逐漸平緩,而風格上有了更多的表現形式,多種新穎風格的佛雕造像應運而生。
至東魏晚期,中原地區的佛雕造像依舊沿襲北魏風格,但是這種風格形式較為單一,在過多的實踐中逐漸流程化,喪失了佛雕造像的藝術性。而且北魏士大夫的形象在普通大眾審美下發生了轉變,成了空疏無用的象征。此時,普通信徒的形象融入了佛雕之中。但是由于其所具有的北魏風格未完全消除,兩種風格形象融合在一起,卻沒有很好協調,導致佛雕過多地喪失了神性,充滿了世俗氣息,神性過多地向世俗性回落,導致神性的本質也逐漸喪失。這一時期的佛雕藝術處于矛盾激蕩的階段,神性和世俗性沒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而是相互背離,但是卻共存一體。
北齊年間,佛雕審美矛盾減弱,其繼續向大眾靠攏。佛雕不僅僅是佛陀形象,而是出現了多種菩薩形象,并且雕像的姿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表現出更多的閑適。經過北齊初期不成熟的探索,圓潤疏簡的風格逐漸形成。此時菩薩花冠形式繁盛起來,并且具有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我國早期的佛調藝術處于文化融合期,作為印度傳入本土的外來藝術,其必定會與我國的審美風格和理想產生碰撞,但是在碰撞中會表現出復雜多變的審美內涵。而在不斷發展過程中,這種審美風格的沖突會逐漸平緩,取而代之的是融合與轉化,相互之間的融合加強,便會形成獨具特色的藝術門類。
[作者簡介]
林匯,福建閩侯人,1993年師從柯加樂,后經林學威等多位大師指導授藝,博采眾長,自成一家。2007年成立“匯寶居”工作室。以琥珀、翡翠、水晶、南紅為載體,傳承創意理念,擅長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以及各種侍女龍鳳等雕刻。其作品供不應求,在行業內享有較高聲譽。2013年藍珀作品《五方財神(五件套)》榮獲中國琥珀雕刻設計大賽“匠心杯”金獎;2013年琥珀作品《禪》榮獲中國瑞麗第六屆“神工獎”玉雕大賽銅獎;2018年藍珀作品《五方財神(五件套)》榮獲中國玉石雕刻作品“天工獎”銅獎;2013年琥珀作品《萬象更新》榮獲中國琥珀雕刻設計大賽“匠心杯”銀獎。
(編輯:李博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