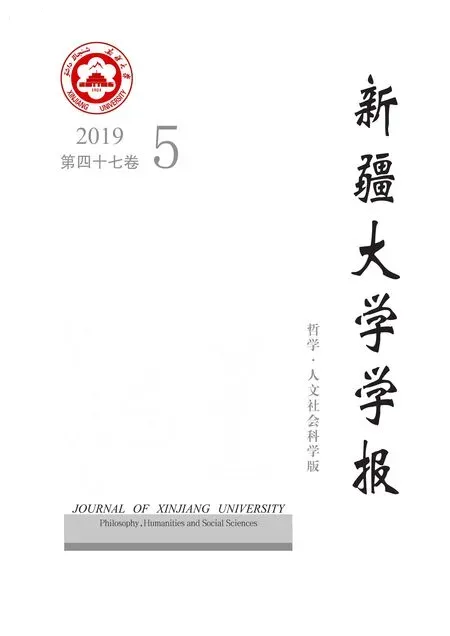伊恩·麥克尤恩小說《黑犬》中的歐洲危機和復調敘事*
王麗云,劉 巍,于麗萍
(1.遼寧大學公共基礎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2.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在當代的英國文壇,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1948-)與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和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齊名,是英國當代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不僅如此,批評界還常把他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相提并論,因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專注于探討人的本性問題,而且都善于將這個抽象的哲學命題在孩子身上具象化。1978年,伊恩·麥克尤恩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最后的儀式》出版,引起巨大反響,伊恩·麥克尤恩更是藉此被評論界視為貝克特和卡夫卡的文學繼承人。1992年,伊恩·麥克尤恩的小說《黑犬》出版,這是一部繼承了英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黑色幽默的哲學寓言。在英國文學的歷史進程上,伊恩·麥克尤恩承繼了英國文學的傳統,對英國小說在當代的復蘇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黑犬》涉及了宏大的社會主題:戰爭和文化(文化是相對于政治、經濟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活動產品)。麥克尤恩先是架構了一個回憶錄式的框架,然后采用復調敘事從不同的視點切入,多角度展示戰爭和文化問題。小說由前言和四個各自獨立的主體組成。在前言部分里,敘述者杰里米回憶自己的成長過程,構建了小說主要聲部的發聲者杰里米的形象,自然地引出了小說的主題。換句話說,前言向讀者交代了一個懷疑論者或者說一個無信仰主義者的生成過程,然后,引導讀者跟著這個無信仰主義者去探尋黑犬事件真相,從個體的思想變化切入,展示歐洲文化根基——思想體系的嬗變。在故事主體的第一部分里,作者是以事件親歷者之一瓊的視角描述黑犬事件;第二、三部分,從無神論者伯納德的視角敘述事件;第四部,以第三人稱的視角,盡量客觀地、完整地敘述黑犬事件。
小說通過描寫一對夫婦的見聞和親身經歷將歷史事件融入小說之中,呈現歐洲戰后動蕩黑暗的局面,探討戰爭陰影依舊在歐洲籠罩的原因,解讀歷史對現在和未來的啟示。在結構和人物設置上,小說中最突出的特點是:作者努力讓三個主要人物脫離自己而存在,成為表現本人思想立場而存在的主體,其在文本中的話語也不僅僅局限于表現其性格特征和推動情節的發展,而是一種他者的、非作者意識的、具有完整思想觀念的主體話語。此外,三個主要人物分別代表了二戰后歐洲的三種思想體系:伯納德的無神論、瓊的有神論和杰里米的懷疑論。在追尋黑犬真相的這個統一的事件中,三種思想體系不斷碰撞,展現出歐洲思想形態的分裂和坍塌。為了更好地表現這一點,伊恩·麥克尤恩在小說《黑犬》中,不僅是設立了三個不同的人物代表不同的思想,而且成功地借用了前蘇聯文藝學家巴赫金的復調式敘事手法。所謂復調式敘事,是與獨白式敘事相對而言。獨白式敘事是把多種性格和命運根據作家的統一意識在作品中分別展開,而復調敘事“是把多個價值相等的獨立意識以及其各自代表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中”[1]。換言之,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僅是作家所敘述的客體,更是直抒己見的主體。為了真實地反映現實,保證文本的客觀性,伊恩·麥克尤恩在文本中復現了生活本身的對話關系,減弱作者的主觀性,讓主要人物實現自我意識的獨立。《黑犬》之所以被稱為復調小說,就是因為它真正地實現了人物自我意識的獨立。伊恩·麥克尤恩讓每一個人物都具有充分完整的思想觀念,并且都各自在小說里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一、多聲部才是人類真正的生存形態
在獨白式小說中,人物僅是作家描寫的對象或客體,是為表現作者的思想觀念或感悟而設計的。但是在復調小說中,人物雖然是來源于作者的創作,但卻不是為服務于作者的思想而生,是有別于作者的另一種思想觀念和世界,是自己觀念的主體,是不依附于作者的獨立存在。在《黑犬》這部小說中,伊恩·麥克尤恩沒有刻意表現自己本人的統一意識,因此每個人物都是獨立的,具有同等的地位。小說的這個明顯特征具體表現在兩點:其一是主要人物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思想體系和世界觀;其二是主要人物之間是平等的對話關系,不分先后和優劣。因此,《黑犬》是屬于典型的復調式小說。
《黑犬》中最先出場的杰里米是一個無信仰主義者,是對話關系的核心人物,代表作者同另外兩個主要人物展開對話。對話的內容表面上是在探究黑犬是否真實存在,實際上是無信仰主義者分別同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針對文明出路問題在各抒己見。
杰里米這個人物角色的設置是非常成功的,在文本中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是個內視角式的人物存在。法國的著名文學理論家、歷史學家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 1939—)認為:“敘事作品的敘述視角分成三種:全知視角(零視角)、內視角和外視角。”[2]外視角多用于偵探類型的小說,敘述者由事件的旁觀者充當;全知視角,即全知全能的作家向說書人一樣出現在文本的背后進行講解,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全知全能,掌控一切。在《黑犬》中,杰里米一身二任,既作為人物之一進入故事和場景,又充當敘事者講述親歷的事件或轉敘見聞。所以,杰里米是讀者能夠借助的內視角,他的視覺、聽覺以及感受都是為了幫助讀者領略事件的全過程。不僅如此,杰里米還是整個復調中的一個獨立聲部。他以寫回憶錄的目的,與故事中的人物形成一種對話關系,是整部小說的復調式敘事得以確立的關鍵。
杰里米是懷疑論者也可以說是無信仰主義者的代表。失去雙親的孤兒杰里米,成長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歐洲,面對喧鬧、動蕩、充斥著各種理論,卻又思想信仰崩塌的矛盾年代,他在迷茫和失落中掙扎,并且以各種方式填補心靈的空虛。在《黑犬》的第二部分里,杰里米常常去拜訪身患絕癥、囚困于療養院中無處可去的瓊。通過杰里米與瓊的對話,以及杰里米的觀察和分析,作者呈現給讀者的信息是:瓊的人生和容貌都偏離了預定的發展軌道,用容貌變化暗喻信仰的變化,即從最初的無神論者變成了有神論者。第二、三部分是杰里米同伯納德的對話。同樣,讀者再次透過杰里米的視角看到黑犬事件在伯納德身上的影響。伯納德的信仰如同他的臉一樣,整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調整:他雖然在蘇聯入侵匈牙利時退出了原來的組織,但是他仍然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
《黑犬》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有“獨立的意識”,代表一個獨立的思想觀念體系。但是如果僅僅是賦予人物獨立的思想,那也只能是一般的心理小說。《黑犬》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它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的小說一樣,給三個人物的獨立意識構建一種平等的關系,允許它們有充分的自由空間去表述其合理性,而不強加任何來自于作者的價值判斷。在獨白式小說中,作家把某一社會生活側面進行詩性的重塑,營造出假定的情境,表現自己的主觀褒貶態度。因此,作家勢必讓文本中所有人物的語言和行動都按照一個統一的、既定的脈絡去展開,以使最后的結尾看起來順理成章。這樣的小說常被詬病為是武斷地凌駕于文本接受者之上的一家之言。與此不同,《黑犬》的是開放式的,沒有依據作者的意志形成固定的結論,只是有三個獨立聲部圍繞黑犬的真相形成一種復調式的和聲。但是,這幾個獨立聲部的存在,終極目標不是為了從多個角度去探討黑犬事件的真相,而是為了展現人類真正的生存方式,即對話性。這種對話性,有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微對話和大對話。首先,人類思維是“微對話”。“人類思維的本質是對話性的。”[3]思維的對話性體現在兩點:其一,人物內心的矛盾,具體體現在分裂的人格或者雙重人格之間的對話;其二,在內心中與一個對立的話語即他人的意識進行對話。其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大對話”。“生活本身也是一種對話的關系,常常是不同的聲音各自不同地唱著同一個題目。”[4]一個人的“言談”是其觀點和價值觀的外向性表達,并且和他者的“言談”一同構建出話語的公共空間。在真實的世界中,并不會存在獨白小說中常有的某一方的最終勝利,而是多元無限期并存的現象。所以,這樣的復調式敘事方式才是表現人類真實生存狀態的最佳載體。
二、歐洲戰后的文化危機
三個主要人物在自我意識上的獨立,目的是為如實復現歐洲戰后的文化中的思想信仰分化現象。二戰史無前例的殺戮和暴行給人類留下了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而且戰后物質生活的匱乏更加劇了精神上的痛苦。戰爭帶來的死亡、貧窮和饑荒等,將人們拋入嚴重的生存危機和思想信仰危機之中,于是一切傳統的道德和秩序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思想體系領域里的危機會直接反映在文化領域里。德國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于戰爭期間創作的《西方的沒落》在戰后的歐洲引發了一股銷售熱潮,這個文學領域里的事件就標志著歐洲人的思想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西方的沒落》能夠熱銷,說明整個歐洲因發達的物質文明而累積起來的優越感已經發生動搖,對曾經引以為傲的文明產生了深刻的懷疑。斯賓格勒認為:“每一種形態的文化就象一株花,一棵樹那樣,都走不出從發生、成熟到衰落的宿命,歐洲正在走向沒落。”[5]戰后的歐洲人對此深信不疑,于是歐洲人開始認真地反思和尋覓自我救贖之路,各種思潮和主張紛至沓來,層出不窮。在眾多的救贖理論中,最突出的是理性主義和神秘宗教主義。
從歐洲文化心態的發展來看,兩次世界大戰前的主流思想體系非宗教莫屬,雖然其宗教流派五花八門,但是究其根本是有神論思想。隨后,啟蒙運動帶來的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技術進步,逐漸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話。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反基督教主流話語方向的作品,表現人類遠離宗教,投入理性和科學的懷抱,并將其認定為發展文明的捷徑。然而理性思維和科技進步不僅僅給人們帶來了生活的便利和物質的富足,更是帶來了殘酷的殺戮,讓人類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于是,理性主義構建的信仰體系搖搖欲墜。“理性主義王國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反人性的,那么退回到非理性之中似乎成了可選擇的一種途徑。”[6]于是,非理性主義思潮再次登上舞臺,歐洲大陸墜入了神秘主義和理性主義相互傾軋的漩渦。
麥克尤恩在《黑犬》中用伯納德和瓊在個人信仰上的沖突,指射歐洲意識形態領域里神秘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立。伯納德和瓊在青年時期都對人生、革命和愛情充滿熱情和期待,但是隨著兩人政治信仰的日漸分化,婚姻最終名存實亡。伯納德雖然崇尚邏輯和理性,堅定地信仰唯物主義,但是在1950年退出了理性主義組織。伯納德的行為影射的是歐洲人的理性主義崇拜遭遇危機的事實,“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滅了”[7]45。理性主義強調極端的理智,認為理智可以排除人類行為上的沖動和感情用事等非理性因素,能夠帶來和平、公正、幸福和無盡的創造力。但是,理性主義主導的技術霸權和民主政治沒能阻止世界大戰的殺戮。于是,歐洲人對理性主義信仰提出了質疑,曾經堅定的理性主義者伯納德動搖了。
瓊代表的是神秘主義信仰。她在青年時期是一個無神論者,在遭遇黑犬之后,開始信仰神秘主義。瓊的變化其實是源于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不解。在目睹了戰爭給歐洲帶來的創傷以及戰后歐洲共產主義的極權政治等,歐洲人對倡導科學技術的理性產生了懷疑和否定,轉向內心尋找答案,瓊是這一類人的代表。她發現理性主義高舉的科技和進步大旗沒能如期地帶來幸福和和平,“即使人人都擁有免費醫療和無所不包的家用電器,可他們還是感到不滿足”[7]42。瓊堅定地認為理性主義倡導的技術進步只能帶來物質的富足,但不足以解釋和驅逐深藏于人類心底的邪惡,所以必須實現一場心靈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瓊的神秘主義信仰既不是傳統的宗教信仰,也不是伯納德所說的非理性,而是對現實生活和人性本質的重新認識。柏格森曾說:“當代的神秘主義并不是非理性,它是理性的補充,是理性中未被發現、未被探測到的一部分。”[8]理性主義信仰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神秘主義雖然源于宗教,但是卻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逐漸成為宗教和哲學的綜合體,把人和神的關系作為道德修養的核心,關注人的心靈、能力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力圖從一個新的角度,更加準確地解釋生命和世界。
受戰爭影響的第一代人是瓊和伯納德。他們在價值上的分野和信仰上的沖突不僅讓這一代人彼此疏遠,同時讓他們的后代在信仰上無所適從,而最終成為無信仰主義者。杰里米就是無信仰主義者的代表。他說:“我沒有任何信仰,……因為我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或者一條持久的準則,……也沒有找到一種能讓我信奉的超驗存在。”[7]36
社會意識形態和信仰是個人身份和心靈的標志,歷史重大事件總是會不可避免地入侵并改變著個人生活。麥克尤恩反其道而行之,用三個獨立的個體把整個歐洲的信仰分裂具象化了。不難看出,在信仰的分化上,戰爭是關鍵的觸發因素。面對戰爭帶來的災難,走出中世紀宗教思想的桎梏并投入到理性主義懷抱的歐洲人中,堅定如伯納德一類,雖然在思想上出現了困惑和動搖,但選擇停留在原地,尋找各種方法為理性主義辯護;本就不堅定的理性主義者,如瓊一類,則投入到了神秘主義的懷抱;背負父輩思想的沉重負擔,如杰里米一類的年輕人,面對對立的思想與觀念,只能是一個質疑一切的無信仰主義者了。麥克尤恩用文學手法書寫歷史,成功梳理了歐洲戰后的各種思潮和信仰以及他們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態度。
麥克尤恩把傳統線性敘事立體化,模糊歷史和現實的界限,精準傳達二戰后歐洲的精神恐慌與焦慮。換句話說,麥克尤恩精心架構了一個復調敘事的框架,用幾個獨立的聲調代表地位平等的意識以及它們各自代表的世界,展現了歐洲戰后意識形態的分化。麥克尤恩借杰里米之口感嘆:“我不能確定,這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是因為有像伯納德和瓊這樣的人,還是因為有像我這樣的人才遭受禍端。”[7]45究竟是伯納德信仰的理性主義,還是瓊崇拜的神秘主義,哪一個能使人類文明免受戰火涂炭?麥克尤恩沒有在作品的最后給出結論。《黑犬》中提出的很多問題都沒有最終答案。可見,作者的目的是呈現矛盾。在《黑犬》這部作品中,麥克尤恩采用了多個獨立主體平等對話的模式,巧妙利用人物設計和情節安排,展現自己在信仰方面的困惑和無所適從。或者說,伯納德、瓊和杰里米只是作者割裂的靈魂的代表,是麥克尤恩讓自己的多個人格進行了一場對話。這場對話目的不在于給出答案,而在于展現整個歐洲思想體系方面的嬗變:從對傳統信仰的質疑到思想體系的徹底崩塌,最后到現代人在信仰上的無所依從。
三、復調敘事是呈現思想體系崩塌混亂的最好載體
在后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人類活動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圭臬,并為此而互相傾軋,與《圣經》所宣揚的博愛產生沖突,人的信仰根基開始動搖。原本堅如磐石的基督教世界里的思想體系出現分裂,導致歐洲人在自我意識和潛意識中,出現割裂的、矛盾的和多重的構造。就麥克尤恩個人而言,其思想意識也是割裂的和矛盾的。在麥克尤恩的生活歷程中,曾經有多種思想體系粉墨登場。他出生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幼年時期因父親的工作調動而輾轉于多個海外的海軍基地,因此接觸到異域的文化和思想。成年后,他與一個神秘主義先驗論者結為夫妻,又開始接觸神秘主義思想。他本人曾經投身于反文化運動,但是后來對反理性主義的文化運動感到厭倦,開始接受理性主義思想。經歷了自身思想變化的作家去表現一個思想多元的時代,是最順理成章的事情。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為這個思想多元化的時代意識表征找到一個合適的文學載體。經過反復嘗試,麥克尤恩最終選擇了對話式的復調。
復調的概念本來是屬于音樂領域的,指相關但卻不盡相同的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聲部同時進行,使音樂形象更加豐富,氣勢更加立體,造成震撼的聽覺效果。復調敘事的具體理論來自于后現代的音樂,所以二者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二者的最高美學追求都不是要呈現和諧統一,而是要呈現多元和矛盾。單就這一點而論,復調就比獨白更加適合當下的多元化時代表征。
獨白式小說是“作者對生活的詩性重塑,有加工過度之嫌,無法表現出生活的真實狀態。獨白式小說是作家固有的對世界的根深蒂固的原則性態度,是一種觀念上的整合和建構”[9]。獨白式作家是把人類救贖看成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借文學言說人與世界的關系,圍繞自己的理念塑造角色。這樣做的結果是:人物雖然也在說話,但他們的聲音和意志經過作者意志的過濾,成為作者意志的傳聲器,因此不契合多種理念并存的時代意識表征。
復調重在多元和矛盾,獨白重在統一和歸化。首先,復調小說與獨白式小說最大的差異是:獨白小說的重點是人物和情節,通過描寫人物和情節來賦予小說一定的思想性,而復調小說的重點是思想本身。“復調小說是在一個平面的、共時的結構中考量各個意識之間的聯系和差異。故事中的人物以自己的意志、生活模式和標準去追求屬于自己的個體主體意識的存在方式。”[10]就《黑犬》而言,麥克尤恩用三個人物作為三個不同思想體系的具象化代表,又用杰里米的敘述交代人物背景。三個人物的背景分別代表著三種思想體系的生成過程。其次,獨白式小說的結尾是終結式的,由作者給出一個預設性結論。復調式小說的結尾具有未完成性特質,是開放式的。就《黑犬》而言,麥克尤恩沒有給文本中對立的信仰一個孰優孰劣式的結局,對立的局面不會因為某一人物的退場而終結,例如瓊的死并不意味著她代表的神秘主義的終結。麥克尤恩在《黑犬》中提出的很多問題都沒有答案,一切就如生活本身一樣,都只是過程。
在工業時代里,人類活動都以利益和金錢為動力,曾給歐洲文明發展提供精神支柱的《圣經》不能再像以往那樣慰藉人類疲憊的心靈,人的信仰根基不像以往那樣統一和堅定,分裂在所難免。在人類自我意識和潛意識中出現的多重構造,已經不適用于古典美學中的單一旋律(獨白式敘事作品),因為它無法描繪現代人割裂的靈魂。《黑犬》為現實里多樣化的意識和聲音,搭建了發言和交匯的場地,這是獨白小說做不到的,因為獨白小說不給他人話語任何語義空間。綜上所述,當下是一個價值多元、觀點多元、體驗多元的豐富而又真實的世界,復調小說的對話性、矛盾性和未完成性契合了這個世界的多元性狀態,是呈現分化格局的最好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