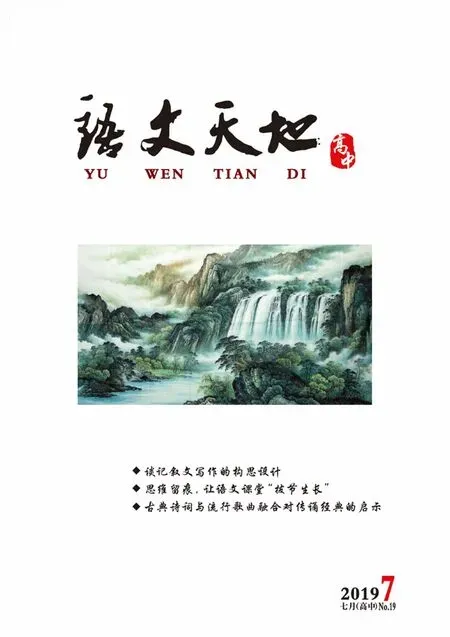高中文言文誦讀法探究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出:“通過閱讀和鑒賞,深化熱愛祖國語文的感情,體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養。”讓學生多讀文言詩文,不但可以開闊視野、增長知識、陶冶情操,而且能拓展知識面,全面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文言文是高中語文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編者的本意是希望學生能夠通過誦讀欣賞這些經典的篇目感受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可是,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往往從應試方面去考慮,把一篇篇字字珠璣的美文分解為支離破碎的知識點和名句填空,名篇的藝術價值、審美價值、人文價值蕩然無存。
談到古文誦讀,南宋朱熹的看法是:“要讀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要多誦數遍,自然上口,久遠不忘。”清代曾國藩也曾說:“非高聲朗讀則不能展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可見,古人是很看重誦讀的。蘇教版高中語文必修課本、《〈史記〉選讀》、《論孟選讀》、《唐宋八大家散文選讀》精選了大量的文言篇章,為學生打開了一座流光溢彩的詩文殿堂。教師應該指導學生通過誦讀古典文言名篇,感受獨有的韻味美和意境美,提高閱讀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從而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一讀:練語感、明句讀
所謂語感,就是學生對于語言的感受能力。這種感受能力的獲得不依賴于理性的邏輯思維,它的產生依靠的是聽說讀寫練。《指南錄后序》中有這樣一句話:“縉紳、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閱讀時,學生受“縉紳、大夫”兩個雙音節詞的影響,將“士”和“萃”兩個字連讀,認為也是一個雙音節詞。面對這樣的錯誤,我沒有選擇傳統的教法,直接從語法上講解,而是讓學生先自己進行自由地誦讀,十幾遍誦讀之后學生慢慢就有了語感,句法結構也就一目了然了。在此句中“士”為主語,“萃”為謂語,兩者是不能連讀的。誦讀培養了學生良好的語感,教師也不必花大量精力去講解枯燥的語法知識,文言課堂亦變得有趣味了。
二讀:理結構,析內容
理解了實詞、虛詞、成語典故、句法結構等文言基礎知識后,就要對作品的內容進行分析。俗話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古人的金玉良言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通過多種形式的誦讀可以幫助學生較為快速準確地把握內容。在教授《漁父》時,因為文本是“對話體”,我就讓學生分小組、分角色多次進行文本的誦讀。這種代入式的情境誦讀讓學生很快理解了文章的內容,文章其實就是講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的取舍,屈原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漁父是“與時推移,明哲保身”。避開大量無味的字詞句段的分析概括,在讀中整體把握住文章的主要內容,我們的文言課堂不再是條條框框,支離破碎。
三讀:品意境,悟情感
意境是作者的主觀的生命情調和客觀的自然景色互相滲透、互相交融而成的藝術境界。古詩文著意追求意境。學生在多種形式的誦讀中,可以放飛想象,還原畫面,進入意境,體味作者情致,獲得強烈的審美感受。
在教授《蜀道難》時,我帶領學生配樂朗讀,讓學生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段落自由誦讀,感受蜀道之高、險,蜀地之亂。其中有這樣一段,學生都非常喜歡。“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簡單的技巧指點之后,在低沉的音樂聲中師生合上課本閉上眼睛輕聲誦讀,放飛自己的思緒,將文字轉化成有聲有色的畫面。這樣的誦讀方式讓學生感同身受,他們感受到了蜀道上的那種凄清、空寂、蒼涼的氛圍。又如《滕王閣序》中的千古佳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通過誦讀,學生不僅能夠欣賞到一幅色彩協調、動靜搭配的美妙絕倫的圖畫,還能神游在一方澄澈、空明的天地之中。在誦讀過程中,學生的審美體驗不斷得到強化。
在教授蘇軾《定風波》時,詳細地了解了蘇軾的人生經歷和回憶了《赤壁賦》等作品后,學生再次誦讀全詞,認為這首詞表達了蘇軾在挫折面前不退縮的曠達,視榮辱沉浮如煙云的瀟灑。如“吟嘯徐行”四個字,就有學生說再大的風雨聲也沒有打亂作者既定的步伐,照樣吟嘯徐行,作者在這里真正要抒寫的是這樣一種感受:面對政治上的腥風血雨我都寵辱不驚,自然界中的這點小風小雨又能算什么呢?寫作此詩時作者被貶黃州已經三年,與剛到黃州時心態已經大不相同,少了一份迷惘、哀嘆,多了一份從容、淡定。又如“一蓑煙雨任平生”的“任”字,學生也讀出了豐富的意蘊。一個“任”字,既能讓作為讀者的我們感到披蓑戴笠、煙雨蒙蒙,體會到那種漁樵江渚之上的逍遙愜意;又寫出了任風雨漫天,我自巋然不動的瀟灑鎮靜。這樣的領悟在誦讀中水到渠成。而這些誦讀得來的情感體驗,撩撥了“美”的神經,讓學生領悟到了文言詩文的魅力。
當然,僅憑誦讀是不行的,也要輔以其他的一些教學手段。例如,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技術,播放音頻、視頻等,給學生的閱讀營造一個情境,讓學生能夠在適當的情境中走入文本,這樣才能更好地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效果。總而言之,我們要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讀起來,動起來,這樣才能真正讓他們學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