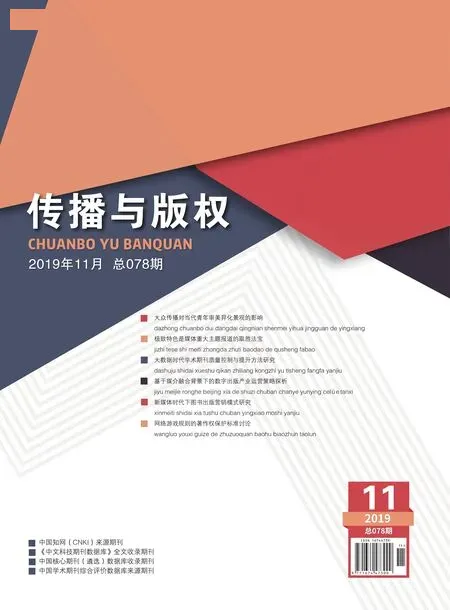民族體育活動的舉辦和傳播對民族交往交流的作用
——以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為例
馬曉軍
(河南大學民族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1)
不同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這些文化通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民族傳統體育活動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表達形式。民族傳統體育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的文體娛樂方式,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形成后往往通過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傳播到其他地區。現代社會通過舉辦民族運動會,能夠迅速、有效地促進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間交流、傳播。
我國56個民族形成了一些各具特點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通過舉辦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可以利用以人為載體和以文本與圖像為載體的民族體育文化傳播方式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實現民族大團結的目標。
一、全國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發展歷程
1953年11月8日至12日舉行了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當時名稱為“全國民族形式體育表演及競賽大會”),滿族、蒙古族等13個民族395名運動員參加了這次運動會,來自全國各地及天津觀看競賽和表演的觀眾超過12萬人次。
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閉幕后,由于種種原因,直到1982年9月才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舉辦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此后,基本上每隔四年舉行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
2019年9月8日至16日,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在河南省鄭州市舉行,全國31個省(區、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臺灣少數民族組成34個代表團參會,55個少數民族7009名運動員參賽(集體比賽項目有一小部分漢族運動員參與)。
二、以人為載體直接傳播民族體育文化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通過競技性或者表演性的體育活動展示出來,參與比賽的運動員、裁判員、教練員用他們的拼搏與汗水直接傳播民族體育文化。
(一)各民族運動員積極互動
1953年11月舉行的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只有13個民族395名運動員參加,隨著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規模的不斷擴大,運動員的數量成倍增長。2007年第八屆、2011年第九屆、2015年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運動員人數均超過6000人,他們以運動會作為民族體育文化傳播的平臺,以各自的代表性項目展開互動交流。參加2019年第十一屆全國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西藏代表團押加運動員羅松西繞說:“押加本來是發源于西藏的民間傳統體育項目,現在推廣到了全國,成為人們了解西藏的一個窗口。”他還說:“賽前賽后,我們各地運動員在一起交流,從押加技術講到生活習俗,我們逐漸成為朋友。”[1]
(二)不同民族裁判員、教練員頻繁交流
由于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規模持續擴大,裁判員和教練員的數量也不斷增長。1953年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裁判員只有340人,1999年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裁判員達到720名,2007年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裁判員猛增到900名。[2]與此同時,教練員數量也同樣伴隨著運動員數量的迅速增長而增加。在運動會舉行前和舉行期間,各個代表團內部和不同代表團之間的裁判員和教練員為了提高比賽成績,他們積極討論專業知識,互相交流訓練技巧。西藏代表團藏族傳統體育項目“打牛角”教練員羅布次旺說:“56個民族都來了,開闊了眼界,結識了陜西、寧夏等地的朋友,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表演各具特色,各有千秋。”[3]
三、以文本與圖像為載體間接傳播民族體育文化
體育活動具有即時性,體育文化交流和傳播受時間和空間的制約。但是,依靠以文字為傳播手段的文本和現代的圖像保存與傳輸技術,體育活動可以擺脫時空限制以新聞報道、廣播電視以及各類新媒體等形式間接傳播。
(一)新聞報道傳播民族體育文化
1953年11月9日,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開幕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民族形式體育表演及競賽大會在天津開幕》為題進行報道,在比賽過程中和比賽結束后《人民日報》又多次向全國各界民眾報道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在后來每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舉辦期間,《人民日報》均大力報道。1991年,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舉辦前后,《人民日報》報道數量高達40篇。[4]以舉辦地為主的地方報刊也大力報道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2015年,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舉辦前后,《內蒙古日報》和《鄂爾多斯日報》發表關于賽事的報道合計418篇。[5]這些新聞報道將民族體育文化傳播到賽場之外的各族讀者之中。
(二)電視與新媒體傳播民族體育文化
從20世紀80年代電視機進入中國家庭后,電視成為信息傳播的一條主要渠道。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舉辦期間,中央電視臺、廣東電視臺等媒體對11個比賽項目進行了現場直播。[6]2011年,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中文國際頻道和英語頻道首次對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開幕式現場全程轉播,綜合收視率高達1.44%,海內外約1.3億人次收看。[7]在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舉行期間,舉辦方利用官方網站、微博、論壇、手機報等新型媒體及時迅速發布賽事新聞,使各類比賽能夠以不同傳播方式為各族觀眾所了解。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組委會逐漸加大以手機作為傳播工具的各類新媒體的利用力度,使手機成為繼電視后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的重要傳播途徑。
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功能
民族傳統體育活動通過人與人面對面近距離的互動和利用媒體跨越時空遠距離交流能夠促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有益于各民族團結,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促進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
在民族傳統體育活動舉行過程中,各民族運動員、裁判員、教練員以運動會為平臺展開了頻繁的互動交流,促進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一些省(區、市)為了豐富參賽項目,從其他地區引進參賽項目,加強了民族體育項目的交流。南方少數民族流行的陀螺、高腳競速、板鞋競速和藏族的押加、蒙古族的摔跤都逐漸被其他一些民族通過互相學習而掌握。參賽項目的交流產生了間接的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效果。寧夏利用主辦2003年第七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契機提前從南方引進了“龍舟”項目,比賽結束后,在銀川沙湖修建的“龍舟”賽場成為一項旅游項目,游客可以劃龍舟、騎駱駝、滑沙,江南水鄉與大漠風光融為一體的獨特景觀吸引了眾多的各族游客前來觀光。2007年,云南省代表團在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上的獲獎項目被邀請到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表演,得到無數觀眾的好評。這些項目很快被推廣到云南一些旅游景點,吸引了許多慕名而來的各族游客。
(二)民族傳統體育活動有益于各民族團結
1991年,臺灣少數民族代表團沖破重重阻力首次參加了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他們的愛國之舉和精彩表演贏得了各族民眾的贊許和歡迎,臺灣各族代表更加堅定了海峽兩岸各族人民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從此以后,臺灣少數民族代表團一直參加每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賽場內外給兩岸各族人民創造了很多交流機會,加強了相互了解,增強了民族團結的信心。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臺灣代表團運動員馬文揚說:“在開幕式入場的那一刻,全場歡呼,我眼眶立馬就濕了,這是回家的感覺,那一刻,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和我的祖國,一刻都不能分割。”[8]參加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臺灣代表團團長、中華海峽兩岸原住民暨少數民族交流協會理事長華加志面對媒體說:“我們希望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有一天能在臺灣舉辦。”[9]這些話語表達了他們對民族團結的感動和臺灣各族人民渴望實現民族大團結的心愿。
(三)民族傳統體育活動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在各地輪流舉辦有助于鞏固中華民族意識。第一屆至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先后在天津、呼和浩特、烏魯木齊、南寧、昆明、北京(拉薩)、銀川、廣州、貴陽、鄂爾多斯、鄭州舉辦,這些城市分布在10個省(區、市)、遍及大半個中國,通過各地不同民族相互協調、共同行動,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每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設計的會徽都蘊含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寓意,體現“中國各民族的運動會”理念。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會徽將變形的阿拉伯數字“5”和“6”巧妙組合成數字“8”,用文化符號表達出56個民族團結一致的信念。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將《愛我中華》確定為會歌,“56個民族56枝花,56個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歌詞成為各族人民維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真切心愿。
總之,在民族體育活動中,運動員、裁判員、教練員通過比賽項目直接傳播民族體育文化,電視與新媒體以文本和圖像為載體間接傳播民族體育文化,民族體育活動的舉辦和傳播能夠促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有益于各民族團結,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