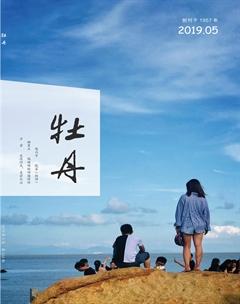英美文學作品中的“自然”觀對當代大學生人文情懷的影響研究
袁漫琳 李前
盧梭和華茲華斯均為生態(tài)作家的杰出代表,兩人在人生的黃金之年逃離俗世的紛擾,居住于心中的桃花源,領略文學的真諦。他們的作品飽含了對自然、對于自我、對兩者和諧的追求。新時代,大學生在人文情懷的滋養(yǎng)下,對于出世與入世、屈原與漁夫、孑然堅守與隨波逐流這類選擇的問題,似乎依然迷茫。大多還是選擇了后者,做一個適應這個浮躁社會的漁夫。這兩位作家對于如何打理心中的花園,怎樣重歸心靈的充實與寧靜,站在人文關懷的角度給了大學生不一樣的思考方式。
一、生態(tài)整體觀
生態(tài)整體觀是指關系到所有的生物,以最全面的角度來看待自然問題的方式。為了解決生態(tài)危機,人們應該考慮到所有方面,以最全面的角度提出有利于生態(tài)的策略,多贏角度解決問題。在《1815年九月》中,華茲華斯提到“海低聲耳語,喚起素靜無華的鳥雀,你們的大敵逼近了要筑好雀巢,加強防護”。這里闡述了鳥與寒冬之間的抗爭,然而這種爭斗和人與自然的斗爭不一樣,前者不會對生態(tài)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傷害,后者卻能摧毀生態(tài)建構。《瓦爾登湖》里有“鋪了石子,沿湖種了松樹,他告訴我舊時的和新近的故事”,石子、湖、樹、人,四個單獨的個體場景融合成了一幅畫。如若將四個場景比喻成元素,那么生物圈則是集合,無數的元素構成了這個集合。如果集合出現了問題,其整個子集都會受到影響。在這一理念下,面對生態(tài)問題,要從各個元素、小處看起,才能構建正確的集合,解決問題。整體的和諧是生態(tài)的最終要義,也是人類和諧的本源。只從對人類有益的視角看待生態(tài)問題是極其不成熟的,要結合自然整體觀,縱覽全局。除此之外,人類作為生物圈的特殊一環(huán),大學生應該有這樣的使命感,人們有義務承擔構建一個更好、更穩(wěn)定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責任,而不是擁有改變世界的能力,卻做著催生自我毀滅這樣愚蠢的事情。
二、重歸自然的懷抱
人類長久以來認為自己是萬物的主人,堅守著自然是敵的思想,受貪婪的欲望所支配,讓自然資源變得緊缺,生態(tài)修復能力重創(chuàng),同時自身也難以得到片刻平靜的心靈。這一思想在華茲華斯的詩歌中主要體現在和動物生靈的交談之間,在盧梭作品里體現在對簡單生活的推崇。
《致公雞》里,華茲華斯說到,雞叫聲的韻律讓他重返自然。“O blithe New-comer!I have heard, I have thee and rejoice.”這種愉悅讓遠離自然的人無法觸及。在詩尾,作者細述了這一歡愉,感謝這自然之聲,讓他躺在草地上冥想,與過去的美好時光邂逅,探索真我。《致云雀》里,他感謝云雀給他了思想的空間和靈感創(chuàng)作,掛念帶他逃離紛繁大世界的小雛菊,哪怕是在路邊巧遇的一片水仙花,也是自然的信使,威斯敏斯特橋下奔流的河水亦為自然的靈媒,它們都在傳達著自然的信息。《約翰》里的那個智力缺陷的男孩,被森林里的大瀑布的美所吸引,不被別人理解。但是,約翰屏蔽了一切外在的紛擾,遵從了自然的感召。
《瓦爾登湖》中,盧梭貶低了人的物欲無意義論,文明人用生命追逐奔波的結果也只是回歸黃土作繭自縛,那么野蠻人終其一生追逐食物以及安身之地也是徒勞,兩者并沒有區(qū)別。他比較了文明人和野蠻人的生活,呼吁人們回歸自然的懷抱,崇尚至簡生活。在建造房子的問題上,他對比了人富麗堂皇的居所和烏龜、杜鵑等動物的巢穴,總結到“只有居住者才是獨一無二的建筑師——它來自不知不覺的真實與高貴”,再次體現了對簡單生活的推崇。
大多數人都被外在的無形之手所局限,聽不見心靈的聲音。然而,在如今這樣一個心理世界匱乏的社會下,大學生是否應該去追求那些虛無縹緲的繁榮呢?有人賣腎為了去買蘋果牌的手機,有為了淘寶的高端購物而借裸貸無法歸還,有為了追星追名牌逼得家破人亡的,在不良的風氣之下,是否應該想想幸福生活的本質為何?兩位作家給出了答案,重返自然。
三、自然即我,我即自然
人們從安逸中醒過來,意識到應該回歸自然,回歸只是第一步,然而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可以更進一步,即與自然融為一體,自然即我,我即自然。在《她住在人跡罕到的路邊》這部作品里,讀者為描述的美麗、寂靜的場景所深深吸引,印象最深的是卻是那個已經回歸自然,長眠于泥土,再無紛擾的蘇格蘭小女孩。作者是這樣描述的,“活著時誰知道她在人間,更有誰知道她夭亡”。露西活著的時候,摒棄了外在紛擾,外在的嘈雜都不曾影響到她半分,因為她的心和一朵半隱半現的紫羅藍,和長青苔的石,和野鴿泉,和自然在一起,離開時就像樹損草枯、葉落花謝一樣自然,無悲無傷。她融入了泥土,和自然融為一體。
《康科德與梅里馬克河》中,盧梭記錄了他的歷程以及感悟,里面有成群的游魚,亦有蒼翠的藤本植物,有屠殺河鯡以求富有的商人,亦有不緊不慢播豆子怡然自得的人。其中寫道:“什么是生命?驕傲的夏日草地。華麗的盛裝,今朝,穿著她綠色的長毛絨,明天成為干草。”這是草地的歸宿,又何嘗不是人的歸宿,什么如曇花一現,最終歸落于黃土之中。生命,隨著斗轉星移、花謝花開,即使海枯石爛,也永不磨滅。生命達到了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最高境界。當自然即我、我即自然的境界達成,軀體的存在便不再重要了,整個世界都會擁抱你,一花一草一樹一木,而你即是世界。人都有經歷快樂苦痛共存的生活,最終的歸宿必然是魂歸黃土,與自然融合,這亦是人最終的存在形式。大學生應該認識到“人就是自然,自然即是人”的思想,善待自然,即是善待自己,在紛擾的生活中堅守靜地。
四、結語
本文從自然和人類的兩個方面著手整體分析,自然是一個整體,人類作為特殊的食物鏈的一環(huán),應該首先建立意識保護生態(tài),在維護生態(tài)平衡上做出積極的貢獻。先有了這個基礎意識,再以遞進的形式,從初階的重歸自然意識到最高形式,與自然融合。但是,只擁有這樣的回歸意識,無法解決人們已經造成的嚴重生態(tài)問題,因此華茲華斯和盧梭的作品里中透露出與自然相融的思想,這也是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終極方法,只有擁有自然即我、我即自然的思想,人們才會真正警覺,行動起來。兩位文學界的引導者不僅僅是文學家,更是在作品中運用生態(tài)觀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保護生態(tài)的斗士,他們像一盞明燈,從人文角度給出大學生答案,使其明白應該追求何種生活,如何調整內在與外在的和諧,如何看待人與自然,培養(yǎng)了大學生的時代使命感。
(湖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北師范大學“英國研究中心”資助項目“英國卓越教師計劃對我國卓越教師培訓計劃實施的啟發(fā)與影響”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袁漫琳(1998-),女,湖北宜昌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英語教育、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