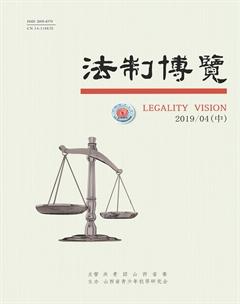新時代,新矛盾,再看科學立法
摘 要: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轉變,成為科學立法新的起點,社會矛盾是動態發展的,要求立法既要遵循法律制定的內在規律和程序,更要準確反映和體現所調整社會關系的客觀規律和基本現狀,正確認識新矛盾和科學立法的相互關系,從而確保立法的科學性。
關鍵詞:科學立法;新時代;新矛盾
中圖分類號:D920.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9)11-0141-01
作者簡介:蔣東燚(1992-),男,山東濰坊人,甘肅政法學院法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訴訟法。
一、何為科學立法
科學立法的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協同并重成為了立法的新階段,并隨著時代的進步,逐漸豐富充實為“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所以在充分理解新矛盾的前提下,科學立法也應當緊隨新時代的步伐。科學立法就是指,在遵循立法工作的程序要求的同時,立法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把握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合理調整社會關系和社會需求,不斷提高立法質量。
客觀既真實,科學的事物要表現出來必須是客觀存在的真實。將法律的科學性以客觀的形式固定下來,該過程以程序的正當合法性確保法律的科學性。邏輯是理性思維的科學,不僅論證規律的科學性,還體現的是一種思維方法的科學,貫穿于立法的各個環節,合邏輯性對立法過程,立法制度等提出了更理性規范的要求,立法規定前后統一,在這種法律邏輯思維下確保立法的科學性。①
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機制,科學的立法行為必須針對應當調整的事態制定法律規則。社會關系和發展規律要應在立法中有所體現,必須從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現今客觀需要與將來可能出發,正確反映社會的公共需求。
二、新矛盾與科學立法
(一)解讀新矛盾
在黨的十九大中精準的指出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是對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成績的有力回應,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歸納而言,則是以安全、幸福和健康為基本出發點的美好生活。
“不平衡”的理解應以人為本,從人民需要的物質需要、社會需求和心理需求,映射到我國經濟與民生發展不平衡、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平衡、人與自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則體現在地區發展差異,相對落后地區主要任務仍是發展,另外發展的全面性也不充分。
(二)新矛盾對立法“科學性”之豐富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意味著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供給的數量多少和供給的總量規模大小,而是社會供給體系整體綜合水平的高低,從重“量”的發展階段進入到重“質”的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狀發生了新的變化,基本國情和當前的實際進行高度概括便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②科學立法的“科學性”必須引入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兩個要素。
三、新矛盾如何影響科學立法
(一)堅持黨領導立法
在歷史的新時期,黨對立法的領導主要應定位在中央和省級的地方黨委,以便處理立法和改革發展的關系。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應同時發揮,中共中央提出的大政方針對全國性立法進行指引,地方黨委響應中央,通過相應政策引導地方立法,才能正確處理好立法和改革發展的關系。另一方面,普遍性和非個別性同時存在于立法調整中,黨在領導立法時,必須提出更具宏觀性指導性的方針政策,此時宏觀性不僅要在覆蓋面上加強要求,還要考慮全國范圍內發展不平衡等地域差異。
(二)轉變立法觀念
步入新時代,對社會發展改革的要求更高,但法律的滯后性問題也逐漸凸顯,傳統觀念認為“法律必須是成熟了的政策的上升”必須是“穩定了的社會關系的調節工具”。不能坐以待斃的等待政策的“成熟”,而是積極創造條件,促成政策的有效運作,從而縮短法律出臺的周期,減輕滯后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要對傳統的觀念有所突破,在改革發展中是否可以先試先行,“創新”的對現有法律進行良性的突破,使立法更好地發揮對改革發展的引領作用。
(三)反映客觀規律
就現階段而言,科學立法要使立法準確契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就需要把握客觀規律,就必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和歷史階段上,面對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深刻認識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和社會主要矛盾,做到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規律與立法內容相符合,改革決策與立法協同謀劃,使立法工作更加有效和主動地回應新時期新階段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③使法律的上層建筑適應階段性變化的經濟基礎,為科學發展、經濟轉型、民生改善提供有力保障。
[ 注 釋 ]
①馮玉軍,王柏榮.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標準探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1).
②張偉.科學立法初探.人大研究,2016(10).
③周俐,閆鵬濤.論科學立法的多層次結構.上海人大月刊,2013(1).
[ 參 考 文 獻 ]
[1]馮玉軍,王柏榮.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標準探析[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28(01):92-98.
[2]熊明輝,杜文靜.科學立法的邏輯[J].法學論壇,2017,32(01):80-89.
[3]黃瑤,莊瑞銀.科學立法的源流、內涵與動因[J].中山大學法律評論,2014,12(04):1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