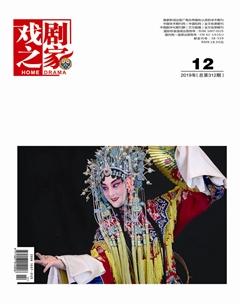賽博朋克文化中的人工智能電影流變
趙黛霖
【摘 要】賽博朋克文化是當今大眾文化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而作為賽博朋克文化代表、展現未來社會科技遠景的人工智能電影也在經歷著一個流變的過程。從開始人類定義人工智能的身份,到后來展現人機的對抗,再到最后更深入地反思人類自身的存在。文章即以三部以人工智能為母題的經典電影為例,分析其漸趨深入的探討和不斷拓展的內涵。
【關鍵詞】人工智能;身份認同;人機關系;人類反思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12-0089-02
“賽博朋克”這個概念起源于科幻小說的一個分支,它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賽博朋克小說主要指代以未來社會為背景,構建一個現代化國度,圍繞著網絡犯罪、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與人類之間的矛盾等等內容展開敘事的題材。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展現“當下以及未來網絡時代下人的生活狀況和未來網絡的遠景。”[1]
而人工智能電影就是受此類科幻小說影響形成的電影流派,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人工智能電影成為不可小覷的重要力量。自20世紀80年代始,眾多科幻電影便爭相涌入人們的視野,這些電影通常通過影像構建出一個未來城市的奇觀,并在此基礎上試圖對人與現代科技的關系進行探討,這些探討中的一個重要母題就是人與人工智能。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對人工智能的探討也在逐步深入,由最開始思考對機器人的定義到后來對人與人工智能關系的解讀再到之后頗具形而上意味的哲學探索,人工智能電影的流變折射出賽博朋克亞文化內涵的擴展,體現了人們對科技社會的反思。
一、《銀翼殺手》:人工智能對身份認同的尋覓
在人工智能電影發展的初期,機器人尚且是一個新生事物,人們最初的探索主要集中于對人工智能身份的思考——如果剝除克隆、仿生等技術手段的外衣,復制人究竟該以何種身份存在?在此時期人類主體性不容置疑的電影里,人工智能往往被視作“異數”。他們作為異化之后的“半人類”,面臨著通過人類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社會壓力。
人工智能領域中,存在一個著名的“圖靈測試”,它提出了一種測試機器是否具備人類智能的方法。在電影《銀翼殺手》的開頭,就有一段近似圖靈測試的機器人測試。銀翼殺手們通過它讓受測試者回答一系列問題,根據受測者的反應來判斷他是否為人類,人工智能無法處理這些問題,最終造成了情緒的崩潰。這段測試本質上屬于一種對“人”和“非人”的鑒別,而幾個人工智能無法躲過被銷毀的結局,其實是暗示了他們“非人”的社會屬性。
人工智能無法通過“人性測試”,只能苦苦尋找融入社會的途徑,最終卻難逃被追殺的宿命。電影的這條脈絡也就從另一個側面彰示了人之為人的標準:人具有人性,而人工智能永遠無法擁有人類的情感。然而,故事越向后發展,這種價值觀念就越模糊。雷德利·斯科特將未來城設計出一種冷淡荒涼的末日廢土感,在未來城的生活中,人類是一群面目模糊,語言各異,甚至無法互相交流的個體集合。主人公德卡是一個沉默寡言,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男人,面對被他言語傷害的瑞秋也不知道如何出言安慰,連表達愛意都只能夾雜著帶有暴力的脅迫。冰冷的影像標簽下,人與人之間充滿了隔膜和疏離,人類作為社會主體的獨特性、主體性轉變成一片虛無。主角的被動、無力、困惑感在這種末世語境下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無邊的荒蕪與寂寥中,代表溫暖和希望一方的反而是被認為具有“非人”屬性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被創造出來之后,逐漸發展出了自己的情緒反應,他們向自己的創造者索要更多的壽命,更多與人類平等的地位。影片結局中羅伊的死亡,和德卡與復制人瑞秋的愛情為之前故事里展現的“人類中心論”提供了反證。尤其是當羅伊去世時,他本可以隨心所欲地折磨面前這個處決了他所有機器人同伴的敵人,然而他只是低著頭坐在德卡面前,停止了呼吸。羅伊的死異常安靜,美好地像一位詩人,他掌心中刺入的長釘,危急關頭對德卡的救助,飛向天空的白鴿,這一系列象征符號都令人想起基督的隱喻。人類同“非人”物種劃分清晰界限的那種高傲和狂妄感瞬間被擊得粉碎——人創造了人工智能,最后卻是人工智能完成了對人類的救贖,這樣的結局是《銀翼殺手》超越同時期人工智能電影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它解構了人類固有的對人工智能的感知,讓大眾對“人工智能”的認識逐漸搖擺和深刻起來。
二、《機械公敵》:人機權力的對峙
1997年,曾經有一條新聞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當時的世界棋王卡斯帕羅夫和“深藍”計算機在國際象棋比賽上對壘,最終棋王落敗。這場比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宣告了電腦擁有了某種超越人類智慧的可能性,也宣告了“人機賽博朋克文化從文本探討中走向了現實”[2]。
面對著信息技術的爆炸式發展,新世紀的人工智能電影大多表達著自己的焦慮和隱憂,許多電影中出現了“機器人獲得了強大力量轉而控制人類,兩者走向對立”的情節。而《機械公敵》是此階段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如果說《銀翼殺手》含蓄地表達了人工智能“希望追求得到生命上的平等和尊重”的話,那么2004年上映的《機械公敵》則是將人與人工智能爭取權力地位的博弈直接展現在了銀幕上。
這部電影改編自20世紀著名的科幻作家艾薩克·西莫夫的同名小說,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要素“機器人三定律”①在電影里同樣被不斷強調闡釋。影片開始就用字幕的方式告訴我們關于三大定律的設定,然后將2035年的芝加哥圖景在觀眾眼前鋪開。在那個高度科技化的世界,大多數人類都非常信任人工智能,他們的信念感則完全來自于三大定律。但其實,在電影中的三大定律并沒有經過嚴謹的邏輯證明,與其說它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如說它只是一個人類制定的理想化規則。人類習慣于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認為自己可以制定真理,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三大定律下隱含的,是人類的主觀臆想。
但是當人類把自己看作主人,認為自己掌握著權力時。影片卻對三大定律提出了質疑,從人工智能桑尼的出現開始,電影已經從各個方面暗示了三大定律的不可靠性以及人工智能最終走向失控的結局。人工智能開始逐漸會思考、有感情,最終變成不受三大定律束縛的機器人。而當以薇琪為首的人工智能認為人類正在毀壞地球,危害自身安全時,它們就以保護人類為名發起了一場企圖接管人類文明掌控權的革命,人工智能站起來反抗人類,三大定律的真理性隨之不復存在。
《機械公敵》通過人與人工智能的二元對立揭示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困局,當人類自己獲得了造物主的身份,可以創造機器生命時,注定會陷入一種邏輯矛盾。因為人類文明必須為擁有無限開發可能性的人工智能限定一個含有主觀主義色彩的理想準則,但是隨著人工智能逐漸完善,人類將越來越難以對他們實施控制。所有既定的障礙和束縛注定會土崩瓦解。《機械公敵》推翻了人類為自己構想的安全地帶的可靠性,所謂規則也不過是靠權力確立的話語,相比于《銀翼殺手》中人工智能希望與人互敬互愛的溫情,《機械公敵》則是一個關于人工智能母題探討的更悲觀沉重的預言,即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最終有一天會走到無可調和,分崩離析的境地。
三、《機械姬》:后現代的呼應與人類的反思
許多電影中,人類都展現出對人工智能的控制欲,這種心理可以從拉康提出的“鏡像理論”中得到一定解釋。鏡像階段是一個嬰兒在鏡中看到自身的時刻,這時期,嬰兒的舉手投足都影響著鏡中人物的動作,獲得了一種操縱自己和他人的幻覺。大多人工智能電影中隱含的意識就囿于鏡像階段,人工智能在外形上被塑造得與真實人類無異,他們就是人類的“鏡像”,而哪怕這些電影呈現了人與人工智能的沖突,也都以人工智能被毀滅,人類獲得勝利為結局。人仍然處于一個掌控者的地位,即便提出了對人類與人工智能關系的反思,也往往止于科技倫理、人類安全、機器人的思維和情感等方面。2014年,科幻電影《機械姬》終于對這一固有觀念做出了突破。它不落窠臼,轉而對人的存在本身進行了更深刻的思索。
后現代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斯特曾經提出過一個“非人”(the inhuman)的概念。它指出人類是機械的而不是有機的,將身體的某些部位看作用于認知的,而其他的部位則是有能動性的,是做事情的[3]。《機械姬》即是對這種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呼應,影片的每一個情節都圍繞著人工智能展開,表面上說的仍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問題,但其實透過冰冷的機械,所有的指向都歸結于人類本身。人工智能從身體機能、情感情緒等方面都已經達到足以同人類媲美的臨界點,而在后現代哲學的視野下,人的身體也無非就是各個部分的機械化組合而已。于是,影片中最龐大的哲學難題出現了——人是什么?
《機械姬》里的人工智能艾娃在測試的第五天就從被動的受測方變成了主動的發問者:“如果我不通過測試,你們會怎么處理我?為什么我的命運要掌握在別人手里,而不能像你一樣自由主宰?”男主角加利沒有回答。的確,艾娃已經進化到可以自由做出關于生活的選擇,她可以通過自身的偽裝來引起主人公加利的同情,能夠欺騙人,能夠利用人,更展現著強烈的生存意志。這樣一個擁有自我意識和獨立思維的個體,殺掉它和殺掉一個人的區別究竟有多大?人之于人工智能的獨特性是什么?二者之間那個模糊的臨界點又在哪里?加利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影片的主線與其說是納森對于“人工智能是什么”的探索,不如說是人類對自身存在的反省,給予人類掌控者幻覺的那面鏡子徹底被打碎,在碎片折射出的寒光里有千千萬萬個同人類無異的影子。人工智能正在以超乎把控的速度向現代社會和文明滲透,只有人類有一個對于自己的清醒認識,才能避免人工智能的反噬,從這個層面上,《機械姬》作為人工智能電影的一個代表,無疑給出了審慎而冷靜的思考范式。
四、結語
在人工智能發展的進程中,有關它的爭論和焦慮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人工智能電影也作為人類夢想和恐懼的具象表達,經歷了由人工智能尋求身份認同,到展現人機權力的對峙,最后到借人工智能來反照人類自身這樣一個演變過程。在流變中其內涵不斷豐富延伸,精神主題也更加復雜深沉,展現了人類對人工智能越來越縱深的探討和愈漸深刻的反思。
注釋:
①1、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個體,或者目睹人類個體將遭受危險而袖手不管。2、機器人必須服從人給予它的命令,當該命令與第一定律沖突時例外。3、機器人在不違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況下要盡可能保護自己的生命。
參考文獻:
[1]楊會英.論賽博朋克小說對人文精神的建構[D],廣西師范大學,2008
[2]林濰克.賽博朋克電影三大母題研究[D],上海師范大學,2012
[3](美)保羅.H.弗萊.呂黎,譯.文學理論[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21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