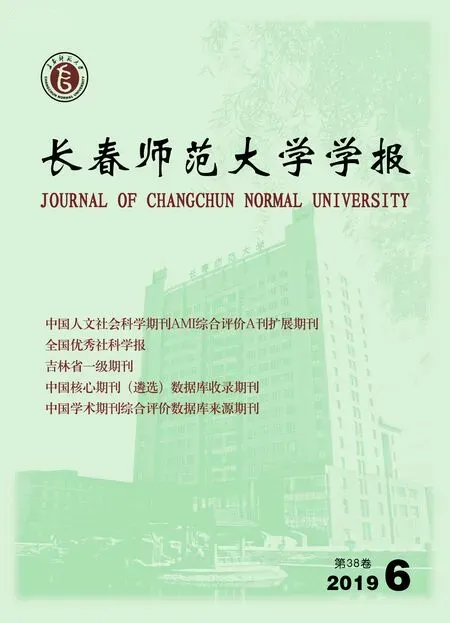基于GIS的城市濱海游憩空間分布特征研究
呂 梁,陳鐘煊,魏文靜,潘 輝
(1.福建農(nóng)林大學(xué),福建福州 350002;2.閩江學(xué)院旅游系,福建福州 350108)
游憩是城市的四大功能之一,游憩空間是城市發(fā)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對于市民的娛樂、鍛煉、交往、旅游等方面都有著重大的影響。據(jù)建設(shè)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截至2015年,福州城市化水平已達到了67.7%,社會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城市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時間和收入快速增加,休閑需求迅速膨脹,城市游憩用地供給與民眾休閑需求的矛盾也日益凸顯。2016年,在《對接國家戰(zhàn)略建設(shè)“海上福州”工作方案》中,福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努力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qū)海上合作戰(zhàn)略支點城市”。依托“海絲優(yōu)勢”建設(shè)世界級的濱海旅游目的地已引起國家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濱海游憩空間是“海上福州”主要的、特色的旅游產(chǎn)品,是福州海洋旅游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重要支撐,福州濱海游憩空間的研究對于實現(xiàn)世界級、國際化旅游目的地的發(fā)展目標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從我國的城鄉(xiāng)規(guī)劃體系來看,缺少對城市游憩空間的規(guī)劃控制和對游憩空間的統(tǒng)籌與整合。對于福州濱海游憩空間分布特征的研究,有助于對城市濱海區(qū)域游憩空間的類型、總體規(guī)模、空間結(jié)構(gòu)和空間布局進行全面的了解,對福州濱海游憩空間進行整合,并為福州濱海游憩空間的統(tǒng)籌發(fā)展提供理論支撐。
國內(nèi)關(guān)于游憩空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憩空間的設(shè)計和規(guī)劃策略[1-6]、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特征[7-11]以及游憩質(zhì)量[12-15]三個方面。如姜洪慶從規(guī)劃布局、地域建筑、通道設(shè)計、開敞環(huán)境和承載內(nèi)容五方面提出嶺南城市游憩空間的設(shè)計策略,探討如何通過游憩空間激發(fā)城市活力的策略[16]。許五軍以贛州為例,分析其游憩空間與特色文化相結(jié)合的布局模式,詳細闡述贛州在宋城文化、客家文化、紅色文化和堪輿文化等地域文化影響下游憩空間的打造策略,為構(gòu)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宜居、宜業(yè)、宜游的現(xiàn)代都市提供參考[17]。李明芳利用空間句法分析從宏觀、中觀、微觀的角度來剖析煙臺濱海游憩空間結(jié)構(gòu)協(xié)同關(guān)系[18]。馮代慈運用內(nèi)容分析法和空間分析法,對深圳城市生態(tài)游憩空間的質(zhì)量進行研究,并提出相關(guān)建議[19]。對游憩空間分布特征的相關(guān)研究較少,本文通過對福州濱海游憩空間分布特征進行研究,為之后規(guī)劃提供理論支撐。
1 研究區(qū)域及數(shù)據(jù)來源
1.1 研究區(qū)域
研究區(qū)域為福州市濱海的4個區(qū)縣:連江縣、馬尾區(qū)、長樂區(qū)和閩清市,總面積約4660.2 km2,包括了福州市主要的濱海區(qū)域,是福州市重點規(guī)劃的區(qū)域。據(jù)福州市統(tǒng)計局統(tǒng)計,2006—2016年福州市濱海的4個區(qū)縣的常駐人口增長了近20萬,2016年有285.1萬常駐人口,占福州市總?cè)丝诘?7.67%。
1.2 數(shù)據(jù)來源
通過網(wǎng)絡(luò)收集和實地考察相結(jié)合的方法對數(shù)據(jù)進行收集,具體分為以下兩個步驟:第一,通過對相關(guān)網(wǎng)站對福州濱海游憩空間信息進行收集,如福州市旅游發(fā)展委、百度地圖、高德地圖等網(wǎng)站。第二,進行實地調(diào)研,通過集思寶UG905專業(yè)版手持GPS定位儀,對游憩空間進行定位,對網(wǎng)絡(luò)收集數(shù)據(jù)進行補充和驗證,最終建立了福州濱海游憩空間數(shù)據(jù)庫。
2 游憩空間分類研究
吳必虎等針對使用者的不同將游憩空間分為“主要面向本地居民”和“同時面向外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游憩空間兩類[20];秦學(xué)依據(jù)大小將游憩空間劃分為室內(nèi)游憩空間、社區(qū)游憩空間、城市游憩空間和地區(qū)游憩空間4類[21];吳鋒根據(jù)游客動機將游憩空間分為主動性游憩空間、伴隨性游憩空間、模糊性游憩空間3個大類[22];蘇平等依據(jù)旅游地的資源屬性和旅游活動將游憩地類型分為自然觀光、自然娛樂、自然運動休閑、人文觀光、人文娛樂、人文休閑、人造觀光、人造娛樂、人造運動休閑等9種游憩地類型[23];馬惠娣則將游憩空間類型分為自給性游憩空間和公共性游憩空間[24]。金世勝以城市用地性質(zhì)、人們游憩活動特征和重要程度,將城市公共游憩空間分為9個大類,28個中類,50個小類[25]。張勛結(jié)合城市游憩空間的現(xiàn)狀,將城市游憩空間劃分為2個大類,8個亞類,52個基本類型[26]。錢冶澄則將游憩空間分為了旅游景點依托型、商業(yè)設(shè)施依托型、公共空間依托型、城市濱水游憩依托型和文化與娛樂場所依托型[8]。李明芳結(jié)合每個休閑區(qū)域為市民所利用的功能性質(zhì)和相互關(guān)系,將游憩空間分為濱海城市公園、濱海廣場、商業(yè)休閑區(qū)域、文化娛樂及體育場所、濱水休閑場所、旅游景區(qū)(點)、城市內(nèi)部及郊區(qū)大型綠地、其它休閑場所[7]。綜合以上研究,結(jié)合福州濱海區(qū)域現(xiàn)狀,依據(jù)服務(wù)人群和場所功能,本文將福州濱海游憩空間分為旅游度假型、公園綠地類型、文化型、商業(yè)型游憩空間(表1)。

表1 福州濱海游憩空間分類
3 研究方法
本文借鑒王洪橋?qū)皡^(qū)分布特征的研究所用的方法[27],通過最臨近指數(shù)、基尼系數(shù)和核密度分析對福州濱海游憩空間的聚集程度、各區(qū)域數(shù)量差異程度和布局特征進行了研究。
3.1 最鄰近指數(shù)
最鄰近指數(shù)是表示點狀事物在地理空間中相互鄰近程度的地理指標[28]。在地理空間結(jié)構(gòu)的研究中最鄰近指數(shù)得到了廣泛應(yīng)用,其表達式為:
(1)
其中,R為游憩空間的最鄰近指數(shù);De為游憩空間隨機分布時理論上的最鄰近距離;n為游憩空間數(shù)量;Di(Si)為區(qū)域內(nèi)游憩空間到其最鄰近點的距離。當(dāng)R=1時,游憩空間分布類型為隨機分布;R>1時,游憩空間分布類型為均勻分布;R<1時,游憩空間分布類型為聚集分布。
3.2 基尼系數(shù)
基尼系數(shù)作為描述區(qū)域空間的離散分布情況的重要參數(shù),已經(jīng)被廣泛應(yīng)用在地理學(xué)中,其公式如下:
(2)
其中,G為游憩空間基尼系數(shù),n代表各區(qū)域內(nèi)的游憩空間數(shù)量值,Wi為各區(qū)域游憩空間累計數(shù)量占總游憩空間數(shù)量的比重。其中G在0到1之間,當(dāng)基尼系數(shù)取值小于0.2時,表明各區(qū)域游憩空間分布屬于絕對平均狀態(tài);當(dāng)G在0.2~0.3之間時,表明各區(qū)域游憩空間分布為比較平均狀態(tài);當(dāng)G在0.3~0.4之間時,表明各區(qū)域游憩空間分布相對合理;當(dāng)G在0.4~0.5之間時,表明各區(qū)域游憩空間差距較大;當(dāng)G大于0.5時,表明各區(qū)域游憩空間差距懸殊。
3.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強度可以清晰地反映區(qū)域游憩空間要素在空間上的分散和集聚特征以及這種形態(tài)的變化[29],其公式為:
(3)
其中,S為待估計區(qū)域游憩空間的位置;Si為以現(xiàn)有區(qū)域為圓心的區(qū)域游憩空間的位置;h為區(qū)域半徑空間范圍內(nèi)第i處游憩空間的位置。
4 研究結(jié)果
4.1 數(shù)據(jù)庫統(tǒng)計分析
如表2所示,通過數(shù)據(jù)庫對各類游憩空間進行了統(tǒng)計,結(jié)果表明福州濱海游憩空間共有960個,其中在馬尾區(qū)最多,為406個,其次是福清市,為250個,最少的是長樂市,為115個。從不同類型來看,商業(yè)型最多,為507個,其次是文化型,為201個,最少的是旅游度假型,為116個。

表2 福州濱海各類型及各區(qū)域游憩空間數(shù)量統(tǒng)計表
4.2 最鄰近指數(shù)分析
通過ArcGIS平臺的Average Nearest Neighbor工具進行計算,得到不同類型游憩空間的最鄰近指數(shù)(表3)。由表3可見,福州濱海游憩空間最鄰近指數(shù)R=0.417<1,表明福州濱海游憩空間總體上分布為聚集形態(tài)。其中商業(yè)型的聚集程度最高,其最鄰近指數(shù)為0.24;其次是文化型,其最鄰近系為0.322;公園綠地型和旅游度假型雖為聚集狀態(tài),但逐漸偏向于隨機,它們的最鄰近指數(shù)分別為0.573和0.672。旅游度假型游憩空間主要依靠旅游資源,而旅游資源的分布是由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共同決定,所以其分布是偏向于隨機的。公園綠地型的服務(wù)受體較為廣泛,各地差異較小,所以也偏向于隨機分布。而文化型和商業(yè)型游憩空間的產(chǎn)生,會更多地依靠當(dāng)?shù)亟?jīng)濟,二者皆會在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較高的地區(qū)聚集。

表3 各類型游憩空間最鄰近指數(shù)
4.3 基尼系數(shù)分析
由表4可見,福州濱海游憩空間的基尼系數(shù)G=0.245,表明各區(qū)域在總體數(shù)量上差距較小,較為平均,但沒有達到相對合理的狀態(tài)。在各個游憩空間類型方面,公園綠地型的基尼系數(shù)G=0.159,小于0.2,表明該類型游憩空間在各區(qū)域數(shù)量差異極小,屬于絕對平均的情況;旅游度假型和文化型的基尼系數(shù)分別為0.216和0.248,這兩類游憩空間類型的基尼系數(shù)在0.2~0.3之間,表明各區(qū)域在這兩種類型游憩空間數(shù)量上差距較小,較為平均,但沒有達到相對合理的狀態(tài)。商業(yè)型的基尼系數(shù)為0.302,在0.3~0.4之間,表明該類型游憩空間在各區(qū)域的數(shù)量分布較為合理。

表4 各類型游憩空間基尼系數(shù)
4.4 核密度分析
圖1為旅游度假型核密度強度圖,總體上看,該類型游憩空間呈現(xiàn)南部強,北部弱的分布格局,分布較為廣泛,有連片的趨勢,其中形成了兩個核密度強度高的區(qū)域,一個在長樂市,一個在福清市,連江縣的大部分區(qū)域核密度強度較弱。從圖2可以看出,公園綠地型游憩空間總體上呈現(xiàn)北強南弱的格局,分布范圍較廣,在長樂市、連江縣和馬尾區(qū)形成了一個核密度強度高的區(qū)域,其中在長樂市和馬尾區(qū)核密度強度最高,福清市核密度強度較弱。從圖3可以看出,文化型游憩空間總體上呈現(xiàn)“三足鼎立”,形成了福清市、長樂市和馬尾區(qū)、連江縣三個核密度強度高的區(qū)域,而且在此三個區(qū)域高度聚集。如圖4所示,商業(yè)型呈現(xiàn)南強北弱的分布局,福清市形成的區(qū)域核密度強度最高,馬尾區(qū)和長樂市次之,連江縣最弱。如圖5所示,福州濱海游憩空間整體上呈現(xiàn)中南強而北弱的分布格局,形成了兩個核密度強度高的區(qū)域,一個在福清市,一個在長樂市和馬尾區(qū)。連江縣形成的核密度強度區(qū)域弱于前者。

圖1 旅游度假型游憩空間核密度強度

圖2 公園綠地型游憩空間核密度強度

圖3 文化型游憩空間核密度強度

圖4 商業(yè)型游憩空間核密度強度

圖5 福州濱海游憩空間核密度強度
5 結(jié)論
游憩空間是城市游憩系統(tǒng)的載體,對城市的健康運轉(zhuǎn)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對城市居民的心理和生理都有非常重要影響。本文通過建立福州濱海游憩空間數(shù)據(jù)庫,并在此基礎(chǔ)上對福州濱海游憩空間進行了統(tǒng)計分類和分布特征研究。結(jié)果表明,福州濱海游憩空間主要分為4大類,總體以聚集形態(tài)分布。其中商業(yè)型的聚集程度最高,旅游度假型聚集程度最低。福州濱海游憩空間的基尼系數(shù)為0.245,表明各區(qū)域在總體數(shù)量上差距較小,較為平均。在核密度方面,旅游度假型和商業(yè)型呈現(xiàn)南部強,北部弱的分布格局。公園綠地型呈現(xiàn)北強南弱的分布格局。文化型總體上呈現(xiàn)“三足鼎立”,形成了三個核密度強度高的區(qū)域。
通過上述研究,在基尼系數(shù)方面除商業(yè)型游憩空間之外,其它游憩空間類型都尚未達到數(shù)量上的合理,尤其是公園綠地類型的游憩空間基尼系數(shù)為0.159,屬于絕對平均水平,這就需要政府在進行城市游憩空間規(guī)劃時注意各個區(qū)域不同類型游憩空間數(shù)量發(fā)展的問題,要統(tǒng)籌兼顧,確定各個區(qū)域?qū)硪l(fā)展游憩空間的類型及數(shù)量。通過核密度分析圖,可以直觀地了解到各類游憩空間的分布情況,政府可以結(jié)合各個類型的土地測評,來對那些開發(fā)適宜性高但核密度強度低的區(qū)域進行優(yōu)先開發(fā),以此來優(yōu)化游憩空間的分布結(jié)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