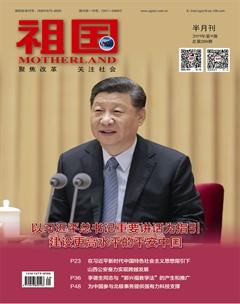城市社區治理中資源何以轉化為社會資本
關鍵詞:城市社區治理? ?資源? ?社會資本? ?轉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單位制的解體和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新型的商品房小區在我國各大城市開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一系列關于商品房小區公共事務的治理問題亦隨之而來。人們普遍認為,“陌生人社會”的商品房小區已經取代了原有的傳統共同體和單位制下的“熟人社會”,它們往往缺乏社會資本,具有如社區聯系松散、信任程度低和社區歸屬感不足等一系列的特征。盡管許多商品房小區的住戶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較高,這些小區的社會資本卻似乎并未與它們豐富的資源成正比。在這樣的社區土壤中,資源如何在社區治理過程實現向社會資本的轉化,是本文通過對比兩則社區治理個案,希望能加以探討的議題。
一、資源與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一個內涵豐富而又爭議頗多的概念,隨著時代變遷和出于不同研究視角的考慮,學界對它歷來沒有統一的界定和解讀。
布迪厄將社會資本視作“與行動者擁有的持久性網絡相關聯的現實的和潛在的資源之集合。”科爾曼根據社會資本的功能提出其定義,強調它的結構性質和公共產品性質。普特南則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上個人之間的相互聯系——社會關系網絡和由此產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依賴的規范”。與前面三位學者堅持在團體活動或集體關系中考察社會資本的視角不同,林南兼顧個體選擇行為和社會結構因素,主張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
雖然這些經典研究角度不一,觀點也存在分歧,但他們都達成了共識: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網絡關系中的可以帶來回報的資源投資。因此,本文對社會資本的生產邏輯的討論,就轉變為如何使商品房社區所蘊含的資源順利轉化為社會資本的議題。
二、個案選取與個案描述
(一)基本概況
本文主要采用個案研究和比較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兩則個案A小區和B小區均位于佛山市南海桂城,它們建成于20世紀90年代,曾是當地中高檔商業樓盤,二者相距不足1公里。其中A小區占地面積約1.2萬平方米,共有樓宇20棟,住戶485戶,約計1600余人;B小區占地總面積約1.9萬平方米,共有樓宇22棟,住戶545戶,約計1800余人。
(二)兩個社區的治理過程
1.A小區的治理過程
2015年底,A小區6號樓的H業主以“樓層太高,老人行動不便”為由,向該樓其他業主發起了為6號樓加蓋電梯的動員,征得該樓三分之二業主同意后,向佛山市國土規劃局申請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并準備動工。工程開始動工時,此舉遭到小區其他業主強烈反對。
他們反對加建電梯出于多方面原因:第一,本來并不寬敞的道路將被電梯占去大部分路段;第二,電梯的加建還占用了消防通道,給小區帶來嚴重的消防隱患;第三,加建電梯“未經全體業主同意”,而且相關材料僅隱蔽地公示在該棟樓道,大部分業主毫不知情。
關于加建電梯的目的,支持和反對雙方各執一詞,6號樓的業主認為該棟老人多,沒有電梯出入不方便;反對加建的業主們則聲稱該棟沒有行動不便的老人,認為6號樓業主損人利己。
爭執發生后,相關公示文件才被貼到小區宣傳欄,聯名反對建電梯的業主超過230戶,甚至有業主將國土規劃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銷該局頒發的許可證,最終法院判決撤銷許可證,加建計劃以失敗告終。
2.B小區的治理過程
B小區與A小區同是樓齡近二十年的舊小區,因為小區里老人較多,小區的設施又陳舊,在2016年初,加建電梯的計劃被熱心的業主提上了議程。
由于B小區近五年沒有引入物業公司,小區里三位退休老人因為看不慣日益嚴重的衛生問題而自發清理小區垃圾,并在2014年成立了自治小組,自此小區的各項公共事務都由自治小組管理。為了方便管理,小區每棟樓宇還選出了樓長。為了這一次加建電梯的計劃,自治小組和樓長們常常召集業主們開會溝通,解決了不少加建電梯的難題,3臺新建電梯最終全部順利投入使用。
三、社會資本:嵌入社會網絡中的資源
由于A小區和B小區的建成時間、地理位置和人口數量相近,又都曾經屬于中高檔商品房社區,可以認為這些業主的財富、權力以及聲望在總體上趨于一致,資源較為豐富。但在上述治理過程中,這些資源卻并未使這兩個小區在社會資本上獲益。
和大多數商品房社區一樣,本文所涉及的兩個小區是典型的“陌生人社會”。由于業主們本來互不相識,許多人工作早出晚歸,加上每家每戶相互獨立,在時空的雙重阻隔之下,鄰里間互動交流更少,難以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
這種冷漠更體現在這兩個社區的業主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上。2006年前后,A小區由于原物業公司管理不善,業主曾集體拒交物業費。B小區同樣發生過大批業主拖欠、拒交物業費的事件,兩任物業公司因此相繼撤場,此后再沒有引入物業公司。在自治小組成立前,該小區的保潔和治安問題嚴重,業主們對此不聞不問。
盡管兩個小區都是高資源的社區,但嚴重的社區治理問題反映出其社會資本的匱乏,業主之間由于缺少交往,沒有形成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社會關系,資源也難以嵌入到社區的社會網絡中,社區的公共事務無人問津。
四、社區治理中社會資本的生產邏輯
(一)普遍互惠與克里斯瑪型領袖
對比兩個小區加建電梯的案例可以發現,動員發起人的出現往往是社會治理最初得以開展的契機。B小區自治小組幾位老人在訪談中提到,“我們都沒有工資……我們本身是業主,是義務的。我又是黨員,想用共產黨給我的福利回報社會。” 這種強烈的普遍互惠特質是動員發起人身為領導者最大的魅力,因為他們不但無法在短期內帶來任何私人的收益,而且還需為此投入大量成本,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使他們贏得社區成員的最初信任。
出于這種信任,一種克里斯瑪型的領導形式開始建立起來。和傳統型領袖和法理型領袖不同,他們的權力既不是社區原有傳統所賦予的——因為社區的“陌生人社會”性質和過去嚴重的治理問題體現出它一貫缺乏公共參與的傳統;也不是來自制度和規范的規定——社區物業和業委會的缺位導致小區的日常管理并沒有固定的承擔者和程序規范。因此老人們幾乎完全是憑借自身普遍互惠特質所帶來的魅力來贏得業主們的廣泛認可,“很多人還很不理解,質問我們有沒有授權,合不合法。我們就是自發起來的,哪有什么授權不授權呢?……就是用行動感動居民的心。”
盡管獲得社區成員認同的過程十分曲折,但克里斯瑪型領袖與其他兩種領導類型相比,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往往更容易激起社區成員的情感共鳴。這是由于克里斯瑪型領袖的統治團體是一種感情共同體,領導者的任免并非取決于毫無交往基礎和情感關聯的規章制度,社區成員對他們的服從也不是出于傳統的威懾,而是情感上的認同。
(二)信息橋的搭建
動員發起人的克里斯瑪型領導一旦建立起來,他們在動員的過程中就承擔起了搭建橋梁的作用,在社區里形成以他們為核心的行動網絡,與他們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行動者的資源就通過這條橋梁不斷地嵌入到社會治理的行動網絡中。
動員發起者在傳遞信息和聯系其他行動者時所采取的動員策略和動員范圍成為結成社會網的關鍵,直接影響這個社會網絡的性質如密度、范圍和資源的流動方向等,不但影響著資源向社會資本的轉化過程,而且關系到動員結果的成敗以及在這基礎之上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因此信息橋的搭建對社區資本轉化過程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在A小區的案例中,6號樓的業主和非6號樓的業主對加建電梯起因的說法大相徑庭。6號樓的業主表示本棟樓“老人很多”,有加建電梯的必要;相反,非6號樓的業主則一致認為該樓“沒有老年人”,只是“想升值”,對其“占用小區公共資源”的做法持譴責態度。有限的動員范圍和缺乏共識的動員策略直接導致了6號樓業主與其他業主在信息獲取上的不對稱,更引起其他業主對加建動機的誤解。
相比之下,B小區的社區治理是一次成功地將資源轉化為社區資本的過程。B小區的自治小組通過按樓棟選出樓長、再由樓長與業主溝通的方式發展社會聯系,將加建電梯的信息層層傳遞到每一位業主。他們還不定期召開討論會,邀請相關樓棟的業主出席討論,增進了彼此的信任程度,又有效地傳遞了信息。因此,盡管兩個小區占有資源的程度相當,動員結果卻截然相反。
可見,業主們所擁有的資源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當中才能作為所在社區的社會資源而存在,動員發起人在其中所搭建的信息橋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采取的動員方式和策略是否得當決定了能否充分地實現社會資本的生產和轉化。
(三)信任與共同規范的生產和維持
信息橋的成功搭建,一方面可以使社區成員便捷而直接地獲取到關于社區治理的相關信息,他們也得以將自身的意見反饋給組織者,信息透明度通過這一過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信息的透明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換取社區成員的信任;另一方面,隨著社區社會網絡的形成和資源的嵌入,業主之間的情感紐帶和依賴關系得到了強化,信任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產物之一。
A小區的加建電梯動員未能最終實現,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動員發起者的做法不符合全體業主的共同利益,在未經小區大多數業主同意就占用消防通道和公共道路。業主們認為加建電梯是6棟業主的自私之舉,引起普遍的反感和阻攔。
對于加建電梯,B小區的業主也并非毫無異議,有業主就提到自己的家庭對加建電梯的需求不大,在被征求意見時也投過反對票,但由于是全體業主共同投票,公開的投票結果顯示大部分業主同意加建,加上多方協商制定的加建方案維護了共同利益和秩序,因此即使他們一開始不愿意參與加建電梯,但考慮到電梯能夠給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提供便利,也信服于動員者對社區整體狀況多番考察后設計的加建方案,他們最終還是選擇妥協。
伴隨著資源的嵌入和社會資本的生成,社區往往發展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規范,這些規范在動員實踐中逐漸成為全小區所共同認可、共同遵守的原則。以B小區為例,自治小組和樓長們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召集業主召開了許多次專題研討會和聯席會議,在會議上對電梯修建和使用過程的各種細節問題和注意事項都進行了規定,對于自治小組的安排,業主們大多也愿意自覺地配合,以至于在成功加建電梯之后,小區各種重大公共事務也必須經過所有業主共同開會協商才能決定,這種新的規范得以在小區里確立并得到維持。通過這種方式,社會資本部分地以規范的形式被固定下來,成為社區社會結構的重要構成。
五、結語
從對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在集體治理動員發生前,A小區和B小區都屬于高資源、低社會資本的社區,社會交往的缺乏使資源無法嵌入到社區的社會網絡,導致這兩個社區社會資本的稀缺。
本文通過兩個小區不同的社區治理運作,分析了資源向社會資本的轉化過程。動員發起人的普遍互惠特質使他們充當起發起者和組織者的角色,這種特質有可能使他們贏得來自社區成員的最初信任,由此他們可以成為主導社區治理的克里斯瑪型的領袖,他們通過一定的動員方式和策略來承擔起搭建橋梁的作用。信息橋的搭建使社區范圍的行動網絡得以形成,與動員發起人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行動者的資源就通過這條橋梁不斷地嵌入到社會治理的行動網絡當中,轉化為社區的社會資本。隨之產生的還有社區成員間的相互信任以及一系列共同規范,它們在社會治理中被逐漸固定下來,共同構成了該社區的社會資本。
參考文獻:
[1]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6:241-258.
[2]Coleman,Jame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
[3]Putnam,RobertD.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2001.
[4]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劉少杰.以行動與結構互動為基礎的社會資本研究——評林南社會資本理論的方法原則和理論視野[J].國外社會科學,2004,(02):21-28.
[6]侯鈞生.西方社會學理論教程(第二版)[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鄧雯文,女,中共佛山市委黨校教師,研究方向:基層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