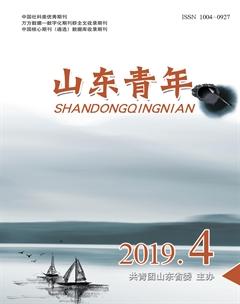社會心理因素對冠心病的影響
黃兆鋒
摘 要:冠心病是危害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發病率和病死率逐漸增加。冠心病的傳統危險因素僅能解釋部分病例,隨著社會的發展,個體的應激狀態、情緒、人格特征和社會支持等社會心理因素與冠心病的發生、發展、治療和預后階段有著越來越緊密的聯系。一方面,社會心理因素作用于有機體從而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反應;另一方面,機體生理功能的變化也會對個體的心理狀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從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兩大方面對冠心病患者的影響因素加以綜述,以期為冠心病的防治和護理工作提供幫助,從生理、心理兩方面去消除病因,促進患者更好地康復。
關鍵詞:冠心病;心身疾病;社會因素;心理因素;身心健康;危險因素
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Disease)是一種器質性疾病,通常由心理社會因素引起而導致持久的生理功能紊亂[1]。在Alexander最早提出的7大類心身疾病中,冠心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不斷上升,是目前中國成人心臟病發病或病死的主要原因之一,涉及到億萬人群的生命和健
康[2]。心身疾病的發病因素并不是單一的,而是由社會、文化、心理以及遺傳、代謝等多重因素共同影響的。除了生物因素以外,社會心理因素是機體賴以生存的一個重要的外環境,對于人的健康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諸多研究表明,社會心理因素與冠心病的發展緊密相關,而影響心身健康的社會心理因素主要有個體的應激狀態、情緒、人格特征、社會支持、經濟狀況、慢性壓力等方面[2],本文將從這些角度去探討社會心理因素在心身疾病的發生、發展、治療和預后的作用。
1.社會因素
1.1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指的是個體通過社會聯系所得到他人精神上的支持。每一個個體都不是獨立地存在這個社會,有著眾多人際關系紐帶,并且這些紐帶都是可利用的資源。如果個體擁有良好的社會支持,那么當他遇到負性的生活事件時,他也能夠緩沖由這些負性事件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從而維持自己的健康。另外,社會支持通過鼓勵個體采取健康的行為方式,提高其治療依從性和自我健康管理水平而直接影響個體自我效能感[3]。但是,在張國富等人的研究中發現,冠心病患者的社會支持評分顯著低于正常人,由于患者在疾病反復發作慢性病程中獲得較少社會支持,不能有效緩解慢性應激引起的負面情緒反應[4]。所以,缺乏了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可能導致疾病反復發作或者使病程不斷地延長,這對于患者的治療還是預后都是不利的。
1.2? 社會經濟狀況
社會經濟水平的高低極大地影響著冠心病的發生與預后。經濟是影響慢性病患者心理狀態的重要因素,而冠心病作為慢性病的一種,其治療過程長,治療費用高,經濟水平高的患者容易接受更好的治療,更容易獲得戰勝疾病的信心,并形成良好的、積極地心理應對方式。如Lazzarino等研究發現低社會經濟水平可能會引起冠心病患者的心理痛苦,影響生活質量,從而提高其死亡率[5]。Woodward等通過對教育、職業、收入和經濟水平相關的因素比較發現,經濟水平的高低與冠心病呈負相關。而在女性的人群中,這一現象更為明顯[6]。另外低社會經濟水平通常伴隨著更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飲酒、吸煙、不健康飲食。同時與低經濟水平相伴隨的還有惡劣的居住環境、繁重的體力勞動和面對更多的生活壓力[7]。總之,低社會經濟水平的人群是冠心病發生的高危人群。
1.3? 慢性壓力
壓力又稱應激或緊張,其定義最早是由Selye在1980年提出,他認為壓力就是“個體在某些因素或事物的作用下,身體為滿足需要所產生的一種非特定性反應,并指出壓力會誘發疾病的發生”。壓力不僅影響認知、行為和情緒反應,而且影響神經體液的反應,若這種生物的應激反應持續時間長,頻繁會誘發心血管疾病或加速其發展[8]。慢性壓力主要指持續較長時間的壓力性事件以及經歷極大影響的突發事件后持續的慢性應激。楊燕飛等人通過分析臨床研究成果和流行病學的調查進展,認為慢性壓力引發冠心病的機制是復雜的,因壓力事件所產生的壓抑、焦慮及消極等負面情感會導致冠心病發病率的增加、病情加重、預后不佳[9]。馬建琴等人認為婚姻壓力、工作壓力、經濟壓力等慢性壓力都與冠心病的發病率呈正相關[10]。李瑩等人認為慢性職業緊張會導致交感神經系統的過度而持久的激活,導致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反應的產
生[11]。持續的職業緊張狀態會引發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Chazelle等[12]通過橫斷面和前瞻性研究證實了職業緊張與睡眠障礙存在相關性,間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慢性壓力是誘發冠心病發生和發展的重要危險因素[13]。胡恩元認為個體若長時間處在慢性壓力的狀態下,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將會 受到明顯的影響,并打破體會皮質醇水平的平衡,這在冠心病的發生和發展中起著重要的影響[14]。
2.心理因素
2.1 應激
應激是個體對緊張刺激的一種非特異性的適應性反應,是決策心理活動中可能會產生的一種心理因素。其中,應激性生活事件,是指在生活中需要作適應性改變的環境變故,是造成人們產生應激的重要原因。張國富[4]等人通過調查問卷研究發現,如果病前經歷了負性生活事件的冠心病患者,在這種反復發作的慢性病程中應付方式會日趨消極。應付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出個體的個性特征,同時它也影響著個體對應激的評價。如果個體采取的是認知探索和行為探索的應對方式,那么他或許能避免由于應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個體采取的是認知回避和行為回避的方式,那么他可能會產生心理危機。根據Selye[15]提出的一般性適應綜合癥,認為應激反應要經過三個時期,分別是警戒期、抵抗期和耗竭期。警戒期階段,機體通過激活神經系統來對抗應激源,保持有效行動并做好準備;抵抗期階段,在神經、內分泌系統的協調下,機體可以忍耐并保持與應激源作長期抗衡的狀態;到了耗竭期階段,機體因為對應激的生理、心理能量的對抗導致耗竭而需要得到及時的休息與能量補充。倘若個體在面對應激時,一味地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此時,應激對于冠心病的發生階段而言,它是一個誘發因素。應激就像是一個入侵者一樣,在個體的機體處于衰竭的情況下,打破了機體的平衡,使得機體往疾病的方向轉移。
2.2 情緒
情緒是指個體根據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己的需求而產生的態度體驗,是對一系列主觀認知經驗的統稱。而體驗主要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兩極分類,肯定的體驗如愉快、欣喜等,否定的體驗如悲傷、焦慮等。良好的情緒對于個體保持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個體持續地出現消極的情緒,那么他將長期處于緊張的狀態而導致機體衰竭,誘發疾病的產生。此外,持續消極的情緒容易使個體采取消極的防御機制,使個體不能正確地認知、評價自己所面臨的遭遇,如患病,進而導致醫生和個體無法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這對于治療而言是十分不利的。應優優等通過對125例患者的研究發現焦慮是誘發冠心病發病的獨立且重要的危險因素,同時冠心病伴發焦慮抑郁的比例會顯著高于非冠心病組伴發焦慮抑郁[16]。負面情緒中的焦慮與抑郁會影響冠心病的發病與預后,是冠心病的一項獨立危險因素[17]。通過日常生活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當一個人處于焦慮或者憤怒的狀態時,他的心跳會加快。甚至有臨床觀察發現,處在這種狀態下的個體紅細胞的數量激增,血液凝聚加快,血液上升,心律不齊,而這些癥狀是會誘發心肌梗塞、猝死等疾病的發生。相反,在任佳豪等人的研究中發現,如果根據冠心病患者的不良心態給予針對性的護理,能對控制冠心病的延伸產生積極的作用[18]。因此,情緒的好壞與冠心病的發展息息相關,不良的情緒會使冠心病患者的病情惡化,而病情的惡化又會增加個體焦慮、緊張等不良的情緒,產生惡性循環。而良好的情緒、心態,能促進患者的康復。
2.3 人格特征
相關研究證實,個體的人格特征與疾病之間存在十分緊密的聯系, 個體的人格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心理、生理的健康發展,某些人格特征與有某些特定疾病具有相關關系[19]。美國醫學家Friedman和Roseman在研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身反應時,把人格分成A、B兩種類型,并提出說A型人格是冠心病的獨立危險因素[20]。而A型行為類型與高血壓、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關系也已經被明確了。根據行為主義理論,當個體的刺激受到獎勵后,其行為會得到陽性強化,當今的社會發展正造就越來越多的A型行為模式者[21]。通過調查研究發現[22],A型人格者的行為特征主要有以下幾點:有遠大的抱負、競爭意識強烈、好勝性強,情緒易波動,好斗、缺乏耐心;有時間緊迫感與追求高效率等特點;常同時進行多種思維與動作,言語與動作的節奏快。從這些行為特征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人群將會常常處于應激的狀態下,而應激會使得個體的交感神經處于興奮狀態,表現為血壓升高、動脈收縮等,導致神經內分泌系統的紊亂,最后引起代謝功能的紊亂,從而引發了冠心病。宋晶晶采用A型行為問卷對40例冠心病患者與對照組40例進行測試比較,發現A型行為模式與冠心病具有相關關系,即A型行為者更容易患冠心病[23]。涂群芳和魏友平通過把60例冠心病患者按照患者行為分為A型行為冠心病患者的實驗組與B型行為冠心病患者的對照組進行研究發現,A型行為是誘發冠心病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A型行為患者發生緊張,使交感神經興奮、血漿兒茶酚增高,導致病情的加重[24]。因此,總體來說,具有A型人格特征的個體和正常人相比起來,更具備了冠心病的易感素質。
由于人體健康受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很大,所以單純地用醫學方法已經不能解決人類身心健康的所有問題。本文通過對社會支持、社會經濟狀況、慢性壓力應激狀態、情緒、人格特征、這六個社會心理因素的闡述,可以發現冠心病與心理社會因素是緊密相關的,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從前面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個體自身的生物軀體素質是冠心病發生的生理基礎,但個體的人格特征卻是其的易感素質。因此,具有A型人格特征的病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還要輔助認知行為的心理療法對其進行綜合治療,讓個體能夠感知到A型行為對冠心病帶來的危害。而由于生活應激事件以及因此所引起的負性情緒則是冠心病的誘發因素,應激事件可能主要作用于冠心病的發生階段,而不良的情緒則主要作用于冠心病的發展階段。應激事件的發生加劇了對個體的心理損傷,進而引發了冠心病。不良的情緒則使病情在發展階段不斷地遷延,難以治愈。在這樣的情形下,彼此相互影響,最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影響了病癥治愈的時機。而社會支持則主要對個體的心理壓力起著緩沖的作用,如果個體在預后能夠有良好的社會支持尤其是家庭的支持,那么不僅能夠減輕患者的心理癥狀,還能夠使患者在預后感受到治療的效果從而提高自身的生活質量。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提的六個因素并不是獨立地作用于冠心病的發生、發展、治療和預后的每一個階段,它們是一起作用于每一個階段,但在每一個階段作用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3.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療過程中,不僅要使用藥物,還得使患者明白社會心理因素在其疾病中的作用,并對其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預,這樣才能夠從生理、心理兩方面去消除病因,從而更好地促進患者治療和康復。
[參考文獻]
[1] 張銀玲, 雷鶴. 護理心理學[M]. 第四軍醫大學出版社, 2003.
[2] 李麗, 高大勝, 蔡鑫.不同年齡段冠心病患者臨床及冠狀動脈病變特點[J].新鄉醫學院學報, 2008, 25(6):608-611.
[3] 劉柳, 田建麗, 張紅,等. 中老年住院冠心病患者疾病相關健康素養與社會支持現狀分析[J]. 護理管理雜志, 2016, 16(1):7-9.
[4] 張國富, 任彩麗, 黃麗. 社會心理因素對冠心病的影響[J]. 新鄉醫學院學報,2009,26(6):2.
[5] Lazzarino A I, Hamer M, Stamatakis E, et al.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s Synergistic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from Stroke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013, 75(3): 311-316.
[6] Woodward M, Oliphant J, Lowe G, et al. Contribution of contemporaneous risk factor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ll causes mortality[J]. Preventive Medicine, 2003, 36(5): 561-568.
[7]楊黎, 張曉明, 楊紅梅. 冠心病與心理社會因素相關性的研究進展[J]. 護理研究, 2008, 22(33):3013-3016.
[8] 辛若丹, 李文森, 管考華,等. 焦慮抑郁障礙與冠心病的相關性[J]. 中國老年學雜志, 2017, 37(6):1556-1559.
[9] 楊燕飛, 張敏, 郭濤. 慢性壓力對冠心病發生、進展及預后的影響[J]. 心血管病學進展, 2013, 34(2):238-240.
[10] 馬建琴, 張秀麗, 張津寧,等. 慢性壓力與冠心病[J]. 心血管病學進展, 2009, 30(3):437-438.
[11] 李瑩, 徐偉仙, 郭麗君. 職業緊張與冠心病發病和預后的相關研究進展[J]. 中國心血管雜志, 2018(1).
[12] Chazelle E, Chastang J F, Niedhammer I. Psychosocial work factors and sleep problems: findings from the French national SIP survey[J].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6, 89(3):485-495.
[13] 史云科, 張敏, 肖踐明. 慢性壓力對冠心病患者心率變異性的影響[J]. 臨床醫學, 2014, 34(1):117-119.
[14] 胡恩元, 張敏, 肖踐明. 慢性壓力與冠心病患者體內皮質醇水平的關系[J]. 心血管病學進展, 2017, 38(1):94-97.
[15] Selye H. Stress and the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J]. Br Med J, 1950, 1(4667):1383-1392.
[16] 應優優, 李浙成, 胡智星,等. 焦慮抑郁與冠心病發生的關系研究[J]. 中華老年心腦血管病雜志, 2015, 17(7):762-763.
[17] Kozela M, Bobak M, Besala A,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cardiovascular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rospective results of the HAPIEE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2016,23(17):1839-1847.
[18] 任佳豪, 劉志琛, 孟憲梅. 冠心病患者不良心態分析及心理護理對策[J]. 心理醫生, 2016, 22(19):106-107.
[19] Hofer S, Sliwinskim. Associations between health,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aging [J]. Gerontologist, 2004, 44 (1): 765-775.
[20] Friedman M,Rosenman R.H., Association of specific overt behavior pattern with blood and cardiovascular findings; blood cholesterol level, blood clotting time, incidence of arcus senilis, and clinica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J.Am.Med.Assoc,1959,169,1286-1296.
[21] 秦子玉. A型行為模式與冠心病綜述[J]. 教育現代化, 2016(16):111-112.
[22]包曉紅. 心理因素與常見心身疾病的發生發展[J]. 攀枝花學院學報, 2003, 20(1):80-83.
[23] 宋晶晶. 冠心病與A型行為模式的調查研究[J]. 大家健康(學術版), 2013, 7(8):81-81.
[24] 涂群芳, 魏友平. A型行為冠心病患者血漿兒茶酚胺、5-羥色胺測定的臨床分析[J]. 醫學信息, 2016, 29(11):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