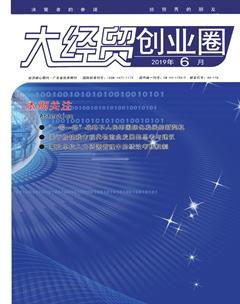高管“限薪令”問題再審視的雙重視角研究
【摘 要】 2009年,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與領導小組明確了國企工資的發展方向,要推動走向市場化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國務院會同相關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被社會稱之為“央企高管限薪令”。從全面深化改革實踐的視角看,政策的出臺其理論與實踐有著深刻的治理悖論,如何化解治理悖論給企業帶來的危機,順應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步伐,建立健全國企高管的市場化收入決定與相應的浮動機制,奠定科學有效的企業高管激勵機制,這將決定國企高管薪酬體系改革的關鍵。本文從我國制度背景出發,通過梳理公司治理結構中高管薪酬決定因素,探究國企高管“限薪令”所反映的公司治理“政治—經濟”的悖論,并就上述治理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 高管薪酬 限薪令 深化改革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顯著成效,我國國有企業薪酬體系制度也經歷一個從無到有不斷豐富的過程。從最初的的年薪制等逐漸到現在的最求權責一致,高管薪酬與企業績效相關聯并給予相應的股權、期權激勵等。從政府文件的規范視角,國企高管薪酬的市場化機制已經初步建立,并出臺了“央企高管限薪令”。
然而,在國企高管“限薪令”中,市場化改革每次伴隨中無形之手的干預,國企高管薪酬改革顯然與薪酬制度市場化相矛盾,是什么緣由導致二者相悖論?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黨政、政企模糊關系;二是經理人的市場假說能否在我國實踐中孕育土壤。就國企內部而言,高管之間溝通效率低下,內部薪酬委員會可能收到高管權利的妥協;就國企外部而言,沒有建立健全的外部審核監督機構和約束機制。因此造成國企高管薪酬治理“政治—經濟”的悖論,能否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將是貫徹國企薪酬體系改革的關鍵。
二、經理人的市場經典理論及其探討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相分離,由于企業內部約束不同,導致職業經理人的職權各有大小。因此,具有職業知識和特殊技能的職業經理人能夠將董事會變成任其驅使的“橡皮圖章” 。相比資本因素而言,職業經理人在計劃、組織、協調、溝通方面已經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生產因素,其擁有的社會專業技術職能與管理才能顯得愈發重要。這是由于職業經理人擁有這些管理能力,導致職業經理人成為企業的實際管理者。隨著職業經理人的興起,職業經理人開始對傳統企業管理的質疑與反對。從國家法律上講,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制度約束,導致職業經理人在公司運營管理具有很大的權利;董事會在名義上享有公司的經營控制權,實際上職業經理人負責企業的日常運營管理,外加信息的不對稱,使得董事會不能依法享有相應的職權。
基于上述現象,職業經理人在公司擁有如此大的權利,且不存在有效的預防監督體系,那么其職業道德風險如何預防?在公司法中,職業經理人的職責規定通常予以規范化,旨在通過市場化的機制,約束其活動,限制其職業經理人的相關權利,使職業經理人能夠勤勉工作并追求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三、國企高管薪酬的內部治理失靈與悖論
首先從頂層設計的制度視角看,國企高管薪酬體系的建立還需進一步完善。從有效建立董事會制度視角看,雖然在央企中董事會制度比較完善,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例如,獨立董事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領導班子高度統一、重復任職等現象屢見不鮮。董事會的先天缺陷,還需要在法律等制度上完善。此時還應當兼顧考慮國企高管中多重任職等問題,否則將會影響薪酬制度良好的運行。
其次,先天缺陷的董事會也難以發揮其有效作用。國有企業規范董事會制度的有效措施是建立外部獨立董事,企業高管薪酬委員會應當由外部獨立董事進行擔任,以滿足其獨立性要求。在我國制度背景實踐中,有的高管可能身兼多個崗位,這就有可能帶來“嵌入式代理問題”,并且薪酬方案的制定往往過于形式,其代表的還是高管的意愿。在實踐中,薪酬委員會的工作更多的是表面形式形式,實則與公司高管的態度一致,基于這種想法,擁有待遇享受慣性的外部董事,則更能夠理解而支持現任高管的薪酬方案。
最后,在國企董事會制度中,寄希望于董事而制約于國企高管薪酬,而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由于我國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國有企業代表的政府公共資源的延伸,則必然使得社會公眾對國企高管薪酬的關注度尤為關心,如果放任董事會做出決策,其必然會帶來不可承受之重,國資委作為其領導監督機構,必然會對薪酬委員會起指導作用。相反,董事會會明哲保身,由于有政府的“指導價”,又何必在薪酬制定中增添煩惱。何況,在董事職位已經帶來的可見的附加價值之時,比如社會地位、有價值的商業關系等等。此外,國有企業的董事一般沒有公司股份,國資委對外部董事的考核與監管機制仍然不完善。因此,董事會會毅然選擇國資委對其薪酬進行指導。為此,對于董事來說,其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搭便車投票的方式。
四、外部治理失靈:股東及社會干預的現實困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寄期待于從董事會這一內部機構來約束國企高管薪酬體系的實現路徑尚不明確,那么我們試探討從企業外部結構來約束其薪酬體系,即增加股東的干預程度。在實踐的過程中,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在針對初創型企業,在籌備和初創的董事會中,直接依據既有的法律進行確定;二是利用司法救濟的手段進行,這種方式主要通過股東行使訴權實現高管不當薪酬安排的訴控。但這兩種方式都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原因是在我國國企高管職位與政黨職位相重疊,這類職位具有過渡性,國企中部分高管職位充當的是某些具有行政職務的官員的中場休息職能。簡而言之,國企的這些職位具有時政性,一方面是用來安排官員做過渡性銜接,為晉升做跳板準備;另外一方面是用來作為組織的關懷,以慰藉這些官員在公職所做出的貢獻。由此可見,更好的 全方位可比性更高的待遇顯然更具有吸引力。如果說真正關心高管薪酬方案是否合理,只有真正的股東的話,畢 竟在保護自身利益的角度上,股東確實有更大的動機。少數股東關心的是如何在仕途中坦蕩以獲得更大的權利,對他們來說限制高管薪酬并不能獲得直接相關的利益。因此,高級薪資計劃的憑證確實是一種高風險行為,可能對未來的職業生涯產生負面影響,或者可能會限制未來的收益。
五、治理對策建議
1、完善國企以董事會負責制的公司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作為作為政府職能的延伸,其職責是為社會公眾提供其公共服務或產品。在國有企業中,要充分發揮黨組織的作用,以黨的領導引領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結構。對此,要發揮黨組織高度的組織紀律性,要嚴把路線觀,將剛性的組織紀律嚴明性與柔性的指導建議相結合,化解國企公司治理與政治原則的矛盾。我國國企治理結構與研究應當側重于最求國家中長期經濟效益的目標,探究企業制度特別是產權制度與治理結構的設計、實施以及變遷的規律。國企公司治理的實質是變革生產關系,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2、國企董事會應當得到授權和執行
國有企業應當切實落實董事會選聘人員和高管薪酬的決定權,從制度方面貫徹落實高管對董事會負責的基本治理結構。對于以非公益性國有企業為主的高管應當徹底從行政體制中分割出來給予單獨設置,逐步關閉體制內的政商“旋轉門”特別是競爭性國企高管與政府官員之間的任職“旋轉門”,國企高管要想獲得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就必須放棄行政級別及其相應的政治待遇,以消除國企高管的政治約束對其經濟動機的扭曲。在國內環境下,獨立董事在公司治理實踐中發揮監督、制約國企高管薪酬的作用有限。為此,應當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經營管理公司的“管資本”作用,通過出資人的身份或者股東代表參與國企高管薪酬的制定,通過董事本身的經濟 回報、連任、聲譽等機制使董事與出資人的長期利 益一致化,“讓董事相對更親近股東”而相對更加獨立于高管。
3、創造薪酬體系的司法和社會輿論監督治理體系
適當的司法介入有利于公司創建更完善的治理體系,促進公司在高管薪酬設計方面更加合理。此外,對于沒有建立合法高管薪酬體系的公司應當建立懲罰性賠償機制用于支付律師費,這樣有利于鼓勵有高水平的專業訴訟律師介入,提高外部監督能力,讓企業更好的遵守相關規定。研究表明媒體監督是一種強有力的外部監督手段,同時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通常會讓公司在媒體壓力下對高管薪酬進行合理設置,縮小和其他員工的待遇差距,因此,媒體的監督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目前我國媒體目前在獲取企業高管薪酬相關信息時還存在一定的困難,企業信息不夠公開透明,因此應該完善媒體獲取相關信息的渠道,保證媒體報道的客觀、公正和自由,結合司法訴訟的懲罰性賠償機制,共同形成對于國企高管薪酬待遇的社會監督合力。
【參考文獻】
[1] 王曾,符國群,黃丹陽,汪劍鋒.國有企業CEO“政治晉升”與“在職消費”關系研究[J].管理世界,2014(05):157-171.
[2] 張楠,盧洪友.薪酬管制會減少國有企業高管收入嗎——來自政府“限薪令”的準自然實驗[J].經濟學動態,2017(03):24-39.
[3] 劉鳳芹,于洪濤.管理層權力、高管薪酬與“限薪令”的政策效果[J].社會科學戰線,2019(04):48-57.
[4] 沈藝峰,李培功.政府限薪令與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業績和運氣關系的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11):130-139.
作者簡介:蔣成(1993.03),男 ,學歷:碩士研究生,單位:重慶工商大學,研究方向: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