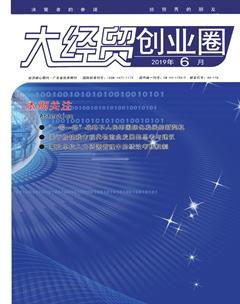廣西城鎮化發展與農村持續脫貧的關系研究
歐灌瑩

【摘 要】 中國三十多年的減貧經驗終發現城鎮發展對農村發展有輻射帶動作用,對此本文以欠發達地區廣西為對象研究城鎮化發展與農村持續脫貧的關系,發現廣西城鎮發展對農村貧困人口持續增收效應不佳。對此政府要發揮調控作用,通過頂層設計、加大資金投入和稅收優惠力度等方式提高城鎮發展質量,打通城鄉聯通障礙,實現城鄉互聯互通。
【關鍵詞】 城鎮化 農村 可持續脫貧
一、引言
2018年6月中央《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不急功近利,注重幫扶的長期效果,夯實穩定脫貧、逐步致富的基礎”。廣西是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2012年至2017年累計減少貧困人口704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8%降低到5.7%。[1]為了實現長效脫貧成果,廣西各級政府積極發掘地區優勢,創新產業精準扶貧規劃,提出的縣級“5+2”、村級“3+1”等特色主導產業的發展模式,成為全國典范。至2018年8月,全區5382個貧困村(包括新增的深度貧困村)中已有新型經營主體的貧困村5032個、已有產業基地覆蓋的貧困村4462個,通過發展鄉村產業保證脫貧質量的做法得到國務院和國家有關部委的肯定。[2]但是從廣西的做法也可以看出,這些產業扶貧措施依靠政府資金和各項優惠政策的推動,引進的大多企業是外地著名企業,廣西本土的產業發展在拉動農村經濟發展存在疲軟現象。在脫貧實踐上,中國30年的大規模減貧印證了華盛頓“滴漏經濟增長”的發展理念。通過“先富帶動后富”的“涓滴效應”能夠鏈接城市和農村的經濟發展,幫助農村發展實現增收。廣西區由于歷史原因經濟建設起步晚,城鎮化發展相對落后,從扶貧的產業帶動上可以發現廣西區城鎮化發展在帶動農村經濟上、實現農村脫貧可持續上存在局限。在這一背景下,需要進一步認識到廣西區城鎮化發展與農村居民脫貧可持續之間的關系,并根據這種關系的大小為廣西區以后的脫貧攻堅工作做出相應的規劃。
二、文獻綜述
農民脫貧和城鎮化長期以來是社會談論熱點,隨著2020年的到來脫貧可持續問題也引起學者的關注。關于農民脫貧,相關文獻指出經濟增長是前期大規模減貧的主力,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城鄉收入差距弱化了經濟減貧的效果(汪三貴,2008)。進一步實現全面脫貧要解決貧困“硬骨頭”,對此學者們普遍認為需要從農民自身的發展能力——例如貧困農民健康、教育水平等人力資本的限制(徐舒,2010;程名望,2014),以及制度(阿瑪蒂亞·森)、自然條件(白南生,2000;施國慶,2010)、社會關系(付少平,2015)等發展障礙著手,采取相應扶持措施提升貧困群體先天羸弱的發展能力才能使他們增收。我國在采用非常規的精準扶貧政策后,地區脫貧攻堅成果顯著,但也發現一些問題,比如非常規的扶持政策沒有帶動相應的產業發展、技術水平的提高(張曉山,2018),而地區精準扶貧與區域的發展聯動相輔相成(王春光;2018),地區發展不與區域發展相適應難以實現持續增長。
關于城鎮化和農民減貧,實際上城鎮化對農民減貧的推動力在于通過城鎮化發展提高貧困及非貧困農民收入。城鎮化能聚集勞動力和生產要素實現聚集經濟(Henderson et al,2004),由此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聚集,進而推動農村規模化經營和擴大農產品市場,實現農民增收(廖丹清等,2002)。對此,眾多學者研究發現區域城鎮化進程對農民收入提高具有正面效應,且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王鵬飛,2013)。城鄉區域的經濟集聚對本地農民和周邊農民收入提升都有正向效應(伍駿騫等,2016;錢瀟克、莫蕙,2018)。
從以往的文獻可以看出,城鎮化發展對農民平均收入的整體提升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于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而言地區發展對農民收入提升和減貧仍有重要的作用。廣西屬于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從當前的現狀看廣西城鎮化發展迅速,但這是否對農村貧困人口的持續增收是否起到作用呢?對此本文選用廣西作為研究對象,對廣西城鎮化進程和貧困農民收入間的關系為進行分析。
三、實證分析及結果
(一)數據說明及檢驗
本文以廣西城鎮化與持續脫貧之間的關系為研究內容,以廣西2000-2017年的統計數據構建VAR模型,“讓數據自己說話”(古亞拉蒂,1997)。在對持續脫貧的指標選取上,根據國內外的研究發現在脫貧方面需要關注貧困人口的多維因素,但是要實現貧困人口的持續脫貧最終體現在貧困人口收入的提高。因此本文使用占廣西農村總人口20%的最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li)作為貧困農民持續脫貧的衡量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從人口學的角度定義城鎮化,使用歷年城鎮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表示城鎮化率(ur),該指標在統計上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未考慮城市基礎設施等城鎮化發展質量問題,但從以往的文獻看這一替代是可行的。為了消除價格變化或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以2000年為基期的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處理收入數據。以上數據均來源于歷年《廣西統計年鑒》。
為了避免無效偽回歸結果,在模型建立及預測之前對變量進行ADF平穩性檢驗。為了減少數據中異方差的影響,對指標取自然對數lnli、lnur,相應的一階差分變量為Dlnli、Dlnur。經過ADF檢驗發現,貧困農民收入指標和城鎮化水平指標本身為非平穩序列,但講這兩個指標進行一階差分后都是平穩的,即這連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二)模型構建及檢驗
根據平穩性檢驗結果,Dlnli、Dlnur為平穩序列。因此采用Dlnli、Dlnur數據建立VAR(p)模型,并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對其進行解釋。利用stata15確定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發現有4個評價準則認為最佳滯后期數為3,因此選擇滯后2期建立VAR(3)模型。將Dlnli、Dlnur滯后1~3期的值作為內生變量,建立VAR(3)模型,在統計量檢驗中發現一部分系數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方程中加入多個滯后值產生了多重共線性。但經過單位根檢驗發現模型對應特征方程的特征根絕對值均小于1,所以VAR(3)系統是穩定。
向量自回歸模型是一種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在此研究中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城鎮化發展和低收入農村群體平均純收入提高的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各自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更看重系統的穩定性,所得出的模型系數顯著性并不影響后續的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
(三)脈沖效應結果及分析
利用建立的VAR(3)模型,對變量Dlnli、Dlnur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周期為10年,結果如下圖。
觀察低收入農民純收入對城鎮化發展的響應發現,在前期低收入農民的純收入水平對城鎮化的沖擊產生一個負向的微調,在短暫負向微調后農村貧困人口收入對城鎮化的沖擊有正向響應,持續一段時間后又有一個較大的負面響應,但又隨之有較長久的正面響應,如此循環,最終趨于穩定的正向收斂跡象,整體來看是有一個正的響應。這說明廣西城鎮化發展與低收入農民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密切關系。結合廣西的地區城鎮化發展和低收入農民增收來看,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廣西區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存在較強的短期行為,城鎮化發展速度快但質量不優,發展方式仍顯粗放,以至于城鎮化規模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經濟發展滯后,無法有效拉動低收入人群增收。從長遠看,城鎮化發展對農民收入增長會產生持續的正向拉動作用,因此,廣西各級政府在推動城鎮化的過程中,應更注重城鎮化推進政策的質量和長期政策效應而非短期“提速”目標,采用長期政策。另外要注重城鄉發展的政策耦合和市場互通,增加城鄉發展聯系,減短響應時間。
另外,低收入農民純收入對自身標準差變動的有很強的正面響應,這種強的正面響應持續時間較短,呈現逐年起伏效果減弱的趨勢。這表明當前低收入農民的純收入水平與其滯后值有較強的正面響應,這種正面效應有較大的波動,趨于減弱。這也側面印證當下提升貧困人口個人發展能力的精準扶貧政策。要實現脫貧可持續需要依靠貧困農民的內生發展動力,通過農民內生發展能力的提升實現持續增收。在這方面政府需要針對農民的人力資本實施政策。
對于城鎮化發展而言,農村低收入人群純收入的增加對城鎮化發展表現為微弱的負效應,效應逐年減弱。這背后蘊含的是資源使用的效率問題。對于農村低收入人群他們收入的提高很大程度依賴外力幫助,這其中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責任,投入和引導社會資源助力脫貧。而城鎮化的發展也需要資源投入,資源是有限的,而且從資源的有效配置來看使用于農村扶貧的資源經濟效率肯定不如投資于城鎮地區的發展,所以最后表現為貧困人口收入的提高會影響到整體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進而影響城鎮化的發展。對此扶貧政策的實施,要從長期角度考慮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與本地城市的發展聯動問題。
另一方面,城鎮化發展對自身標準差變動一開始為正響應但逐年減弱并變為微弱的負面響應,而后向正響應最后趨于正向穩定趨勢。這背后也隱含和城鎮發展的長期有效政策問題。
(四)方差分解結果
方差分解作用在于分析不同變量的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對VAR(3)模型分解得如下結果。
從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發現,農村低收入人群純收入對于自身的沖擊影響非常強烈,在第一期完全受自身的沖擊影響,隨后逐年減弱。對城鎮化沖擊的影響在第一、二期幾近于無,第三期開始有微弱影響并逐年擴大,到第8期達到10.25%。城鎮化發展從第一期就受自身沖擊和農民低收入群體純收入的影響,受農民低收入群體純收入的影響初期相對較小,而后影響變強并超出自身沖擊的影響,穩定在55%左右。
四、結論及建議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城鎮化發展與農村貧困人口收入增長之間存在長期性的緊密聯系。廣西近17年的數據顯示廣西的城鎮化進程對拉動貧困農民增收效果不佳,農民對城鎮化響應時間較長。當前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和引導作用,以市場選擇為導向,從頂層設計著手充分使用財政資金、稅收優惠等手段,從基層的產業扶貧、教育扶貧落實、促進城鄉融合,促使城鎮集聚效應的發揮。
首先,解決貧困農民先天發展障礙、開拓貧困地區市場經濟。對貧困人口而言在中短期內自身發展能力的限制仍是增收的主要障礙;大多貧困地區以小農經濟為主,地區發展能力有限。對此中短期要堅持以人為本、以開拓地方發展能力為主的精準扶貧原則。在此期間,廣西加大對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的財政扶持力度,短期內帶動貧困地區農民增收,開貧困地區市場。此外,從農旅結合角度,通過產業獎補、扶貧補貼等方式調整農民養殖種植的農業經濟結構,引進優勢產業或龍頭企業,培育地區主導產業,加快農村地區產業發展和融合,提高農民的長期創收能力。
第二,提高城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廣西具有多重優勢,對此政府要依據地區優勢,對各城市發展做出定位,出臺相應政策、制度引導地區產業發展。結合市場需求和地區要素稟賦,從需求角度進行供給側調整,加大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力度,推動農業轉型升級,提高農業產品競爭力,因地制宜實現城鄉經濟和工農經濟的聯動和供需匹配,通過全區各產業鏈條的互通實現城鄉互聯互通,為城鎮化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可持續發展動力。
第三,改善城市服務環境,為城鄉交互奠定基礎。政府要安排專項資金自城市中心開始優化、強化公共服務體系,尤其是鋪設交通網絡,包括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城鄉交互的便捷度。當前特色小鎮、農旅結合是扶貧的重點,而要充分廣西自然條件實現旅游扶貧就要完善旅游條件。其次要積極推廣包括資金融通、市場開拓、技能培訓等內容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和相關制度完善,逐漸全方位鋪設經濟發展服務網絡,實現城鄉信息、資金、技術等的互聯互通。
【參考文獻】
[1]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實施意見[Z].2018-10-24
[2] 陳靜,賀亮軍. 廣西產業精準扶貧規劃成全國典范[N]. 廣西日報.2018-10-25(5)
[3] 李愛玲,王凱.新型城鎮化對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影響研究——以湖北省為例[J].商業經濟研究,2018(17):153-156.
[4] 廖丹清,郭慧伶.城市化對減少農村人口、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J].中國農村經濟,2002(11):78-80.
[5] 王春光.貴州省脫貧攻堅及可持續發展研究[J].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3):39-56.
[6] 張曉山.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應關注的重點[J].經濟縱橫,2018(10):1-11.
[7] 王鵬飛,彭虎鋒.城鎮化發展影響農民收入的傳導路徑及區域性差異分析——基于協整的面板模型[J].農業技術經濟,2013(10):7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