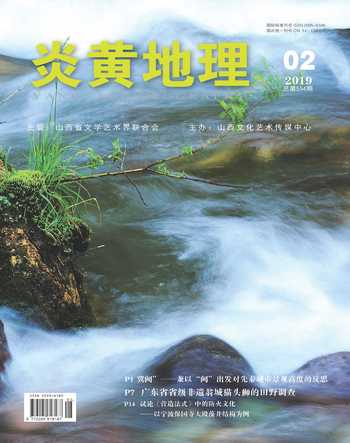從黃河最后一道彎看蘭考的苦難與治理
摘 要: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不僅塑造了華北平原,造就了中華文明,也帶來了嚴重的黃河水患。尤其是下游黃河蘭考段決口泛濫頻繁,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歷史上給蘭考人民帶來過深重的災難。新中國成立后,為治理黃河,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胡錦濤、習近平等多次到黃河視察,并就治理黃河、改善民生等發出偉大號召。蘭考人民的黨的領導下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與自然斗爭的過程中化害為利,將黃河變成了一條造福一方的金河,譜寫了一曲曲人與自然斗爭的壯美詩篇。
關鍵詞:黃河;蘭考苦難;治理
黃河東壩頭位于蘭考縣西北部的東壩頭鄉,距縣城10公里。在這里,我們的母親河——奔騰咆哮的九曲黃河完成了她那最后一彎,直奔大海。歷史上黃河多次在此決口,新中國成立后,為治理黃河修筑了工程石料運輸專用線,毛主席、習近平總書記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先后在此視察黃河,現如今,當地群眾充分利用這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走上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致富路。巍巍黃河東壩頭見證了這里的苦難和輝煌。
黃河改道,苦難蘭考
黃河自古以來就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歷史上向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據史料記載,歷史上黃河共決口1590多次,在蘭考決口就多達143次。蘭考東壩頭就是黃河最后一次決口改道的地方,這里的28號壩在明朝弘治年間為河道北岸大堤,清朝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在此以西的銅瓦廂決口改道,于是此處變成了大河東岸的一段堤頭,故稱“東壩頭”。1912年,黃河在東壩頭以上兩千米處坐灣坍塌,隨即搶修了3座垛子。1914年,又在東壩頭拋石加固,以防再次坍塌,出現了東壩頭險工雛形。上個世紀的1901年和1933年,黃河還先后在附近的四明堂和南北莊決口。當時有首民謠曾廣為流傳:“六月二十一,打開南北堤,先淹考城縣,后淹小宋集。”[1]訴說的是1933年農歷六月二十一,黃河在河南蘭考縣東壩頭西的南北堤決口的辛酸往事。正是因為這里有潰堤決口造成黃河改道的危險,所以東壩頭在黃河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
黃河多次肆虐,造成了蘭考風沙、內澇、鹽堿“三害”的形成。正因為黃河的不斷決口與河道的來回擺動,在蘭考這個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留下了一條又一條黃河故道和斷堤、廢堤。斷堤、廢堤和村莊縱橫交錯,形成了一個又一個大風口,冬春季節5到7級的大風十分常見;黃河故道上的黃沙隨風起落、堆積下來,又會形成大面積的風沙地和一個個移動的大沙丘;夏秋多雨,坑洼不平的土地上,到處積水,形成了難以治理的內澇;這里冬春天旱,澇地里的水蒸發后,又形成大片大片的鹽堿地。據統計,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蘭考大的風口就有80多個,風沙地36萬畝、澇地24萬畝,還有26萬畝的鹽堿地,而當時蘭考的耕地面積還不足一百萬畝[2]。
嚴重的“三害”,導致了數百年來蘭考老百姓的極度貧窮。走投無路的蘭考百姓,不得不攜家帶口外出逃荒要飯。解放前,一般年景,有40%-50%的人要外出要飯,受災年份,常常達到80%以上。1913年蘭考通火車后,“蹬大輪”扒火車成為蘭考及周邊群眾外出要飯的主要選擇。1942,河南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旱。上百萬的河南人被饑餓、浮腫、奪去了生命。而蘭考就是河南的重災區之一,這里不僅有旱災,還有內澇、鹽堿,甚至蝗蟲。逃荒途中有首民謠說:“春天風沙狂,夏天水汪汪;秋天不見收,冬天白茫茫;一年汗水半年糠,交租納稅恨官堂;扶老攜幼去逃荒,賣了兒和女,餓死爹和娘……”[3],可以說這就是當年蘭考百姓生存狀況的真實寫照。
十里險工,濟國安瀾
1952年毛主席視察黃河(網絡圖片)
治理黃河歷來是中華民族安民興邦的大事。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十分重視黃河治理開發與保護工作,為了讓“地上懸河”造福人民,重點加大了黃河蘭考東壩頭十里險工的建設力度,在黃河蘭考東壩頭段筑起了一道道防洪石壩,使這一帶的大堤得到徹底加固,促使河道順暢,水流平穩,東壩頭也成為了當時一個相當繁華的小型碼頭。80年代以后,由于河道爛滾,加上公路交通發展,東壩頭的小碼頭僅作為民間擺渡使用。
2003年,黃河流域發生了多年不遇的長時間秋汛,黃河干、支流共發生十余次洪水,洪水量超過20億立方,河南蘭考、山東東明部分灘區上水,村莊被圍。由于蘭考至東明黃河灘區位于“二級懸河”較為嚴重的河段,進灘洪水在行進中匯于大堤堤根,形成堤根河,洪水偎堤長度35公里,平均水深1~3米,當時河南、山東10萬多群眾被洪水圍困。期間,受河勢變化,大溜頂沖,在東壩頭東北10多里外的灘區,一場洪水沖垮了那里的生產堤,后經上萬軍民共同奮戰40多天,才堵住了決口。災情發生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12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迎著凌厲的寒風,專程趕往受災灘區,把黨和政府的關懷及時地帶給了災區廣大干部群眾。即便如此,60多年來,黃河水雖然多次在蘭考東壩頭段兇猛逼岸,但每次都能安全度過,這里再也沒有發生過一次決口溢水。
今天,當我們站在壩頂,低頭細看奔流不息的黃河時,只見由西而來湍急異常的黃河水猛地撞了一下堤壩,又打著漩渦掉頭奔騰北去,兇險之狀令人頭暈目眩心驚膽寒。不過若極目遠眺,又會感覺反差很大,但見滾滾黃河天水一色,十里險工巍巍壯觀,讓人頓覺心曠神怡胸襟開闊。再看四周,這處“險中之險”猶如有“重兵把守”一般——一道道堤壩全用水泥石頭砌成,壩上碼好的備方石,堆放的整整齊齊,猶如防護大堤的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解放以來,這里已經數十次經受住了洪水的考驗。可以說,黃河蘭考東壩頭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勞動人民“改造自然,造福人民”的重要歷史見證。
一段鐵路,難忘記憶
當年,為了治理黃河,國家在蘭考車站的2號道岔處,引出了一條西北走向的鐵路線,這就是中國鐵路史上最短的鐵路支線——蘭壩支線。這條鐵路專用線是1951年修建的,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烽煙未熄,百廢待興,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已經下定決心治理黃河。為了不讓黃河再從東壩頭決口禍害人民,為了便于運送防洪石料鞏固堤防,國家斥資修建了這條12.5公里長的蘭壩支線。
1952年10月30日和1958年8月8日,毛澤東主席乘坐的專列先后兩次停在了蘭壩支線上。當專列第一次穿過田野村莊,爬上了巍巍的黃河大堤,來到東壩頭時正值秋末,汛期剛過。這位新中國的締造者漫步于大堤內外,眺望著大河上下,時而詢問,時而沉思,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并在視察結束后,擲地有聲地發出了“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4]的偉大號召。2014年3月17日,在蘭考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期間,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黃河蘭考東壩頭段,望著滔滔河水,不時向有關人員詢問黃河防汛狀況,詳細了解黃河灘區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并叮囑開封、蘭考的干部要切實關心貧困群眾,帶領群眾艱苦奮斗,早日實現脫貧致富。在毛主席、胡錦濤、習近平等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下,黨和政府帶領沿黃人民多策并舉,綜合治理,不僅保證了黃河安瀾,而且引黃灌溉,變害為利,蘭考也由原來“三害”肆虐的重災區,變成了林茂糧豐的米糧川。
東壩頭原來設有車站,配有值班站長和值班人員。站內原有3股道,1道、2道的有效長度848米,可以容納敞車60多節,3道的有效長為1089米,可以容納敞車80多節。運送石料的任務的一直由蘭考車站調車組擔當。上世紀50至70年代,石料成列到達比較多,調車任務比較重,進入90年代,石料都是零星到達,任務輕多了。至于列車一共往東壩頭送了多少石料,沒有人去細致算過。不過,據當地人講,大壩之下的石料全部來自安徽碭山一個山頭,如今,那個山頭已經被夷為平地了。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勞動人民,包括我們的鐵路職工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造就了這巍巍堤壩。1998年,為了支援長江抗洪,從蘭壩線裝運了一列石料發往長江抗洪一線。小浪底水庫建成并投入使用后,黃河下游的防汛壓力大大減輕,蘭壩線就此完成了其歷史使命,被逐漸廢棄。廢棄后的蘭壩線成了幾代蘭考人心中的永恒記憶。
近年來,為了讓更多的人領略九曲黃河最后一道彎的壯麗與雄渾,追思治理黃河的艱辛與不易,感受蘭考時代發展的腳步與脈動,蘭考縣規劃建設了蘭考·1952鐵路文化旅游項目,重新啟用了部分蘭壩線,在黃河蘭考東壩頭建設了一座小火車站,打造了以蒸汽小火車為主題的沿黃河觀光游覽線路,并于2017年5月1日起正式投入運行。如今,蘭壩支線上的火車又一次開始轟鳴,沿線村莊的鄉村群眾也借機發展各類配套產業,在東壩頭的大堤上,當地人建起了果園,河灣里跑起了游船,周邊不少村莊還搞起了農家樂、民宿等,吸引不少人前來游玩,鄉親們也終于過上了香甜滋潤的好日子。
參考文獻
[1]譚可、栗鑫、張海鋒:《焦裕祿精神在蘭考》第二篇《黃河故道的舊貌新顏》[N].映象網-新聞廣播,2014-4-10.
[2]周長安、趙永祥、吳玉青:《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3]姚偉:《豫地密碼之蘭考:地名演變錯綜復雜 主要因為黃河》[N].大河網-大河報,2014-3-17.
[4]孟冉:《“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指示由來》[N].大河網-大河報,2007-8-9.
作者簡介:
賈關青(1983 -),漢族,河南蘭考縣人,河南大學經濟學學士,焦裕祿干部學院辦公室干部,研究方向為黨性教育和焦裕祿精神相關。